世博会和我的理想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朱步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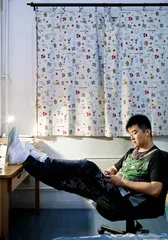 ( 朱步冲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2~至今 )
( 朱步冲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日子:
2002~至今 )
2010年,按照中国人习惯以当年某个重大事件将其命名的习俗,似乎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为世博年。从电视购物频道里各种名目繁多的主题收藏品到矗立在世博园区内,外形宛如中国古代冠盖、颜色大红的中国展馆,似乎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既有经济与组织上的能力承担这样一件繁复浩大的盛事,亦拥有足够的技术与文化成果以供展示与分享。在这种情况下,《三联生活周刊》要做出一期彰显自身话语权与独特视角,关于世博会的厚重封面报道,早就成为板上钉钉之事——而“如何做”这个既简单又至为复杂的问题,却一直横亘在整个编辑部面前。3月底,主编朱伟特地召集苗炜、舒可文、李鸿谷等编辑部高层以及许多周刊同僚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严肃而漫长的“神仙会”,得以列席的我在兴奋紧张之余,也不免开始推敲。这次讨论的结果,有了一个叙述最终落脚点以“理想国”概念的噱头,超越了对于历届世博会本身历史的盘点与罗列,将焦点集中在技术进步与人的关系上。出乎意料的是,我被主编委以重托,让我撰写封面主文,任务就是以有限的篇幅为读者提供某种浓缩式的简约回顾,并将150年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纳入某种宏大的理论框架之中。
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在主编分配任务时,我已经习惯性地拿出那个有点陈旧磨损的三联书店记事本,开始勾勒这篇文章结构的“立体图”。在这个存在于三坐标系统的立体矩阵里,首先要依据时间坐标,确立一条竖直的“行动线”——任何特定工作最终指向的目标,即这篇文章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总体观念——关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技术进步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另外,被“行动线”贯穿的,是许多个“平面”与“块”,即被这些进步影响的人类生活与生产的不同层次和领域。而它们的交汇之处,就是一些理应关注的焦点问题与事件:诸如化学肥料,无土栽培技术的发明遭遇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口激增时,所引发的“绿色革命”。
幸运的是,在前期准备工作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资料收集和梳理工作——主编曾有远见地叮嘱我在最初阶段整理一张分类表,历数那些在历届世博会上亮相,改变人类物质文明与社会的工业科技成果——蒸汽机与蒸汽机车,转炉炼钢法,机械计算机,电话,乃至宇航飞行器与工业机器人,诸如此类——作为基本资料与同事分享。从这些表面上的切入点,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常常是与某些焦点问题关系密切的象征性个案:诸如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世博会上亮相的麦考密克收割机:这台由美国弗吉尼亚农庄主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发明,带有地轮驱动切割刀、拔禾轮和集穗台的新奇机械,能够使得两个劳动力数小时内就能收割一英亩小麦,而利用传统方式,同样的工作量需要40小时才能完成。如果采取某种“大历史”观念来考量它诞生的年代,以及当时美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就会发现,它无疑是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时代到来的讯号——借助这项发明,美国小麦产量在19世纪50年代从1亿蒲式耳上升至1.73亿蒲式耳,同时成功地将农业产业人口挤压下降,进而带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如此以某件非常事件或“奇闻趣事”为引线,激发读者好奇心,就能使得他们得以放宽视界,看到长期发展态势,而不会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时而被连续不断,彼此看起来毫无干系的人名、统计数字所激怒,失去耐心;抑或感觉某一事件无法诠释,必须倒退到谴责历史当事人品行之愚顽不肖,方能释怀。
在世博会诞生的历史年代中,公认的三波现代化大浪潮相继发生,工业的助推力从煤炭、蒸汽机演进为电力与化工复合材料,进而转化为石油,人工智能乃至基因技术——如果将世界比作水塘,而以投入的一颗石子比拟为技术进步,则这三次现代化运动宛如石子投入池塘所激发的涟漪一般,迅速从欧洲波及北美、中东、东亚乃至拉美、非洲等地,而在我的构思中,写作的叙述也必须以此三次浪潮而做出分期。
宛如拍摄一部电影一样,一旦确定了剧本大纲,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遴选演员,确定拍摄地点,定制服装与道具等一系列工作。然而正如同《星球大战》、《斯巴达三百壮士》等计算机数码图像时代的好莱坞票房炸弹的拍摄一样,绝大多数情节不得不发生在动态捕捉“绿屏”之下,演员必须对着空气讲话,等待电脑特技制作者在后期将他们的对手戏演员和CG布景“粘贴”上去——这是一次完全发生在书斋中的写作任务,我无法同在这150多年风云激荡历史中的那些伟大人物和先贤——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罗斯托、帕森斯等——直接对话,更难以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那些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刻:戈特里布·戴姆勒博士在巴黎世博会上展示第一辆汽车;艾默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这两位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在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上进行的环境问题讲演;或者土星五号火箭第一次从肯尼迪宇航发射中心腾空而起。不仅如此,所有能够落实的,对于历史研究者和一些关键人物的采访也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我也无缘与他们面对面地进行攀谈。毫无疑问,无论我怎样竭力避免,都会使得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隔膜感——他们无法直观地走进150年前阴郁、街道狭窄、笼罩在煤烟中的伦敦工人区,或者今日底特律汽车工厂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也不易对这种技术以及其对应的社会结构感同身受。
 ( 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原子模型馆 )
( 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原子模型馆 )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虽然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道德评判,但无论普通读者还是研究家,都无法在阅读时完全摆脱个人好恶。我们自身的情感亦时刻发生作用:进步这一概念是工业社会意识领域的核心,然而我们今日却发现对于进步的信仰是一个残酷的神话。世博会从单纯展示人类在诸多领域取得的累累硕果,逐渐演变成为大众娱乐时代的主题公园,虽然其本意在于宣扬工业文明人类带来舒适便利生活,但在多种方面,技术进步与工业革命并没有做到那些期许:当我们在阅读中,得知恩格斯当年曾亲自走访伦敦工人区,发现纺织场内清理破布的女工罹患伤寒,斑疹等疾病,工人一家常常与跳蚤、虱子共居斗室,无床铺、被单与家具。而今日,从越南服装加工厂到玻利维亚铜矿,第三世界广大劳动人口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勉强糊口——在此一个月后,深圳“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又一次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分配不公,劳动者境遇恶化的一个鲜活案例——这一切都不能不令我们掩卷反思: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意义何在?到底有何种力量,才能对全球不公的经济与贸易体系作出匡正,以适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时隔几日,我在北京鼓楼一家咖啡店里跟一个混迹京城的英国留学生吵了起来。我告诉他,并非中国人完全乐于盗版、仿冒,考虑到每个价值1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能拿到的加工费不过35美分,而从发达国家以贷款和投资形式流向第三世界的每一美元中,最终能够留在当地的不过7~9美分,其他都以公司利润、债务利息等形式流回,如何指望世界的另一部分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富裕与发展?
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思绪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北大燕园:在1997年秋季学期,我在机缘巧合之下选修了亚非拉教研室董正华老师的“现代化理论与进程”专题课。董老师是“现代化研究”系列丛书主编,曾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并将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译为中文。他治学严谨,讲求纪律,常以一身简朴的蓝色中山装,手拎一黑色旧皮包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曾对调皮私语的同学加以斥责,不留情面,但课下又亲自分发亲手选择考订之阅读材料,对前来发问者知无不言。在我的书柜里,迄今为止还保存着一份自己学士毕业论文《拉美近代政治中的军人干政》的答辩意见书,上面留有董老师用蓝色钢笔字写成的详尽评判意见。何为现代化?即便在进入历史系学习数年后,自己对这个宏大概念的理解仍然是粗浅的“经济现代化”或者更为狭义的“工业化”。然而,通过在课程上接触塔尔科特·帕森斯、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社会学名家的理论,我方才意识到,“现代化”可以囊括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有变动,也是人类对自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合理性控制的扩大。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诞生,大背景则是60年代初,美国政府策士意图抑制第三世界相继发动古巴式社会主义民族革命,而对于其“替代性发展道路”的探究。它忽略了欠发达社会的具体环境和文化特性,而将其囫囵地放在一组静态,一元单线的发展指标体系中衡量,并过高地估计了后者的可塑性。曾作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成员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持续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和不平等的“中心-外围”全球体制,造成了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现状;但总之一点毋庸置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应归咎于当地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功能性部门中的缺陷,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仅仅是更大的社会综合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 曹玲
2008年入职的年轻记者,关注生物、太空、医学等领域,曾参与封面故事《国际红十字与新红月运动15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科学与权力的复合纠结——疫苗的安全问题》、《超级水果秀》等。 )
( 曹玲
2008年入职的年轻记者,关注生物、太空、医学等领域,曾参与封面故事《国际红十字与新红月运动15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科学与权力的复合纠结——疫苗的安全问题》、《超级水果秀》等。 )
其次,现代化进程既然可以量化分析,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可资借鉴的作用——中国如何自强?这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学生和青年最为关切的话题:依稀记得在当时的燕园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腋下夹着厚重的书本,也许另一只手还拎着搪瓷饭盒,却已经在宿舍,或者前往教室自习的道路上热切地讨论起来:国有企业改制到底向何处去?如何有效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复制?对于我来说,这些青春期喧闹的激昂声音和诸位先生的耐心教诲一样,一直是我对这个领域保持长久兴趣的最重要动力。
回想那段为期半个多月、几乎无休无眠的写作,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仅是自己的耐力与精力,更是各路来自身边与远方的支援:周刊同事俞力莎几乎变成了我在北大图书馆的资料搬运工——每隔几日我们就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在北大43楼研究生宿舍的门口集合,交换一包包沉重的书籍与资料,匆忙问候寒暄几句就迅速掉头各奔东西。还有美国马萨诸塞州开放源代码汽车制造公司Local Motors的公关专员菲蕾娜女士,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丹尼·罗迪克,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兰德公司成员约翰·阿圭拉,以及加拿大科幻小说家、独立媒体人科瑞·多克特洛,他们无一不是在接到了我匆忙写就的电子邮件和粗陋的采访提纲后,就在短时间内给予了尽可能充分的回复。他们的见解与阐述如同米诺斯迷宫中引路的宝贵线团,通常能让在资料之海中几乎溺毙的我感到绝处逢生——除去对方的慷慨好意,这也是信息时代提供的便利。正如我自己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津津乐道于信息通讯技术对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重塑一样,撰写这篇长文似乎是一次对于我大学所学专业倍加严酷的迟来测验,所幸互联网能够及时将所需资讯分门别类地送到我手上。
 ( 黄燕
2006年加入三联,从IT业转入商业报道领域,跨国公司在中国与中国品牌的生长是她关注的两大方向。试图在财经报道与三联风格之间找到结合点,长期跟踪报道宝洁、可口可乐、卡夫、百威英博、海尔、国美、苏宁等知名企业。 )
( 黄燕
2006年加入三联,从IT业转入商业报道领域,跨国公司在中国与中国品牌的生长是她关注的两大方向。试图在财经报道与三联风格之间找到结合点,长期跟踪报道宝洁、可口可乐、卡夫、百威英博、海尔、国美、苏宁等知名企业。 )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中国在这篇长文中所占据的分量几乎为零——工业革命至今的150年,也正是传统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中努力变革自身,试图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漫长探索时期。所幸在短短3月后,第589期封面故事《火烧圆明园150年祭》的撰写让我得偿所望:在解释1840年以降之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时,不分畛域地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为一切问题与失败的解释显然不妥,因为中国对于西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之反应,以其本身结构、组织与精英阶层之认知力,已经不可谓迟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等人已经在呼吁“制器”、“筹饷”,而1860年以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入京师,兴兵焚阙等较深的刺激,中国传统社会已由“洋务自强运动”作梯度式的应对: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甲午一役败于日本后,则企图通过“百日维新”从法制方面革新——修改宪法、废除科举,编列预算;然而维新之失败,以及庚子国变,使中国先进分子发现阻碍现代化之根本在于“君君,臣臣”之道与皇权,于是革命党人索性以手枪炸弹发难,以新军会党留学生为骨干建立民国,却仍然发现各种西方舶来先进制度与理念在民间缺乏对应基础,所以只好以新文化运动继之——直至今日,中国的长期现代化革命仍然任重道远,而我们的工作与责任,无疑也不会仅限于用手中之刀笔,做出忠实记录。周敦颐曾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在大规模信息碎片洪流时刻冲刷大众精神世界的今日,这种责任不仅显得艰巨,也更为必要与紧迫。■
 ( 李晶晶
原为央视财经记者,2007年进入三联后方始接触收藏行业,开始收藏栏目的采写,参与的封面故事有讲述古玩传奇的《平地崛起的一代》,《藏文化薪火之传——布达拉宫穿越千年的大修》、《龙泉窑 顾绣 紫砂壶等——传家宝》、《曹操墓的确认逻辑》等。 )
( 李晶晶
原为央视财经记者,2007年进入三联后方始接触收藏行业,开始收藏栏目的采写,参与的封面故事有讲述古玩传奇的《平地崛起的一代》,《藏文化薪火之传——布达拉宫穿越千年的大修》、《龙泉窑 顾绣 紫砂壶等——传家宝》、《曹操墓的确认逻辑》等。 )
 ( 上海世博园 ) 现代化理论理想国现代化世博会
( 上海世博园 ) 现代化理论理想国现代化世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