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馆,毛利的启示
作者:贾冬婷 ( 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效果图
)
( 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效果图
)
仪式
在世界起源之初,天空之父Rangi和大地之母Papa曾经紧密地靠在一起,没有一丝光亮可以穿过他们照亮世界。他们的孩子们,也就是众神,企图将Rangi和Papa分开,但只有森林、人类以及所有生物之神Tane做到了。他将双手支撑着大地Papa,用自己的双腿顶开了天空Rangi,创造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光明世界。
这一毛利人的创世神话便是世博会新西兰馆“自然之城:生活在天地之间”的灵感来源。新西兰馆总代表吉赋礼(Phillip Gibson)对本刊记者说,新西兰城市犹如Tane一样屹立在天地之间,大自然始终无处不在。86%的新西兰人口生活在城镇中,与大自然的紧密连接以及对可持续平衡的重视是新西兰人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核心理解。
距中国馆一步之遥,两片巨大的挑檐倾斜而出,其下由白色柱群支撑,映衬着玻璃墙内的草木葱茏。在吉赋礼眼里,新西兰馆的外形首先让他想到了一个毛利语词汇“Aotearoa”,它代表着毛利人最初来到新西兰时的印象——绵长的白云覆盖下的一片土地。“其实,新西兰的全名应该叫做‘Aotearoa NewZealand’。毛利人口述历史中,最早发现新西兰的毛利人是由南太平洋波利希尼亚群岛乘独木舟劈波斩浪而来的库普。当他们看到远方白云之下的一个大岛屿时,库普的妻子希内·蒂·阿帕拉尼脱口叫道,‘白云!绵延的白云(Aotearoa)!’”在他看来,新西兰馆建筑中包含了所有新西兰文化、景象、人文等重要元素,比如挑檐代表天空之父Rangi,广场则是大地之母Papa,白色支撑柱代表高耸的森林,森林中矗立着毛利图腾柱Pou。
“当游客走出中国馆,会被不远处的音乐吸引,你会看到一群毛利人跳着充满活力的毛利战舞哈卡(Kapa Haka)。”吉赋礼说,这种舞蹈看上去很有震慑力:他们的身体一点点地向后挺,击打双膝,看起来像在抽搐。他们双眼圆睁,面部表情狰狞,并把眼球藏在眼皮下,同时双手举在面前,手指极力向外伸,不停地在脸前晃动。最著名的哈卡当属讲述毛利酋长Te Rauparaha故事的Ka Mate:酋长曾被敌对部落掳获,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后来却成功地逃脱了。Ka Mate把他被捕时的恐惧和逃脱后的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哈卡在新西兰当今社会仍充满活力,它是自1888年以来著名的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全黑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象征。在每一场关键的比赛开场前,队员们将哈卡演绎得激情四射,调动全场热情使对方阵脚大乱。

吉赋礼介绍,进馆时的哈卡是要传达一个新西兰的核心理念Manaaki-tanga,即毛利的迎宾之道。这一完整的仪式以“挑战”为序幕。由主人一方的勇士手持长矛,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通常是一段小树枝)放到地上,客人应将树枝捡起,以示自己为和平而来,不抱任何敌意,至此都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第一个声音是“呼叫”,目的是织出一条抽象的绳子,在精神上围着来宾,并开出一条安全的通道,引领客人进入毛利战神的领域。之后主方开始跳哈卡,以拉动客方的精神上的独木舟进入会堂,并借此舞蹈来显耀主方的会堂、部族、部落分支及祖先的威望。会堂是毛利人社交、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核心,是一个将毛利族价值观和哲学重复肯定的地方。在这里,主方向客人演说,以此向创造者、监护人、死者及生者致意,借此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起来。每一位演说者演说之后都会出现吟唱环节,向演说者的宗族谱或团体本身致意。所有演说完成后,客方的最后一个演说者放下礼物,主客双方正式开始接触。传统上,礼物是毛利人认为贵重的物品──绿玉石、鲸骨、斗篷等,多寡轻重显示来客的威望和聚会的重要性。客人在向主人行以碰鼻礼仪后,宴会开始,仪式的庄严神圣气氛会随着分享食物而消失。
正如绿玉在毛利迎宾之道中的作用,一块重达1.8吨的绿玉(Pounamu)也将作为新西兰馆的镇馆之宝。吉赋礼透露,这块玉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绿玉石,大约是中型会议桌的大小。新西兰的玉石不如中国的玉石通透,但整块玉呈墨绿色,在潺潺的流水下闪现出沉静光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在毛利文化中,玉不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还隐含着对坚忍品质的称颂。大部分的绿玉都产于新西兰南岛的毛利部落所辖地,最早被毛利人用于制作工具。在VIP区域,还将展出一块来自奥塔哥博物馆的毛利传世美玉。这块名叫Heitik的玉高16厘米,宽9.6厘米,毛利部落的能工巧匠用鲍鱼贝壳制作双眼,雕琢出一个盘腿而坐的毛利人,头微翘,做若有所思状。它来自毛利人三大部落之一Kai Tahu,是当地部落酋长代代相传的玉挂坠。为了与这块毛利玉相呼应,上海博物馆挑选出一块5000年历史的玉琮,高21.6厘米,宽7.3厘米,呈方柱状,内圆外方,表面复刻人面图纹。它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器物,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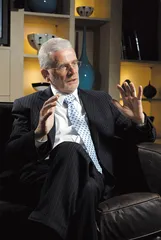 ( 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总代表吉赋礼
)
( 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总代表吉赋礼
)
“对于外界来说,秀丽壮美的自然风光,独一无二的动植物是大家对新西兰的印象,但对新西兰人来说,毛利文化才是新西兰的根基。”吉赋礼说。
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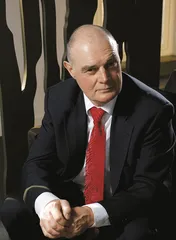 ( 负责新西兰馆展示设计的Story Inc总监迪安 )
( 负责新西兰馆展示设计的Story Inc总监迪安 )
负责新西兰馆展示设计的Story Inc总监迪安(Dean Cato)每天佩戴着一块毛利绿玉。他向本刊记者展示,这块玉状如一个剑柄,并无任何装饰或雕琢。它对迪安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与新西兰土地的一种关联。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新西兰是世界上刺青最多的国家。迪安说,这一毛利传统不仅存在于毛利族群内,目前在新西兰更广泛的人群中是一种风尚,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传统的毛利文身通常刺在面上,其目的和用途都是十分神圣的。对毛利人来说,刺青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项历史记录。每个刺青都对受刺人本身有特殊意义,含有其祖先或部族的讯息,家庭与部族的关联,以及在此等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为什么人口仅占14%的毛利人对于新西兰社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迪安说,这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复兴运动。新西兰想与英国殖民者做一个切割,切割后的国家特性是什么?不同族群的移民都在寻找。与此同时,毛利人开始积极争取索回其部族的土地,并争取保护其语言、艺术和文化的机会。这些由波利尼西亚而来的开拓者经过了1000多年在新西兰的生存经验,逐渐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思维和信仰,与其他各群岛而来的移民信仰暗合。于是,在共同的寻根过程中毛利文化逐渐融入当今社会,最终成为新西兰的精神根基。
毛利文化是一种充满故事和传说的口头文化。作为新大陆上最早的登陆者,毛利人拥有对历史的优先诠释权。这片新大陆分南北两个岛屿。毛利神话中,是半人半神的英雄毛伊将北岛从海中钓起。在地图上看,北岛很像一条鱼,被称之为毛伊之鱼。毛伊的哥哥们迫不及待地动手“切鱼”,之后便成了北岛的山谷、山脉、湖泊和岩石耸立的海岸线。至今仍有许多地名都与毛伊传说有关,如南岛被命名为毛伊战船,斯图尔特岛被命名为毛伊锚石。
虽然新西兰并非像条大鱼一样被人从海中钓起,但它的确是地球上最后一块被发现的主要大陆,因此成为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度。
在毛利人到达800年后的1769年,库克船长环游新西兰一周,欧洲移民开始进入。最早的欧洲移民是捕鲸人和传教士。在1840年签署《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新西兰人口开始大量增长。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南岛淘金潮则带来更多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包括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中国人,形成新西兰的多种族社会。
打造了《指环王》国际巡回展的迪安介绍,此次世博新西兰馆展示想传达的独特一点是,新西兰由多元化、多种族人共同创造,这刚好与毛利人创世的故事相符合,因此成为新西兰馆的主线。游客们从分开天空和大地的Tane双臂间穿过,进入“一个新西兰家庭的一天”。按照时间顺序,旅行从拂晓开始,在黄昏结束,历经春夏秋冬,纵览从海洋到高山,以及市郊和城市的各种风景。
故事始于一个小女孩的梦。“当奥克兰海港的晨曦照进卧室,小女孩正梦到天空之父Rangi和大地之母Papa。当游客们漫步到下一站时,呈现眼前的是小女孩的妈妈正在海边的家中做早饭、沙滩上很多新西兰人正在玩耍的景象。之后,小女孩在市郊的学校中描画自己的梦境。顺着通道继续往前,将会来到新西兰各个城市的中心,这里也是包括女孩父亲在内很多新西兰人工作的地方。最后一站是在山坡上的一栋房子,在那里,女孩正向她的父母和祖父母展示她画笔下的毛利创世神话。
一个家庭的故事将新西兰特有的城市生活串联起来,而且,这一家庭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种族。迪安说,这在新西兰是很普遍的,比如他的祖先是由苏格兰而来。那是在1800年左右,大量苏格兰移民涌入新西兰,尤其是南岛的奥塔哥地区和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风笛、苏格兰乡村舞蹈和滚球运动由苏格兰人带来,现在已成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过了好几代,这些移民开始在当地寻找新的关联,并找到了最原始的毛利文化。
每7分钟,模拟雷暴就会掠过整个展馆,而黑夜也会转为白天,再次周而复始。迪安说,这也符合毛利人顺应和守护自然的基本法则。
迪安说,毛利人按部落、小部落、山脉和河流将自己归类。他们与土地有着强烈的精神联系,认为土地、土壤和水都是“宝物”(taonga),视自己为这项宝物的监护人,因为土地是当地人民的团结力量之源和身份依归。因此,失去祖先的土地对毛利人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自1987年起,新西兰政府接受及处理被英国殖民政府没收土地的索偿。新西兰四周环海,所以毛利人与海洋也有天然的联系。从划探险舟而来的口述历史至今,他们都是能干的渔夫,而且会遵从钓鱼的惯例。按惯例,捕获的海产是不可交易或出售的。
吉赋礼介绍,在《怀唐伊条约》的基础上,今日的政策制定者进一步照顾毛利人的期望,并刻意介入以保持毛利文化的生命力。毛利语现为新西兰官方语言之一,在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学生有权选择以毛利语、英语或这两种语言混合教授。最近的典型案例是政府在北岛修建公路时,为避免惊扰水神而修改了施工方案。按最初的施工方案,公路将穿过一片沼泽地。此片沼泽地是独眼水神卡鲁大希的居所。当地毛利部落纳蒂纳霍认为,水神卡鲁大希有半年时间居住在此片沼泽地。在洪水季节则游到怀卡托河,在那里住半年。为保证此片沼泽地不受干扰,新西兰道路管理局最终修改了施工计划,保留了这片沼泽地。
守护
倾斜而下的屋顶花园为设计师金姆(Kim Jarrett)和蒂娜(Tina Hart)提供了“从高山到大海”的自然联想。这对夫妻档擅长花园和景观造型,金姆曾担任电影《金刚》的绿色植物布景大师,为这部在惠灵顿拍摄、新西兰人彼得·杰克逊执导的电影设计了史前丛林、沼泽以及海岸景观。他们对本刊记者说,独一无二的屋顶花园是对新西兰自然地理的模拟:冰河、峡湾、山脉、平原、亚热带雨林、火山高原、漫长的海岸线与诸多绵延数英里长的靓丽海滩在此会聚,而且彼此之间近在咫尺。“在一些地方,可以早上在山顶滑雪,下午在海里冲浪。在众多火山地带,眼前是牧场,推开窗就是海。这也是我们在屋顶花园中设立牧场的原因。”
迪安对本刊记者说,为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打造全球巡展时,他们试过很多不同的展示方式,最后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入手,让观众感觉这故事在现实世界发生过。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新西兰地理风貌中的魔幻效果。彼得·杰克逊的童年是在惠灵顿北部的普克乌阿·贝(Pukerua Bay)小镇度过的。他从小就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痴迷于幻想。或许那时候他就把亦真亦幻的家乡风景想象成霍比特人的“中土世界”,之后又把这一想象带给全世界。
金姆和蒂娜的花园故事也沿着毛利人的创世神话展开。当游客们从黑暗的内部展厅走出,进入到光明的屋顶花园时,象征着进入了分开Rangi和Papa的Tane的光明世界。蜿蜒的步道将花园分为六大区域,由“迎宾”、“欢送”和等六大守护神(Kaitiaki)负责守卫。金姆说,Kaitiaki传达着毛利文化中的一大核心理念Kaitiakitanga,即护卫环境。
一首著名的诗歌表达了这一人与自然的契约,金姆将它刻在花园的墙上:“砍断生长在灌木丛上的嫩枝……对鸟儿意味着什么?无论你是来自陆地或是来自海洋,如果你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肯定是人,人,还是人……”金姆说,诗中的灌木是新西兰特有的亚麻灌木,将运到世博花园中种植,其纤维质用在渔网、篮子、斗篷和其他织物上,种子有药用价值。诗中的鸟是一种铃鸟,以亚麻花的花蜜和种子为食,有动听的嗓音。当人们在花园中参观时,会听到铃鸟的歌唱。
屋顶花园步道的起始点是冈瓦纳古大陆(Gondwanaland),这是Rangi和Papa在拂晓时的分离创造的第一块大陆。设计团队专程从新西兰运来银蕨(Ponga)对该区域进行装饰。在毛利传说之中,银蕨原本是在海洋里居住的,其后被邀请来到新西兰的森林里生活,指引毛利族的人民。只要将其叶子翻过来,银色的一面便会反射星月的光辉,照亮穿越森林的路径,因此从前的毛利猎人和战士都是靠银蕨的银闪闪的树叶背面来认路回家的。新西兰人认为银蕨能够体现新西兰的民族精神,故此这种植物便成了新西兰的独特标志和荣誉代表。
之后游客将经过Korokoro热湖,该湖常见于新西兰北岛的Rotorua地区,薄雾、水汽和气泡将在热湖中营造出水面不断沸腾的效果。根据毛利人的神话,这是Rangi和Papa最小的儿子,地狱之神Ruaumoko的喉咙(korokoro)。漫步在小径中,游客将看到树蕨丛生的森林峡谷,其中有一个多节瘤的巨大树桩,名叫Kuia树,一些毛利人称其为Puwhakahara(Tane的妻子)。森林山谷之后,小径两侧是两片牧场,着重展现新西兰的畜牧业和农业。其后,游客将进入南太平洋动植物保护区。通道上覆盖着毛利编织技巧织出的植物藤架,两边设有水景和亚热带植物,突出了新西兰人喜欢在花园中融入的南太平洋风情。
屋顶花园斜坡步道的终点是沿海地区,一棵高大的Pohutukawa树在步道的尽头欢送游客。Pohutukawa会在12月开花,正值新西兰的夏季,因满树艳丽的红色花朵被称为新西兰的圣诞树。因新西兰地理上的隔绝,花园中60%的物种都是新西兰特有的。也就是说,只能在新西兰土地上栽种,将它们移植到上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如Pohutukawa,让金姆遗憾的是,这么大尺寸的树要入境,除非确认它已经死亡。最后他们只好在新西兰制作一棵人工树运到上海,象征一棵400年树龄的Pohutukawa。
金姆和蒂娜说,像电影《阿凡达》中的灵魂树一样,Pohutukawa在毛利文化中被称作“生命之树”。它贯穿人的生死,它是出生时看到的第一棵树,也是死亡时看到的最后一棵树。1000年前,第一批毛利人到达北岛时,它是旅途中出现的第一批风景之一,如今,它还在那里。■
(文 / 贾冬婷) 启示毛利新西兰生活新西兰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