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生姐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彭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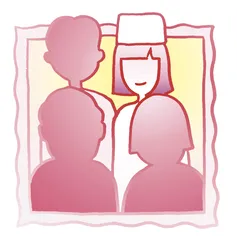
我姐姐选择学医是万般不情愿的,尤其是被发送到酷热的长沙。之所以是长沙,除了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的湖南医科大学(现在又改回叫湘雅了),更多地寄托了爸爸对家乡的怀念。
5年的学习让我姐姐痛苦不堪。好容易熬到了毕业,姐姐对于她即将开始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恐惧。医院狭窄的空间、嘈杂的环境,病人痛苦的呻吟,期待的或者绝望的眼神,都让她觉得难以承受。可是对于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做医生又去做什么呢?何况医生是一个看起来很体面、很适合女孩子的工作。于是在简单的挣扎后,我姐姐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医生。
医生的生活是复杂的(他们自己认为是有序的)。光是他们的排班,我已然搞不懂,一会儿是白班、夜班,一会儿是大白班、中班;一日在门诊,一日在病房,一日在急诊。我几乎从来没有通过她们办公室的电话准确地找到过她。医生无疑是忙碌的,我不知道我姐姐平均每天看多少病人、写多少病历和报告,只记得她说过,体检时一天要检查一两百人。
在“看病难”已成一个社会现象之中国,家中有个医生简直是个宝。我经常和我姐姐开玩笑说:牺牲你一个,幸福全家人。老妈生病住院那次,多亏了她,老妈才能及时地住进医院做上手术;多亏了她,老妈才不用拖着病体在迷宫一样的医院里的各个科室之间奔波;多亏了她,老妈才能用上最便宜却最有效的青霉素而不是有着华丽包装和拗口名字的进口药;更是多亏了她,老妈得以获得主任对待病人那关切的眼神、难能的微笑。
不过我姐姐在家总被我们戏称为“蒙古大夫”。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老爸的耳聋。一年前,发现老爸耳背了,经我姐姐咨询他们耳鼻喉科的主任,断定老爸是神经性耳聋。神经性耳聋是退行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渐进,治不好的,姐姐解释道。于是,在倒笔画、不会汉语拼音、记不住人名、分不清“黄王房”诸多毛病之外,老爸又多了个被老妈取笑的缺点。
夏天的时候,老爸来看我。一日游泳回来,发现老爸聋得更厉害了,而且老爸自觉耳朵里有胀痛感。到左近的医院,医生看了看老爸和他的耳朵,说:看老爷子身体和精神这么好,哪至于就得了神经性耳聋,多半是耳垢堵住了。回去点些药水,耳垢软化后掏出来就好了。回去遵医嘱,老爸的耳聋迅速治好了。想我那可怜的老爸被我那庸医姐姐害得受了一年多耳聋之苦。
姐姐怀孕时,预产期前两周,发现胎儿心跳不正常,一分钟200多次。被要求立即住院,时时监控。姐姐慌了神,问了产科的主任还不放心,又去找返聘回来的老主任。结果,两个主任的意见不一样,一个说她的状态很危险,得立刻做剖宫产手术;一个说,她的孩子还太小,可以再等等。最后,两个主任都说,你也是医生,道理你都明白,你自己决定吧。这一下,她更没了主意。“心跳过速就说明胎儿可能缺氧,造成缺氧的原因有很多,也许是脐带绕颈勒着胎儿了,也许是……也许是……缺氧会造成胎儿大脑损伤……虽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医疗设施这么先进,可毕竟‘肚里货说不透’……什么可能都有……”姐姐在电话里跟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剖!我决定剖了!”经过了一昼夜的思想斗争,姐姐做出了决定,“你想,怀孕时最担心的莫过于孩子有缺陷、不健康,要是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的却因错误的判断没有采取措施而导致不良的后果,我可实在承受不起!”姐姐后来告诉我,她的主刀医生、主刀医生的助手、麻醉师都是剖宫产,还有她的许多医生同事。虽然没做过统计,但我想剖宫产的比例在医生这个特定人群中一定是最高的。所谓无知者无畏,医生们知道太多的可能,看到太多不可能发生的事的发生,在对待他们自己和亲人时,他们最脆弱,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不愿承受那些不确定。
最近,她刚刚“下乡”回来。“下乡”是他们对为期半年到一年、去省内县医院支援或者锻炼的俗称。我总觉得这个称呼体现着他们高高在上的感觉,并透露出诸多的不情愿。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把去北京或者上海医院、同样为期半年到一年的支援,称为“进修”。此时他们又显得很谦逊,一派向往的样子。县城与省会相比确实是乡下,县医院的条件和省立医院相比也相去甚远。姐姐她们一行5人,分别来自骨科、脑外科、内科、放射科、儿科。县城离家2小时车程,开始时,他们每周日晚上去,周五晚上回来,可慢慢地就变成周一早上才出发,周四晚上就回来了。姐姐说待在那边没事情做,医院的病人不多,又缺乏机器设备,很多检查、手术都做不了。“哎,现在的医生啊,离开了机器设备就什么都做不了,真不知道当年的那些赤脚医生是怎样医好病人的。”妈妈听了她的话,不尽感慨。他们的下乡锻炼,成了一个走过场,县医院没有得到实际的帮扶,他们也没有得到锻炼。县医院倒宁肯卫生厅把这笔经费直接发放到院里,而不是派这些无用的医生来。
“下乡”回来,搬到新的门诊大楼,姐姐比以前更忙了。门诊、病房、医生、护士的增加速度似乎永远赶不上病人增加的速度,医院里永远都是人声鼎沸、人满为患。终于等到午休时间,疲惫的医生们或倚或靠在椅子上,漫谈着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医生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