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 议案大王张仲礼
作者:魏一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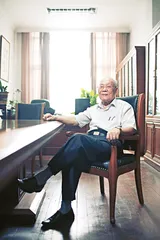
( 张仲礼 1920年4月生于上海。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7年初进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主研中国绅士问题和太平天国史。1958年底回国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1984至1998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
学以报国
9月15日,周二。这天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研究生教育30周年纪念大会在位于淮海中路的大楼里召开,已经89岁的老院长张仲礼自然是会上会下最引人注目的长者。这天,华盛顿大学副校长专程赶来拜访,激动地称他是“华盛顿大学的骄傲”。
就是在华盛顿大学,张仲礼奠定了其一生的学术地位。1955年,列有247种参考书目的《中国绅士》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张仲礼潜心研究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的代表作。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在其导言中如此评价:“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它带给张仲礼的学术声誉持续之久,以至于此后的数十年里,很多研究中国的欧美学者来到上海,都会专门打听起这本著作的作者下落如何。当他们得知眼前这个接待自己的老者正是张仲礼后,都会兴奋地说,“我读过你的书”。
半个世纪前,张仲礼离开华盛顿大学返回祖国,当时,不满40岁的他已经担任了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每月750美元的工资,为了挽留我,学校破格给了终身教授的称号”。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回忆起这些,平淡的语气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1958年12月,张仲礼在阔别祖国12年后踏上了归程。
中学就读于英国工部局兴办的育才中学,大学又是美国人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张仲礼的学生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虽然教学质量很高,但越是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就越会激发报国之志”。直至今天,回忆起儿时时光,中学时的一堂作文课仍是张老最深的记忆。当时,有位同学的作文写到纪念“五卅运动”,被英国老师当场撕下,这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愤慨,一直把状告到校长那里,最终以老师道歉并归还作文结束。“所以,1947年通过国民党政府的留学考试时,我就想将来学成一定要回来。”
 ( 1995年2月,张仲礼(右一)在准备当年提出的《关于建议制定宏观调控的基本法》等议案 )
( 1995年2月,张仲礼(右一)在准备当年提出的《关于建议制定宏观调控的基本法》等议案 )
上世纪50年代,国内政治时有波动,但张仲礼并不担心,“学以报国是我从小的理想”。他清晰地记得,当年转道香港抵达深圳时,国务院已经派人在口岸迎接,采访此事的美国记者给自己报道所起的标题是《中国教授回到红色中国》。由于早就听说当年钱学森辗转回国途中被美国当局扣押于夏威夷,没收了他随身携带的所有研究资料。张仲礼痛下决心,把自己做论文时攒的几抽屉卡片都留在了美国,行李只有一台巨大的美式冰箱和几把椅子。
回国后的条件并不如愿,张仲礼也无怨言。“文革”中被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开荒的张仲礼很快迎来了曙光。1971年底,中美关系面临突破,中方急需加大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了解,张仲礼等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翻译。“别人一般每天翻译2000字,我那时候每天能翻5000字。”他说起这些时一脸的认真,靠着曾有在华盛顿大学任中国文献翻译组组长的经历,张仲礼很快就成为翻译队伍中的骨干。1974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基辛格》一书,成为当时中方谈判组几乎人手一册的法宝,它的译者署名为“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
虽然当时还不是党员,年复一年的翻译也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张仲礼仍对这段日子心怀感激:“说明组织上开始重用我了,学的东西派上了用场,未来有希望了。”果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张仲礼回到上海社科院,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他的职务看起来仍没有多少起色——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主任,但接踵而至的3件大事还是让他兴奋不已:1979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劳模,成为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第一个获得奖励者;1980年,他经丁日初等经济学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卢湾区人大代表。
副所长、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此后的6年,张仲礼的升迁之快甚至让他自己都有点惊讶,“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出来,经济研究开始成为最炙手可热的领域,这正是我的老本行”。1983年,张仲礼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议案大王
真正进入到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跟许多人一样,张仲礼最初几年对“全国人大代表”的理解也不过“只是一种荣誉感,跟着大伙出去视察,走走看看”。直到1987年,第六届人大任职的最后一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认识。
当年,张仲礼正式出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做院长,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职称评定,1980年,中央组织评过一次研究员,此后就只能等待,一直没有建立起定时评定的长效制度。”张仲礼对本刊回忆道,“由于研究员评审的年龄上限是60岁,院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如果错过了一次评定,基本就没有希望了。”这已经是他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第五个年头了,“以前只知道议案一般是组织提出来,个人附议一下,要真的自己提议案,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在同事的鼓励下,他开始查阅、咨询、汇总各方意见,最终带着一份《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登上了北去的飞机,在上海团代表中凑足了30个签名。按照人大制度规定,代表个人提出议案需至少30人联名提交。
就是这个看起来是“被逼出来”的议案,开启了张仲礼“议案大王”的传奇。4个月后,他收到全国人大的回复,他的议案被确定为当年的1号议案,职称评定“制度化”的建议很快被国务院有关部门采纳并在全国推行。张仲礼开始意识到:“原来人大代表只要认真履行职责,还是真管用的啊。”
1988年,张仲礼顺利连任,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次,他就有些坐不住了,赶在人代会开会前两个多月,就开始忙着调研、汇总信息,拟定议案。当时上海社科院有一位老干部,同时参加了上海老年学会,便向张仲礼提出,希望国家专门立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出所料,这年,张仲礼带到北京的《关于制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再次被列为1号议案。“虽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直到1996年才通过,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点推动作用,我已经知足了。”这是张仲礼最大的欣慰。20年间他所提交的61件议案或早或晚都得到了答复,其中许多已由国家专门立法。
从1987年到1990年,连续4年,张仲礼所提的议案都被列为当年的人大1号议案,“议案大王”的称号由此而来。“到了1991年,我发现有个江苏团的人大代表跑得比我还快,我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证券法议案只列到了第8号和第9号。”每到人代会召开的时候,似乎1号议案非张仲礼莫属。说起这些,张仲礼略显不好意思起来,毕竟,那时候的1号议案更多还是按照上交的时间顺序来排定的。
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张仲礼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80年代时去北京开会,代表们讨论议案的并不多见,到了90年代,开会期间大伙都忙活起来了,互相找人签名的多了起来,要不是在飞机上就签好名,到了北京就落后了。”曾担任院长助理的顾肖荣向本刊记者介绍,每年的11月份,张仲礼就会开始着手准备第二年人代会上的议案,依托上海社科院的资源优势,先由法学所、经济所等机构拟定出当下最紧迫的几个议题,交由张仲礼与同仁们反复讨论后进行筛选和补充,“他总是亲自改正完善,手写完之后交给我们继续讨论”。顾肖荣对他那份知识分子般的严谨记忆深刻,“只要是有关基层群众的议案,他都要亲自到社区、工厂、菜场调研”。
他把人大代表的职责延伸到了一年365天里,街道办、居委会、菜市场,都成为他搜集社会热点问题的工作点。1993年他提出的“专有技术法”、1996年提出的“保税区管理法”、1999年提出的“国家反腐败法”、2000年提出的“电子商务法”又先后被列为当年的1号议案。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张仲礼最后一年参加人代会,时年82岁的他成为当时最年长的人大代表,一口气提交了10个议案。“议案大王”又回来了。
智库之宝
9月的上海,工地上发出的噪音更增添了几分燥热,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只剩200多天,各项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早在1999年上海正式提出申办世博会之前,申办世博的想法就在张仲礼脑子里酝酿了长达十几年。1982年,张仲礼应邀回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让他吃惊的是,与30年前自己在此求学时相比,西雅图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人口从二十几万猛增到200万,市区面积扩大数倍,不仅吸引了波音公司等大企业,还成为全美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后来,张仲礼才知道,原来这些都得益于1962年西雅图承办的世博会。一次盛会,超越城市空间的意义,自此引起了张仲礼的关注。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社科院开始积极介入世博会研究。
“智库之宝”,是2008年出版的张仲礼传记对他的称呼。传记的作者之一——上海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王泠一博士向本刊记者坦言:“早期的绅士研究奠定学术地位,后来的人大代表是社会职责。其实,在这之外,在上海社科院做过11年院长、工作超过50年的张仲礼,最切实的贡献还是他作为高层智库及时提出来的3个议题——开发浦东、申办世博、“长三角”一体化。”
从学者到智库,虽非刻意而为,却也并不超出张仲礼的追求。据他回忆,早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的时候,每逢有杜鲁门总统、肯尼迪参议员等要人前去演讲,他这个研究晚清绅士的中国学生都会跑去听听。当时,学校图书馆里有一份由华人主办的《华侨日报》,不管是放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都能找得到,他说:“朝鲜战争后,中美通信中断,只能通过这个了解中国。”
1984年,刚刚上任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张仲礼,很快接到了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一起外出考察的邀请,去巴基斯坦出席上海与卡拉奇友好城市的缔结仪式。在张仲礼回忆中,也正是这次形影不离的出访,让他走进了上海高层的视野。
从卡拉奇刚刚回到上海不久,张仲礼就接到了汪道涵分派的第一个正式任务——接待前来上海考察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学家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与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带队,智囊团包括了薛暮桥等著名经济学家。“当时,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讨论很热烈,也就是在这次讨论中,我们率先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设想。”张仲礼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我们坚持认为在此基础上新建一个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张仲礼所带领的上海社科院摆脱了以前“大讨论”的角色,开始直接为政府绘制发展草图,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此后几年,张仲礼组织社科院的研究力量为浦东开发做了大量准备,待到1990年李鹏总理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时,基本框架已经奠定。后来,就浦东的开发模式、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重大问题提出建议,成为张仲礼和他的团队的工作内容之一。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城市研究系列,从上海的单个城市研究到沿海、沿长江流域城市研究,再到内陆城市研究,正是这种对外交流、团队合作的典范,长三角一体化也由此而推动。
显然,相比普通人大代表,张仲礼拥有更为便捷和高端的参政议政通道。“汪道涵、江泽民、吴邦国等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都很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之间有一些交流。”说起与高层领导的交往,张仲礼略显谨慎,也为他的智库角色增添了几分神秘感。1989年“两会”期间,尚未到中央任职的江泽民,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了张仲礼所提有关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1号议案。晚上22点多,正要睡觉的张仲礼接到了江泽民秘书的电话,说首长想了解议案内容。他起身,将议案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对方记录。20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些,仍是整个采访中最让张仲礼感到兴奋的一刻。
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仍坚持每周到社科院上班两天,亲自布置、讨论学术事宜。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自己亲自去菜市场买菜的习惯,只为了这样能“了解民情”。回答每个问题之前,他总要习惯性地思考片刻,严谨的表述一如他的论文。表面看起来像个文弱的书生,但老人骨子里却有着另一番天地,“我总相信知识可以报国”。他提着满满一袋子书独自缓缓下楼,拒绝任何人的搀扶。 张仲礼华盛顿大学议案社科院大学上海时政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