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米奇·阿尔博姆 )
(
米奇·阿尔博姆 )
10年前,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凭纪实作品《相约星期二》,从一名体育专栏作者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书中记录的是他和大学老师莫里·施瓦茨的谈话。他偶然在电视上见到他,接下来的14个星期二持之不懈地拜访,与之长谈,看着身患绝症的莫里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不失尊严地死去。他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付出版,曾经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最终这本书从第一版的3万册,一直重印了200多版次,在全球销售1500万册,成了美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大多数智者避开谈论人生,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有时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谈论价值自然不会很高。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过自己的生活,少对人生高谈阔论。但是,谁都想听听别人怎么说。莫里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为什么他对人生的思考可以撩拨许多人的心?阿尔博姆说:“因为他的故事不是社会学教授对自己一生功过的总结,他首先是个老人,而且是一个时日无多的老人讲如何看待生死,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故事联想到自己。”
几年间,阿尔博姆出版的另外两本书都与生和死有关。《你在天堂里遇到的五个人》讲一个叫爱迪的瘸腿男人,为救一个孩子失去了生命。他在天堂遇见了5个人,天堂并不令人乐不思蜀,但他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地图,终于看明白自己一生的道路原来是那样勾连。《一日重生》的主人公凡事不顺遂,但在和已去世的妈妈的灵魂重逢后,岁月翻然改变。在去世前的一星期,他心满意足地对别人说:“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那个点石成金的转折点就是书中描绘的重逢之日。这其中根本的差别,阿尔博姆在采访中给出了解答。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为什么来中国?
阿尔博姆:看奥运会。我看了美国男篮的比赛,以及游泳、体操和摔跤。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体育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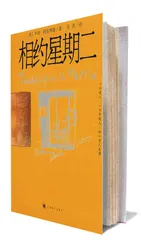 (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 )
(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 )
三联生活周刊:你去看开幕式了么?
阿尔博姆:看了,非常辉煌……
 ( 《你在天堂里遇到的五个人》的中文版 )
( 《你在天堂里遇到的五个人》的中文版 )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传里有一句话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你年轻时,曾经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个酒吧演出?
阿尔博姆:我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当个作家,我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大学毕业后,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去欧洲游历,一个偶然机会来到雅典,在那里等着转机去别的地方。30年前不像现在每天都有飞机去往各地,我等的那班飞机在3天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克里特岛上的一个酒吧招聘钢琴手,我觉得有意思,就去面试。一个女人问了我唯一一个问题:“你喝酒吗?”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看我有没有酗酒的习惯,我说没有,于是她给我写了个纸条,我拿着纸条在机场得到一张去克里特的机票。我在克里特岛的一个酒店弹了一小时的钢琴,就有人把我带到一个酒吧,酒吧里有个乐队,他们问我:“你能唱摇滚吗?”我说还成,于是就给他们唱了首“猫王”的《蓝色小山羊皮鞋》,把他们都给震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岛上听过美国摇滚的现场。我留了下来,一直待了7个月。现在回想,那真是一段激情四溢的生活。30年前,生活似乎到处充满奇迹。我正计划明年夏天再回去一趟,重新得到那份工作,起码做上1个月,可能写本书。我还留着那时候录的一卷磁带,我想把它转成DVD附在书上。
 ( 《一日重生》的中文版 )
( 《一日重生》的中文版 )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你的成名作和后来的几本书都在探讨生死?
阿尔博姆: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莫里·施瓦茨很喜欢我,我毕业时他跟我说,记得回来看我啊。我答应得好好的,但是一毕业就忙东忙西,做乐手,做记者,做电视工作者,生活越来越主流,却从来没回去看过他,甚至连电话也没打过。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视里看到老莫里,他正在讲述他由于得了绝症,对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的感受。那时我大学毕业已经16年了,才又重新看到他的脸,心里觉得很愧疚。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还记得我,说:“你怎么不叫我教练了?”我回去看他,他身上有一股沉静的力量很吸引我,使得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么多年我忙忙叨叨的,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我在许多个周二都从底特律飞过去看他,我们聊了很多,当一个人临死时怎么看待人生,他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无常,我们应该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计划生活,问一问自己什么是最值得做的,不会让自己在临终时后悔。当你理解了死亡,你会让每一天变得有意义。人生就是一条单行道,它的终点就是死亡,很多人看不到这个终点,看到的是无尽的欲望,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没有人相信其实不必那么忙。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有句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似乎不这么想就会觉得愧疚,为什么会这样呢?
阿尔博姆:《相约星期二》写完的时候被很多出版社拒绝,但为莫里支付医药费的初衷,让我多了份执著,少了些胆怯,可能这后面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给我力量。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毕业后,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所有事,老师只存在于求学阶段,现在是我们站在舞台的中心表演,不再需要任何人教我,至少很多美国人会这么想。其实不会改变的关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回去看望莫里的过程让我发现,人生始终需要老师。尽管他越来越虚弱,却仍然保持着睿智和风趣,这证明了他是一个终生的教师,这是他曾经的愿望。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再是具体哪门知识,而是生活本身。陪伴一个人走向死亡是很奇特的经历,他说的话、关心的事、对待过去的态度和平常人有所不同,而你可能在临终前很早就得到了这些经验。这样的一个人也会哭,会害怕,给了我很多不同层面的感受。我一直相信,我们永远可以从年长的人身上学到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下一步做什么?
阿尔博姆:我明年出版的书是关于“信念”的。我的家庭信犹太教,当我还是小孩时,就认识了那位拉比,他为我们家所有成员主持宗教仪式。大约8年前,我回老家做演讲,他问是否可以帮个忙,他说希望在他去世后,由我来主持他的葬礼。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做这件事,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从小他在我眼里一直是高高在上。我告诉他,除非我很了解你,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了解你,因为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将是来总结他一生的人。于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就像对莫里那样,我经常去拜访他。我们的对话讲到人为什么需要信仰,为什么当我们拥有很多智慧、知识和科技的时候,仍然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以后,我还想拍电影,反正还有那么多年要活,我不想一成不变地做个作家。我觉得在20年内,人们可能不再读书了,我是说人们可能用另一种形式接受书本传达的信息。未来的作家不仅要会讲故事,可能还要想如何把他们视觉化,我很想尝试别的讲故事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上过好几次“奥普拉·温弗里秀”,是她特别喜欢你,还是你的经纪人公关能力特强?但你的书在中国目前好像没有制造出版奇迹。
阿尔博姆:你不能对温弗里使用公关,如果你自己要求上她的节目,可能就上不了。我听说不知道谁给了她一本《相约星期二》,于是她邀请我上了5分钟的节目,后来她做了同名电影的制片人。不知道在中国都有谁看我的书,老人还是年轻人?我想我的书可能在中国不会有太多读者,大家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且这里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从香港地区打来的电话,一个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说要来美国采访我,我说好,于是他们就从香港飞来底特律。一见面,女记者直道歉,说对不起头发太脏,衣服也没换,因为在机场丢了行李,唯一没丢的就是照相设备,我老婆给他们找了些洗漱用品和换洗的衣服,我说你们何苦那么远跑来,他们说:“你真不知道么?你是香港地区头号畅销书的美国作家。”■(文 / 苌苌) 为师终生一日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