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与收藏家的画
作者:李晶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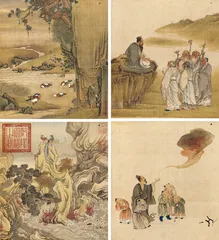 ( 丁关鹏《群仙献寿》册
)
( 丁关鹏《群仙献寿》册
)
1999年,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以101万港元的价格,拍得一张明代项元汴的《竹菊图》。这幅画作曾为张学良先生旧藏,钤有张学良鉴藏印,并收录《石渠宝笈三编》,钤有乾隆、嘉庆御玺,著录见于《南画大成》、《中国名画宝鉴》、《宋元明清名画大观》、《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宝鉴》、《历代著录画目》等10多部著作中。今年,翰海春拍,《竹菊图》再次出现在拍场上,从330万元开始起拍,最后以739.2万元成交。
“项元汴工绘画,兼擅书法。山水学元代黄公望、倪瓒;书法出入唐智永、元赵孟。这幅《竹菊图》笔致简素,得其恬淡疏落之趣,和倪瓒完全是一个路子。对这位并没有载入中国绘画史的画家来说,这样一幅绘画小品,两次拍卖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说道。
项元汴得名于收藏。在他的“天籁阁”书斋内,曾藏有东晋顾恺之绢本设色《女史箴图卷》(现收藏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唐韩的《牧马图轴》(现收藏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照夜白图卷》(现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王羲之的《兰亭序》(神龙本)(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被乾隆视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韩的《五牛图》、李唐的《采薇图》、晋朝索靖唯一的传世墨迹《出师颂》……这些在明朝时就已十分罕见珍贵的藏品,只不过是项元汴天籁阁收藏的千分之一。
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收藏之风胜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私人收藏普遍增多,鉴藏之风甚于前代。明代在书画鉴藏方面,前期画院鼎盛,内府收藏相当可观;中期以后,官方收藏不力,国库管理混乱,使得皇室所藏传世书画大量流失,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晚明商品经济发达,涌现出大批有钱人,他们在财富上得到极大满足后,开始希望在社会地位上获得尊严,于是逐渐向文人靠近。
项元汴本为世家大族,家底殷实,自身介于商人与文人之间。丰富的收藏,使得风雅之士常常会慕名来嘉兴求访项元汴,以登瞻天籁阁、观赏珍玩名画为荣。项元汴与仇英关系甚笃,既是其好友也是重要的赞助人。项家丰裕的物质生活,给予仇英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项元汴收藏的历代名画,极大地满足了仇英的精神需求,使其有机会临摹宋元各家,汲取众长,画功日进,达到其艺术创作的高峰。而项元汴自己也因熏习既久,书画自通,他的工画墨竹、梅花、兰草,颇有逸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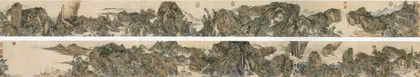 (
钱维城《雁荡图》卷
)
(
钱维城《雁荡图》卷
)
“文人画在明代占到了主导地位,写意画成为一种风尚。项元汴在他的收藏过程中,对于唐、宋、元以来的绘画已经是看得很清楚,绘画的技术、题材到宋元时期已经结束,明代绘画只是对前朝的总结和梳理,唯一的变化就在于明代文人将自己崇尚自然的生活观、讲究做人的品位、追求生存的格调,借情于竹、石、菊这类自然之物,抒发自己的心性。这就成为明代特有的一种风格,也是文人之间的对话,普通老百姓是无法懂的。于是个人的修为和审美情趣的高低决定了这种对话的级别。”一位专家如此说。
然而到明末清兵入关,天籁阁收藏全部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所掠,天籁阁至此衰败,部分收藏辗转流传后世。由于项元汴生前没有留下天籁阁藏品名目数量,身后文物又流散,因此无人能说出全部珍藏的名目数量,但当时散失的文物中一部分为后来的收藏家安岐、梁清标等收得,多归入清室内府。乾隆一直痛惜项氏天籁阁与所藏俱无所存,曾下旨按嘉兴天籁阁意境,在承德避暑山庄新建“天籁书屋”一座,还命内府将宫廷收藏的原项氏天籁阁旧藏书画,选出宋、元、明名家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画卷各一幅,移藏于避暑山庄天籁书屋。而乾隆也将项元汴的多幅作品录入于《石渠宝笈》。
“其实,项元汴的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还是比较常见的,但价格都在几十万元左右,不会太高。而这幅《竹菊图》之所以两次拍卖都能拍出高价,是因为它著录于《石渠宝笈》。”那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1997年开始,《石渠宝笈》逐渐得到重视,逐渐为一些收藏书画作品藏家所追捧。到2003年,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那些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作品,价格肯定高于其他作品很多,这一两年尤为明显。”
2007年嘉德推出的钱维城《雁荡图》卷,最终以2408万元高价成交,这幅作品曾经于2002年在中贸圣佳以429万元成交,5年增值近5倍。另外一件丁关鹏的《群仙献寿》册以772.8万元成交,而文征明的《吴山秋霁图》手卷,成交价达880万元。杭州西泠拍卖推出董诰的《万有同春图》册,成交价为770万元,还有清乾隆帝的《御制十八应真像赞》册,成交价为549万元。北京匡时拍卖春拍推出的文征明《行草书诗卷》,以1111万元成交。北京翰海拍卖推出的钱维城《渔浦翰烟》手卷,以431.2万元成交。而中贸圣佳的徐扬《南巡纪道图》手卷,成交价达到了3696万元,此手卷曾经在1995年由中国嘉德第一次推出,以297万元成交,到2004年,北京翰海第二次推出,以1980万元成交,而另外一件恽寿平的《山水花卉册》,也以1232万元成交。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共编44卷,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9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
“现在著录于《石渠宝笈》的又能在市场上流通的书画作品,大概也就两百来件吧。明代书画市场十分活跃,书画作伪也更加普遍,并出现各式各样的作伪手段和方法,如改款、添款、加盖印章、临仿、凭空伪造、代笔等等。伪作不仅造前代名家,也造当代甚至同时人的画迹,如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董其昌等人,均有时人的大量伪作流布。明后期以来,还出现了地区性造假,专门制作某类或某些名家赝品,其中以‘苏州片’最为著名。像那些在当时仿造的画作,鉴定起来是会有难度的,所以利用《石渠宝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会有利于鉴定,但也并不是说一定就准确无误。上一代专家对《石渠宝笈》并不看重,他们比较重视画家本来体现出来的风格和画作的技术、技巧。”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说,“如果这幅《竹菊图》以后还有机会在拍卖会上出现的话,我相信它肯定能过千万元。它并非是一件单纯的绘画小品,在它的身上,有太多的历史、文化、艺术的信息可以扩展,不过在今天我们还无法展示。可以说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才刚刚开始,当人们的审美回归本位的那一天,它们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体现。”■(文 / 李晶晶) 石渠宝笈项元汴乾隆收藏家书法仇英艺术文化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