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王小五(北京) 图/陈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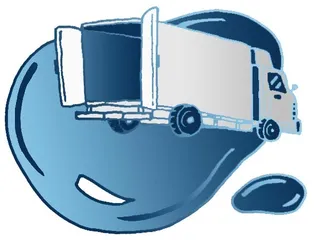
在一个公司待了8年,总有些别人不曾经历的资本值得炫耀,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数次搬家。我曾经以“搬家”为内容策划过一个主题沙龙,找一些企业主和商家坐在一起,谈搬迁在企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样的活动无非是想从业主口中套出些溢美之词,在“选择写字楼”和“象征形象的提升与实力的展现”之间画等号。而我们的领导则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及培训中反复宣扬这样一个理论:企业其实可以在任何地方办公,之所以择A而弃B,基本等同于形象工程加品牌战略。
列数我们的数次搬家,从临建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临建,从一个临建到另一个临建,从临建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房地产业真是个怪胎,给别人盖房子的同时,自己也在不遗余力地换地方。或许所有的地产老总都和我们曾经的大领导有着某种共识,因为他逢采访必说,我就喜欢把办公室放在工地旁边,探探头就能看着房子一天天盖起来,舒坦,安心。
刚到公司的时候,办公室就是一个三层临建。那时候周围不过几十人,大家齐心协力地为着身后的工地能够诞生出中关村的第一高度而不懈工作。大厦落成的那日,大领导决定在顶楼辟出半层作为企业总部,“一个公司,应该有个像样的总部”。
搬家那几日我们总喜欢去空荡荡的屋子转悠,跷着腿坐在前几日还是“办公帮凶”的桌子上,主人一般地四处审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泄愤感。如果那些人间消失的墙有记忆,它应该会记得某天有3个女生聚在这里共同编派某个男生的不是,说到酣处,在场唯一的男生一脸严肃地发话了:“你们要真想把他赶走,那咱们应该这么这么着……”至今我还对那场景记忆犹新,仿佛是某次重大工程之前的战略部署。那个被我们编派的男生最终是被公司扫地出门,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但是人家之后却混得更上一层楼,做上了某公司的总裁助理,坐驾从捷达升级成为奥迪A6L,至于曾经的“仇视”,也在最后的告别宴上和着酒精成了互相调侃忆苦思甜的话题。
我们在那座名噪一时的大厦的顶层做了不到一年的白领,饱览了中关村晚高峰时辉煌的人流与车海,甚至在北京那次著名的大雪塞车时跑到楼顶去打雪仗观长龙,看着空荡荡的三环主路成为路人们的“11”路快行线。
一年后,某公司财大气粗地买下了我们的这半层楼,准备用来安置他们自己的北京总部。昔日大老板的“总部豪言”犹在耳边,然而事实又一次证明,理论层面看似英明的方案在利益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又一次搬家。
这一次,临建的位置坐落在北京CBD的核心区,这应该得益于公司拿地的本事。2002年的CBD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工地,每晚21点一过,大型水泥搅拌车和各种大货车从三环辅路上呼啸而过,把一车车物料运到不同的工地上,帮助开发商编织各自的造城梦想。按说我们的位置就算是工地也一度名声在外,因为曾经有个很著名的迪厅就开在我们的隔壁,入夜那一声紧似一声的鼓点对于加班的我们说不上是挑拨还是鼓励,有时候走晚了,出租车司机看看一脸疲惫的我,都会很贴心地问一句,小姑娘,刚蹦完啊……这个迪厅后来因为打架或者嗑药被勒令停业,然后房子被推掉,那些声色犬马的夜晚就这么消失了。
从西到东,说得矫情点,是从朴素无华到纸醉金迷,只不过这夜夜笙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当四周还是一片工地的时候,生活不便利;四周变成了一片玻璃幕墙的时候,生活不经济;错过了公司的早饭,就只有星巴克或者赛百味可以选择,最近的超市就是贵族化的华润或者屈臣士,这样的生活成本可见一斑。
当然,CBD的价值是绝不能用这么小市民的眼光来衡量的。最起码,这里从来不缺新闻曝光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天天地守着对面的工地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大坑慢慢地起结构、合龙、上幕墙,最后成为一座倾斜的地标式怪物。我们在办公室里目睹过一次爬屋顶拉大字报,一次爬广告牌,一次跳京广桥,一次爬拆迁楼,当然,还有那次著名的路面塌陷。这些故事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没人知道,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只是把这看做日常工作的小插曲,让枯燥的日子看起来和别人有些不同。
随着工程推进,我们的食堂从独门独户变成了一层楼,然后变成了每天20元的饭补。第一座临建消失的时候,大家翻出经年不用的毛笔,有艺术细胞的开始随处写诗画国画,没文化的就直接抡圆了胳膊在墙上写标语,类似“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第二座临建需要拆除一半的时候,我们忍受了半个月和装修零接触的日子,呼吸了无尽的灰尘,然后从西半边的三层搬到了东半边的四层。
相隔的两次搬家之间,总会有几人消失,如同那些随着旧房子一起被清理的书报杂志一般,淡出常规的关系圈。同样会有新的面孔出现,坐在他们在公司的第一个座位上。就连搬家公司的工人都会讲,多搬家有好处,可以清理掉大量不用的垃圾。轻装迎接新生活,我想这就是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那些曾经的似水流年,却总是在搬家的时候跳出来,提醒着一段又一段永远不会被推土机推掉的过去。 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