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的中国逻辑
作者:王恺 ( 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认为:“对于一个处于经济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国资委职能只能根据变化的市场而调整”
)
( 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认为:“对于一个处于经济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国资委职能只能根据变化的市场而调整”
)
“政资分开”的起点
2002年,当时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的张文魁接到国务院交办的要求,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课题组。张文魁回忆,当时这个课题的核心研究在于“管人”,也就是管住当时归中央企业工委管理的190多家企业的一把手的任命权。
而成立这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张文魁说,是彻底实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资分开”的目标。“党政分开”早在80年代就写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而“政资分开”成为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目标——然而,唯有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后,两个“分开”才有可能在国资委的框架下得以实现:国资委将成为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权力的特殊机构。
“成立国资委前的中国的现有国资管理体制,是大家最常提到的‘五龙治水’的局面。大型企业工委或金融工委管人,行使选择经营者的职能;财政部管钱,行使收益及产权变更管理职能;国家经贸委、计委、劳动部也要行使管理权,它们分别行使技改投资的审批、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及企业工资总额的审批。”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宁向东说,按分管职能分工,当时一些大企业的管理还有可能涉及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其他政府部门,所以又有“九龙治水”之说。当时最通常的抱怨是:“央企要办一件事情,可能要跑若干个部委,盖上一大串的章。”“‘十六大’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方针定了,国家分级行使所有权,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方针。”
 (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指出:“随着行业的兴衰变化,很多企业会贬值,昨天还值几亿元,今天可能就只有几千万元,所以要从国家投放的资本中拿来回报,不仅仅是做大,而是要看见真金白银”
)
(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指出:“随着行业的兴衰变化,很多企业会贬值,昨天还值几亿元,今天可能就只有几千万元,所以要从国家投放的资本中拿来回报,不仅仅是做大,而是要看见真金白银”
)
而张文魁心目中,国资委成立不仅仅意味着“分权管理”的结束,更意味着政府体制改革迈出的一大步。“自从凯恩斯主义流行以来,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开始实行对官办企业的干预。”这种干预,往往和政府的服务功能相互冲突,“政府不能又是企业的出资人,又制定种种企业规则,因为出资人追求的是资产回报,而政府应该追求的是公平,是行政效率。就是说,当时的央企按照国际经验必须走商业化之路,不能官不官,商不商。国资委的出现,代表着政府不再直接行使出资人的权力”。分出了出资人职能后,中央政府能“专注于公共服务”。
理想中的国资委,应该是法定机构,即先出台《国资法》,再依法设立相应的机构,可是当时因为时间仓促,只能依照相关条例成立特设机构。国资委企业改革局的原副局长、现副巡视员周放生多年来进行相关研究,觉得这是国资委成立时的一个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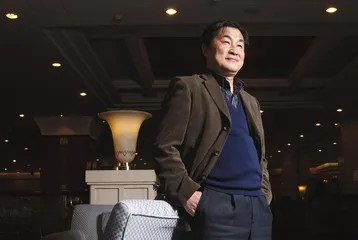 ( 周放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巡视员、研究员)指出:“外界总喜欢批评这些考核制度不合适,但是考核是肯定要进行的——这是出资人的职能,哪里有大股东出钱后不管企业的?就算是慈善捐赠,捐完了大家还关心钱的使用呢。”
)
( 周放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巡视员、研究员)指出:“外界总喜欢批评这些考核制度不合适,但是考核是肯定要进行的——这是出资人的职能,哪里有大股东出钱后不管企业的?就算是慈善捐赠,捐完了大家还关心钱的使用呢。”
)
“当时‘十六大’结束到十届全国人大召开时间太短,来不及立法,就先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条例成立了这个特设机构。”他研究了许多国家的国资管理方式,发现国资管理部门作为法定机构存在是最合理的。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专项法律的产物。先立法规定、授权一定的机构做什么,再成立相应的机构,就能解决很多争议中的问题”。“所谓一司一法”,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背后就有专门的法律,“这样就把纷争解决了,又能突破种种限制”。“法律赋予这个机构有多大权力,这机构就有多大权力。”
出资人角色如何实现:从机构到位到职能到位
宁向东一直与国资委各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记得,“国资委宣布,要花1年的时间实行机构到位”,而李荣融上任时也明确地说,“我们将用3年的时间做好起步工作”。所谓机构到位,是解决来自于“五龙”的人员的“磨合”问题,因为仓促成立的国资委各局的职能尚不明晰。
机构到位属于“物理变化”,可是国资委需要一场“化学变化”。早期出资人的职能尚不清晰,宁向东说,因为没有建立董事会,当时国资委与企业的关系属于“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所以干出了很多越俎代庖的事情,而且特别辛苦。“比如说当时要考核央企的业绩,考核局的董局长得去100多家企业一家家了解情况,和企业负责人一对一谈话,所以当时国资委的‘苦劳’非常大。”可是,这些花费巨大精力去干的活,不一定有成效。
从2004年开始,“李荣融主任的思路逐步清晰,开始确定了一系列考核、重组、风险控制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很多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出资人的职能开始初步具备雏形,产业定位和企业改制也是国资委明确统一的。
当时反响巨大的全球招聘央企领导人工作,被李荣融誉为和“神五上天”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这工作持续多年,海内外共有4000多人报名,最后从中录用了71名。中国长江航运集团的总法律顾问赵玉阜回忆他被招聘的“奇特经历”时,将之称为“历史性的机遇”。“去年8月开始,我先后经历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几道大关,直到最后面试前,我都不认识长航集团的领导。”进入最后环节时他发现,竞争对手不少是来自武汉本地或本系统的,“开始我担心会不会因为我是外地人受影响,后来的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强调,即使一年拿出央企的几十个岗位对全球公开招聘,“也是不多的,这样可以为央企打破干部选拔观念起到示范作用”。而国资委已经建立起来了中央企业的人才库,“未来的企业竞争肯定是国际化的,越早按照市场机制建立人才招聘制度越合理”。
对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定级也是一项新规定,央企的业绩第一次被量化。2005年,首次考核结果公布,9个企业被评为D级,属于指标没完成企业,而4个被定为E级,属于限期整改的企业。周放生说:“外界总喜欢批评这些考核制度不合适,但是考核是肯定要进行的——这是出资人的职能,哪里有大股东出钱后不管企业的?”
在周放生看来,国资委履行的若干出资人职能中,最具有创造力的表现之一是关于国有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其实我们也是碰到问题后才想出具体解决办法的,2003年中航油事件爆发,我们开始制定对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这体系在全国的企业范围内都属于有超前性的。”
国际企业制定风险管理体系是大趋势,“国资委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信息,前后用了3年时间,出台了成熟的体系管理办法,各企业也都接受,国家标准委准备将之制定为标准,这一步我们走到了很多民营的先进企业前面。世界上有多少进入500强的企业之后又走向破产,我们不能这样,基本想法是一定要让这些央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能发展”。
“成立以来最有意义”的大事件
“爷爷和孙子之间,肯定需要有父亲,而这父亲就是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建立。”宁向东对国资委逐步推进的董事会建设表示肯定。
2005年10月,宝钢集团按照公司法改建为国有独资企业,成为央企中第一个外部董事全部到位并且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的中央企业。李荣融宣布,这是国资委自成立以来“最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国企改革的宝就压在这上面,董事会问题不解决,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就解决不了。”董事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国资委可以通过选派的董事们,将选择经理人员、考核经理人员以及决定薪酬、重大投资融资权的决策等具体权力得以执行,也意味着以往受批评的带有行政色彩的国资委管理变成股东方式的管理。目前,董事会制度已经在宝钢、神华集团等19家企业开展了试点。
宝钢的董事会由9位董事组成,其中有5位是外部董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院长夏大慰是其中之一。他回忆当时的过程,“是国资委领导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担任外部董事的,直言看重我的专业学者身份,以及我在日本做研究的经历,因为我在日本研究过战后企业怎样结构调整,发展为大型企业。要知道,国资委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的聘期都是一年,在此期间,要看你是不是真正履行责任,你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
而5位外部董事还有来自香港特区的冯国经和新加坡的李庆言,“就是为了从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入手,给国企改革摸索出经验来”。外部董事拿固定报酬,薪酬水平不是太高。“从薪酬来讲,对这些外部董事没多大意义,也没有多少吸引力。由于都是华人,大家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关心。”夏大慰坦陈当时的想法。
宁向东观察,成立了董事会的企业,明显在管理水平上会有提高,“像我们一直关注的网通的董事会改革,变化更明显”。网通由于引进了西班牙电讯等合作伙伴,并且在香港上市,按照法律引入了独立董事。“我们现在去参加董事会,和以往完全是两种感觉。”从前董事会开会,基本上是董事长一人说了算,“现在来了香港的独董桑顿,他的谱多大啊,把早饭带到董事会的会议上来吃。他始终会提要求:你决策可以,但是给我决策依据”。
这些“外人”的进入,在国资委看来,是出资人进入企业并且加强企业管理的最好方式。周放生说:“以往中央企业的管理模式有两种,一是按《企业法》规定实行的总经理负责制,即一个人说了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二是按《公司法》设立董事会,但在实际操作中是以内部人为主,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决策与执行合一,缺乏相互制衡,难以科学决策。”他认为,外部董事除了在董事会表决外没有其他权利,不干预经理层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这样有利于外部董事更好地代表出资人的利益。
“出资人通过董事会体现意志,并且行使职能。围绕这个改革,以往发生的一切疑惑都会迎刃而解,国企改革将上新平台。”
“绝对控制力”背后的中国环境
世界银行的专家张春霖在国资委成立时就做了预测,称国资委将是一个“强势”机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在国企改革的各个方面,国资委都做到了李荣融所要求的“控制力”。
最典型的是央企重组,李荣融曾经说过让所有企业都紧张的话:“进不了前三名就要重组。”周放生解释:“不重组肯定不行。当时调查显示,央企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战线非常宽,行业也特别泛滥。我们首先做的是从一些民间资本可以经营好的领域逐渐退出,而关系到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国防安全的一些领域,你不能退出,而且要发挥规模优势,进行产业链的整合。”
最典型的是中交建集团的重组,“本来一个是修路的,一个是建桥的,天然就有联系,重组后变成了世界排名前三的企业,产业链做长了”。而一些以往单纯的制造行业,在重组后变成了加上前端设计、研究的合理产业链的企业,“竞争力加强了”。在周放生看来,这些重组,“还是解决让这些企业活下去的问题。很多企业不愿意重组,可是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你不重组就活不下去”。
国资委的企业在重组中减少,并且在不断上市过程中形成了市场化管理的体系,但是按照改革局副局长贾小梁的宣布,国资还将在7大行业实行绝对控股,如军工、电力电网、石油石化、煤炭、民航等。周放生说,这是由中国的特殊环境决定的,“这些行业无法放弃绝对控股,首先这些行业不适合由外资控股,而民间资本即使进入,也需要漫长的过程,无法短时间内适合这些企业的发展”。
周放生早年在企业工作,特别熟悉企业管理,他举例说:“像发电制造设备企业,我们国内只有3家,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经过10多年积累形成的,不是说有设备、有资金、有工人就能依照样子画出来个相仿佛的。”像哈尔滨的电力设备生产厂,当年是举国家之财力,并且借助苏联专家无偿的技术才形成的,又“足足磨合了这么多年,才有今天的生产系统。现在即使花几十个亿,也很难在短时期内造出这样一个在国际同行业内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国资委的专家们觉得,中国的民资可以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或者新兴产业去寻找投资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李泰熙一直觉得,国资委不分行业占有绝对控股地位是不合适的,他提出要分开竞争行业和非竞争行业。周放生解释说:“一方面,我们已经逐步分开;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世界市场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我们绝对控股,是为了保证这些企业在短暂时间内能够进入世界去竞争。你看经过几年努力,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又多了几家。”
国资委成立之初,李荣融一直在提出央企的保值和增值,张文魁觉得这还不够。“随着行业的兴衰变化,很多企业会贬值,昨天还值几亿元,今天可能就只有几千万元,特别是现在国际经济局势变化这么快,特别要预防企业贬值。”他成为编制国有经营预算制度的鼓吹者,“要从投放的资本中拿回报,不仅仅是做大,而是要看见真金白银。”
于是,央企自1993年停止上交红利的制度废弃。“收不收红利,什么时候收红利,收多收少,这都是出资人的权力。”周放生说。
张文魁说,企业多年来习惯把利润留给自己做扩大再生产,认为自己上缴了税收之后就没有任务了,所以开始对红利上缴抵触很大,“可是对于那些高回报的垄断行业,凭什么不对出资人有所回报呢?”而且,出资人是国家,国家完全可以将这些红利拿来进行再分配,典型的如补充社保基金——2007年,国资委通过红利上缴,为国家争取了1.6万亿元的财政收入。
国资委的未来走向
按照部分专家预测,国资委有可能会变成中国最大的控股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将全部资产管理责任转为公司化管理。李兆熙为此专门研究了2002年法国成立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他们的投资也很广泛,但是管理上更合理,将不同行业分成8个处,而国资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外聘的专家和有企业高管经验的人。”
宁向东也觉得,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尽管已经开始建立董事会制度,“但还是需要在国资委和下面直接控股的企业中间形成一个夹层,成立若干个跨行业的控股公司来控制下面的企业”。在他看来,全盘学习新加坡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的国有资产太大了,我们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
周放生去很多国家进行了国资管理的考察,在他看来,很多国家都有值得学习之处。“像匈牙利也进行了国资管理改革,他们的经验是给董事更明确的监控,除了一些相关经济责任外,甚至还有刑事责任的规定。”而挪威这样的国家,它的石油公司属国资,但是管理完全市场化。
至于国资委是不是必须改为中国最大的控股公司,是不是要在国资委和企业中间加设若干家控股公司,在周放生看来,“都是没必要讨论的。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我们的责任不是将国资私有化,而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国企做大做强,这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张文魁的补充也很有趣:“你能想象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但是你能想象一个国资委变成的国有控股公司的破产吗?”■ 逻辑中国国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