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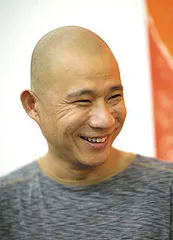
初春时节,我在北京通州潮白河大堤上转悠,在一个马场附近向一个村民打听村子里有没有房子卖,他问我是不是画画的,然后指给我河堤边上的一个院子,说这里住的是画家。敲开门,原来认识,是老冯的儿子。去年圣诞节宋庄艺术促进会请画家们吃饭,我去了,和老冯的家人坐一桌,这才知道了老冯的传奇经历。
老冯是老一代了,“文革”的时候在北京帆布厂做清洁工,办画展的自述就叫《一个扫地工的梦》。可画画给老冯带来的贫困甚至超过了一个扫地工的命运,“文革”后,他参加了画展,却因为“画家”的不好名声和经常旷工丢掉了扫地工的工作,自此命运多舛。他练过摊,开过古董店,可从来没怎么赚过钱。买不起画布,也买不起颜料,老冯最后迷上了木刻这一成本最低的形式,越来越穷,最后带着一家人,从北京城里搬到了郊区,在潮白河边落了户。老冯没怎么读过书,几乎独打独撞做了很多要么“野兽派”,要么装置的作品。方力钧花了8万美元买下了老冯的作品,才算让老冯苦尽甜来,那些天,老冯天天请大家到饭馆里吃饭喝酒,一连半个月,在整个宋庄轰动一时。
老冯的去世,也算得上一个传奇:有人说,老冯是因为喝酒太多得的癌症,有人说是因为看到大家伙都租地盖画室,自己也去租,结果被人骗了,租的是一块马上要到期的地,气得得了病。不管怎么说,老冯等于是一辈子受穷,临了,赚的钱还都送给了医院。老冯的去世是宋庄画家中的一件大事。这边,老冯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那边,画家们全体出动,在“798”为老画家冯国东举办了盛大的个展,老栗为老冯展览写的序就是《一个扫地工的梦》。个展开幕当天,老冯就去世了,病床上还画了上百张的速写自画像,用老冯的话说,他是染上了艺术的瘾。
后来,我买了马越的房子。我问马越有没有吃过老冯的请,马越说吃了好几顿。我居住的村子,画家们很少有人没吃过老冯的请,大家对老英雄的敬仰更是洪水滔滔。买马越的房子,还有一个奇特的经历。去年,宋庄镇政府成立了艺术促进会,10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艺术节,画家们多拿出画作参加活动,小堡村的马路成了巨大的露天展台,马路中央展板延伸3里地,两边挂满了画。当代艺术和当地民歌表演同场举行,一时间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样展览亵渎了艺术,不把画拿出来。这次展览最让人叫绝的是展线正中央身着中山装的宋庄四大天王画像,栗宪庭、方力均、岳敏君和杨少斌,因为这几位大师的示范作用,宋庄吸引着一批批画画的前赴后继。
展览的同时艺术促进会还推出了一本刊物《宋庄ART》,杂志发表了马越写的小说《长在宋庄的毛》,里面提到了他落户宋庄的全过程,比如他1998年来的时候,画家最初的聚集地小堡村已经住满了,他才定居任庄,因此也就成为了任庄里的第一个画家。自从他搬来,这个小村子已经陆陆续续住进了40多位画家,算得上宋庄大画家村里第四大的小画家村。这小说里还介绍了他们两口子是如何侍弄院子的,院墙上爬满了蔷薇和爬山虎,石槽里养着小鱼。我不由反问自己,那些高价买了商品房的业主们,动不动要为广告宣传里的“文脉相承”啊,“艺术摇篮”之类的毫不沾边的浮夸多付出几万乃至几十万元的钱,而这里,一个被铅印文字记载的地方难道不值那些商品房的零头么?
住进来后才发现惊喜还在后面。有一个姓翟名墨的画家就借住在这个小院里,当时刚好是上海帆船展,老翟在那儿正招募志愿者和他一起航海呢。我的房子里贴着老翟的宏伟蓝图,全球海图上用粗大的箭头标示着他未来3年将要绕地球3圈的计划。老翟在新西兰的时候租住一个老航海家的房子,从老头儿那儿染上了航海的瘾,先是绕新西兰一圈,接着在南太平洋上驾着8米帆船遍访海岛,回国后还从大连兜到三亚。就是在我住进来的当口,老翟从日本买了一条船,正在划回来的海上,海上起了大风浪,打破了帆老翟又回去修船,耽搁了我们房屋的交接。老翟的一句口头语是“欢迎到我的船上来”。山东口音,诚恳加热情,对女孩一定极有杀伤力。等老翟完成了他的壮举,我一定把房子改成“航海英雄事迹展览馆”。
买房子之前,我是不认识马越的,我甚至不认识介绍我买房的单智。在小堡村一家当地人开办的画廊里,随便一搭讪,他便带着我跑到几公里外的村子看房子。绘画是个单纯的事,在城里,你很难找到这么热心而没心机的一群人。看房之前我在老冯家所在的小杨村看了一个3间的小院,打电话给那户农民,问他是不是5.5万元,他肯定很懊悔出了这个价,就说你可以把旁边的那个院子也买了,两个加起来15万。我怎么算两个5.5万的和也不是15万,按理说多买还应该有折扣。可农民的逻辑是,你买多了,有了大院子,就得多付钱。当然我没跟他耍心眼,假如我5.5万元买一个,另一个对他难道不就变成鸡肋,到时候他不便宜卖给我才怪。这里讲的是生活的智慧,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甚至学到的完全相反。那本划时代的《宋庄ART》就是生活的智慧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一群避居郊区,生活上潦倒,艺术上也处于停滞状态的画家的价值被当地官方发现了,被“招安”了。画画的在圆明园、索家村人人喊打,但在宋庄却是满自豪的称谓。这是一个庞大计划,文化造镇,镇政府还成立了文化造镇办公室。
“招安”对创作能有什么好处?艺术上显然不搭调,可招安意味着不会被扫荡,被驱逐。只这么一点好处,就成了全国画画的滚滚而来的一个原因。在索家村,据说画家的工作室是违法建筑,被铁面无情地强制拆除,而在这与河北交界的宋庄镇,全国各地画画的却在文化造镇的招引下滚滚而来。广东来的一个大二学生要到小堡村找宿舍,我们一家家敲门,居然发现大多数农家院子里都盖了小厢房,一排排的,如同城中村的租房户一般把地皮最大化利用。一间小宿舍100到150元不等,而一个3分地的院子,年租金能高达8000到1万元,最贵的院子年租金竟然到了3万元。要知道,想当年圆明园画家最早迁移到此的时候,几千块就能买一个一亩地的大院子。那天我们转了两小时,找遍了村中可能的出租房,居然只有一个月租150元的,刚盖好的房间空闲着。
即使还没有大规模的文化造镇项目落地,艺术家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繁荣都是空前的,介绍我买房子的单智租住的是4间的,很小的院子,还不在房价最贵的小堡村,1999年的时候一个月的租金是100元,现在年租金是5000元了。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到过小堡村,一户待租的房主用征询的口气问我300元一个月行不行,现在,你得问他600元行不行了。飞涨似乎就发生在一年间,油画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宋庄一下充斥了形形色色的人。一个两三年前五六万元买来的院子,现在就会有人问你十五六万卖不卖。一个本来边缘的农村小镇,随着当代艺术的春风,就这样从边缘走向中心状态。在进宋庄的必经之道,一个大粮仓改造成的宋庄一号(TS1)美术馆拔地而起,展线800米,据说是全国最长的展线。在小堡村,6层楼高、5000平方米、设计极有现代感的当代美术馆将成为艺术园区的标志性建筑。小堡村拿出了一大片荒地,建造人工湖,湖边则是一圈开放的艺术家的工作空间。这个庞大的规划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画家报名,一时间蔚为壮观。
其实早在自发状态,这里的村子就自发形成了“艺术基地”、“艺术集中营”和“艺术大院”等画家聚居地,方便创作也方便展示。过去办展览,一定要进城,现在在村子里也能吸引到足够的客流。当代艺术的买主多是西方人,大街小巷经常见到他们的面孔,油画的标价也全用美元,一幅小一点的3000美元,大的6000美元。这里的饭馆里也挂着画,颜料店里也挂着画。一个小堡村有多少画家?按村长的说法500户中超过了20%是画家,这还是去年的统计。整个宋庄,据说有七八百画家。
温州人炒完煤,也来这里开画廊;美院的老教授退休了,也来这里颐养天年,至于画家们,不时有奇迹传出。打熬了很多年的画家们有的终于签了画廊,解决了生存问题,有的还是要靠代课画画填饱肚子。艺术合作社的张海鹰告诉我,只有20%的能以画画为生。但这20%的力量足以鼓舞人了,至少在我们村,马越正在盖他500平方米的工作室,王强小楼造价高达百万,十几栋小楼改变了这个北方小村落的面貌。
因为染上了艺术的瘾,因为地处离天安门仅20公里的“CBD后花园”,这个传统的北方农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画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