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古埃尔论好奇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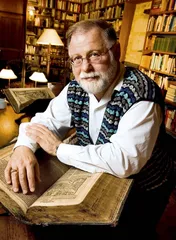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
我是谁
《经济学人》说:“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是一个好奇心很强、喜欢探索、迷恋于细节的人。他博览群书,35年来平均每年出一本书。他是一位阿根廷外交官的儿子,懂多门语言,在定居法国之前住过很多地方。几乎没有不向他开放的文化或历史时期。他的新作《好奇》是多本书合为一体:对人生的大问题的思考、过去的伟大著作提供的回答、向但丁的致敬,以及对好奇本身的思考。”
好奇是我们获取知识的动力,但也会给我们招致祸害。所以说“好奇”一词有双重含义。它可以是一种关注细节、热爱真理、谦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的美德,也可能是一种学究式的小题大做、窥探和智识上的傲慢。总之,好奇是我们探求为什么、怎么办的冲动。
《好奇》一书一共17章,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一个问题,如:什么是好奇?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如何推理?我们如何提问?什么是语言?我是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什么是动物?我们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能占有什么?如何使事物井然有序?曼古埃尔提出的这些大问题引领他探讨了流亡、疾病、气候变化、宠物、文化屏障、社会认同、奥斯维辛、广岛原子弹爆炸、贪婪和死亡等主题。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1948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特拉维夫长大,因为他父亲是驻以色列大使。在学习他父母说的西班牙语之前,他就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16岁时他回到阿根廷,刚好在一个书店里遇到了博尔赫斯。那时已经失明的博尔赫斯需要一个人读书给他听,曼古埃尔做了他4年的朗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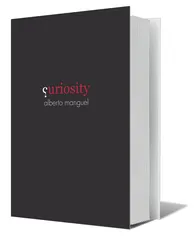 《好奇》
《好奇》
1969年,21岁的曼古埃尔离开了阿根廷,在伦敦做嬉皮士腰带,在巴黎从事出版业,把博尔赫斯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1980年,他出版了《幻境辞典》。之后他非常高产,已经出版了《阅读史》、《夜晚的书斋》等21部非虚构作品、5部小说,还编了23部文集。
在讨论“我是谁”时,曼古埃尔引用了心理学家荣格的论述:“我存在的意义是,人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自己是一个向世界提出的问题,我必须说出我的回答,不如我就依赖于世界给出的答案。”我们读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就像是镜子,能从中看出我们自己隐秘的特征。“我们的心智图书馆是由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的地图组成的。弗洛伊德敬佩《浮士德》的开头,而荣格被《浮士德》的结尾吸引,博尔赫斯更喜欢康拉德而非简·奥斯丁,多丽丝·莱辛更喜欢伊斯梅尔·卡达莱而非村上春树,这些偏好表现的不是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立场,而是对认同的同情问题做出的反应。”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对身份提出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说法。爱丽丝在奇境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毛毛虫,它坐在一个巨大的蘑菇上吸水烟。毛毛虫从嘴里取出水烟,问爱丽丝:“你是谁?”爱丽丝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早上我起床时还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打那以后我已经改变了好几次。”那个毛毛虫让她背诵一首诗,来测试一下她的记忆力。爱丽丝和那条毛毛虫都知道,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的传记,曼古埃尔说,它们“保存着我们关于自己的图像”。
在该书最引人入胜的一章中,曼古埃尔讨论了古希腊智者派的名声问题。希庇阿斯、阿尔西达马斯等哲学家四处云游,收费给人上课。“智者”一词指的是他们的教师职业,而不是一种思想学派。在柏拉图之前,智者的意思是英明、智慧,它是褒义的。在柏拉图之后,它的意思变成了“一种花言巧语的、谬误的、不诚实的推理”。“智者的风趣”变成了扭曲逻辑学规则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者派是造谣中伤者、是小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得智者派驻历史上臭名昭著。但曼古埃尔指出,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和智者派其实一样。柏拉图作为贵族后裔,鄙视那些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服务、教他们修辞技巧的老师。除了在他们的批评者的书中,智者派的哲学著作都没有保留下来。但即使在这种不利的材料中,曼古埃尔还是努力挖掘了一些段落,来展示智者派的严肃性。希庇阿斯相信一种可行的政治世界主义:一种普遍的团结,为了更好的人际关系而证明相互对立的、民族的法律的合理性。阿尔西达马斯挑战了奴隶制,这是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从未想到过的,因为他们认为少数人有统治权。曼古埃尔说,智者派的著作都消失了,但其他人著作中对他们的刻画揭示出,他们有更多了解一系列复杂的想法和发现的欲望,他们拒绝“追随苏格拉底显而易见的逻辑,走上一条误入歧途的道路”。
衰老和死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章讨论的是衰老和死亡。曼古埃尔转述了一个故事:在意大利小说家乔治·巴萨尼的小说《芬奇-孔蒂尼花园》的第一章中,一群人参观罗马北部的一个墓园。一个小姑娘问她爸爸,为什么古老的坟墓不像新坟那样令人感到悲伤,她爸爸回答说:“这很好理解。那些刚刚去世的人离我们更近,所以我们更爱他们。而伊特鲁里亚人已经死了那么久,以致他们好像没活过,好像他们一直是死的。”他借这个故事说明,死亡总是会引发我们的好奇心。
67岁的曼古埃尔说,他已经进入了老年,他对身体与精神的关系的思考既生动又感人:“我的身体总是把它的重量放到我的精神上,好像它很嫉妒我赋予我的思想的注意力,在用蛮力排挤它们。直到不久前,我还以为我的身体只在年轻时主导着我,待我成熟后,我的精神将占据那个优势地位。身体和精神各主导我生命的一半,它们应该淡泊、公平地统治,一个悄悄地接替另一个。
“在我的青春期和刚刚成年时,我的精神好像是一个杂乱的、不确定的存在,笨拙地打扰身体轻松愉快的生活。悖谬的是,那时我的身体觉得不如我的思想那么稳定,只有通过我兼收并蓄的感觉,早上闻到新鲜的空气、夜晚穿越城市、在阳光下吃早餐、在夜里抱着爱人的身体时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甚至连读书也是一种身体的活动:触摸,嗅觉,词语在书页上的样子是我跟书的关系的重要部分。现在快感主要源于思考,梦和思想变得更加丰富、清晰。精神想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是老去的身体就像一个暴君,拒绝撤走。年轻时我总是觉得我是我自己的,哪怕旁边有人,因为我的身体永远都不会困扰我,永远不会显得是某个跟我分开的东西。它绝对是我完整的自我,不会投下影子。但现在即使我孤身一人,我的身体也会像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一样,当我想思考或入睡时发出噪音,当我想坐下或走动时推我。”
塞涅卡说:“生命够长的了,我们被分配的一段生命已经大方到足够我们实现最有抱负的计划,如果我们小心地花费它的话。”但是人人都希望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朽。有一段拉丁文碑文说:“我是灰烬,灰烬是土,土是神,所以我没有死。”曼古埃尔说,这段推论优美地概括了来生、不朽的观念。在碑文背后是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人死后不会彻底消失,那么后人就有机会跟他们谈话,他们也有机会说话。 读书文学好奇曼古埃尔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