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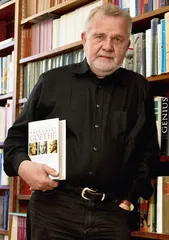 文 / 陆晶靖
文 / 陆晶靖
作为文化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具有永久性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影响具有世界性,但究竟什么才是其根源和核心,人们很难弄清楚。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如此之繁多,即使许多饱学之士也不得其门而入,丹麦人勃兰兑斯曾想原原本本地描述德国浪漫派,他后来觉得对于一个丹麦人来说,“这个题目大得吓人”。何止大得吓人,连定义都难以给出。英国人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的第一章就叫“寻找一个定义”,他引用了歌德、海涅、司汤达和尼采谈论浪漫主义的话,这些话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歌德还站在浪漫主义的反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人都在描述浪漫主义“像什么”,最后也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义。连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也觉得这个话题很容易陷入永恒的交谈和毫无成果的喋喋不休。但是阿多诺的学生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看起来打算简单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援引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话说:“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
但浪漫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到达了诺瓦利斯描绘的那种状态,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体现为一种对于理性之外的世界的好奇和迷惘。赫尔德觉得理性永远处于一种迟到的状态,它使用因果关系的概念,因此无法领会创造性的整体,因为整体——也就是这个世界——并非完全遵从因果律。这种困惑也反映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在开头就感到自己被书本包围,已经对世界丧失了感知能力,而书斋外面有更广阔的知识和经验。赫尔德和歌德在书斋外面发现了“人”和“生命”的复杂性,虽然不能把他们也算作浪漫主义者,但当启蒙精神挟着法国大革命的剑与火轰隆向前的时候,在德国,反抗的力量就从他们的先贤那里找到了精神资源。开始,革命给理想主义带来的是鼓舞,而革命演变为恐怖和暴政之后,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启蒙精神也遭到了怀疑:人们开始想,启蒙精神和理性是否能把握生命之深邃及其黑暗面?进步是否总能带来改善?一开始,德国知识分子对大革命欢呼雀跃,因为在他们的国家,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而当大革命出现问题,他们又是第一批开始反思的人。世界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性来构建的装置,曾经难解的、神秘之物是可怕的和耻辱的,而到了18世纪末,德国人对神秘的兴趣大大增强,它们成了有魅力的东西。
诺瓦利斯在阅读费希特的时候写道:“神秘莫测的道路通向内部,谁在此停留,仅成功一半。第二步必须是朝向外部的有效目光——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和有分寸的观察。”这时候想象力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想象力成为游戏最重要的元素,他们把世界看成另一个样子,像诺瓦利斯在开头说的那样,在俗世寻找诗,寻找有限中的无限,世界辽阔无边,但对于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这又像是他的家园。诺瓦利斯和妻子索菲结婚时,她才13岁,他赋予她无数的意义,而索菲却未曾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当索菲去世后,诺瓦利斯实践了他的浪漫理念,他想竭力赶上爱人,与她交流,却不是通过自杀的方式,而寄希望于自己无尽的想象力达到神秘的超验。如果说妻子只是诺瓦利斯的小的“外部”,并且这种体验过于神秘,其他的浪漫主义者就相对“健康”得多。他们明确表示不想当白日做梦者,他们想改变生活自身,从自己开始,接着是朋友、读者和整个民族。信条来自不是浪漫主义者的席勒:“只有当人在词的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世界游戏,和知识上陈旧的条条框框游戏。这种态度与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有诸多相似,但相对来说浪漫主义更加现实。卡尔·施密特批评说,浪漫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巧妙地选取诗的、哲学的和政治的题材作为其智力游戏的契机,而那些不那么符合其世界图景的东西则被忽略。也就是说,他们构建的世界是片面的。
作为政治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者迷恋黑夜与人类神秘的起源,这一迷恋到后来渐渐成长为对德国文化乃至民族性起源的追问。他们对希腊-罗马的解读完全不同于温克尔曼以及歌德等人,在他们眼里,希腊曾经带给世界神秘的快感和骇人的残酷,而不仅仅是古典艺术推崇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年代,这种问题获得了政治分量,他们开始真正追求一种只属于德国的东西,称之为文化自觉也好,民族觉醒也好,总之,虽然在欧洲政治中德国没有自己的地位,但他们通过文化获得了政治上的尊严,并且认为这种觉醒将会带来比拿破仑的炮火更大的轰鸣。浪漫主义者关于无限的形而上学成为历史、社会、民族和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学,在个人与超验(上帝,无限者)之间并不存在深渊,历史和社会都染上了一种醉醺醺的气息。将现实浪漫化的尝试可以变形为将历史超验化,历史被解放了,历史重新开始了,我们要重新看待历史。萨弗兰斯基敏锐地发现了浪漫主义和德国式非理性乃至后来的整体迷狂的联系,浪漫主义可能含有纳粹元素的胚胎:废弃理性、对人的兽性化、对权力和猛兽的美化……按照卢卡奇的观点,浪漫主义是德国精神史的灾难性转折点,直接为国家社会主义做了铺垫;以赛亚·伯林和沃格林也都觉得,浪漫主义是这场灾难的精神的史前史,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伴随着浪漫主义的成长。在世界观上,浪漫主义的影响是:个人的和创造性的意志强于任何一种客观的、世人必须适应的世界结构,任何粗暴的事件都会经由这种创造性的意志被真诚地进行崇高的解读。这种气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才被压制下去。
 浪漫主义甚至和反资本主义也有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的开始不一定光彩。E.T.A.霍夫曼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痛苦地认为,市民世界以经济原则和功利思想摧毁了艺术。艺术不再是崇高之物,霍夫曼对艺术家必须依靠市场谋生这一点痛苦不已,将写出待售的作品视为耻辱。市民社会里的人被浪漫主义者视为庸人,他们为自己不属于庸人而感到骄傲,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艺术家毕竟是一小部分人,对于艺术的爱,最后演变为对市民社会的恨,这是令人痛心的。这种思想在瓦格纳那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应,瓦格纳有不少有钱的崇拜者,但他瞧不起他们。《尼伯龙根的指环》里的阿尔贝里希,多少有着犹太人的影子。该剧的结尾,神奇的黄金终究回到莱茵河的怀抱,而宫殿燃起烈火,爱超越了财富和权力的欲望。他对于市民社会的反感在艺术上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多多少少有这种情绪,最后与反犹主义融合到了一起,最终在希特勒那里达到了灾难的顶峰。 文学瓦利斯德国歌德政治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甚至和反资本主义也有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的开始不一定光彩。E.T.A.霍夫曼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痛苦地认为,市民世界以经济原则和功利思想摧毁了艺术。艺术不再是崇高之物,霍夫曼对艺术家必须依靠市场谋生这一点痛苦不已,将写出待售的作品视为耻辱。市民社会里的人被浪漫主义者视为庸人,他们为自己不属于庸人而感到骄傲,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艺术家毕竟是一小部分人,对于艺术的爱,最后演变为对市民社会的恨,这是令人痛心的。这种思想在瓦格纳那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应,瓦格纳有不少有钱的崇拜者,但他瞧不起他们。《尼伯龙根的指环》里的阿尔贝里希,多少有着犹太人的影子。该剧的结尾,神奇的黄金终究回到莱茵河的怀抱,而宫殿燃起烈火,爱超越了财富和权力的欲望。他对于市民社会的反感在艺术上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多多少少有这种情绪,最后与反犹主义融合到了一起,最终在希特勒那里达到了灾难的顶峰。 文学瓦利斯德国歌德政治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