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迈耶自宅:“我一生珍爱之物,都在我的私人博物馆中”
作者:丘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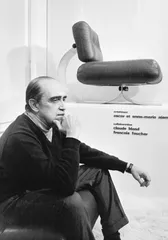 ( 巴西建筑师尼迈耶。作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建筑的倡导者,他经历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一个世纪
)
( 巴西建筑师尼迈耶。作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建筑的倡导者,他经历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一个世纪
)
在与自然融合处
在2012年12月5日奥斯卡尼迈耶去世之前,几乎每个慕名前去里约热内卢工作室拜访他的人,都不忘之后探访一下他曾经在卡诺阿斯区山谷中的住宅。直到去世之前一个月,这位104岁高龄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他坚持每天早9点到晚19点、一周6天在事务所里工作。为了方便,他就住在办公室附近“一座平淡无奇”的公寓中。卡诺阿斯住宅如今是奥斯卡尼迈耶基金会所在地。虽然随着1965年尼迈耶流亡海外,他没有再回去居住,但这栋住宅更符合人们对一所建筑师自宅的想象与期待,它也充分展现了尼迈耶的建筑美学。
由里约市区开车前往,一路都行驶在大西洋的海滨,还要经过一段叫作“尼迈耶”的大道,那其实是根据尼迈耶的远亲、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来命名的。由海边转向一条上山的小路,路两旁是遮天的棕榈树和别墅的高墙,山顶上可见红红绿绿的滑翔机在翱翔。1953年卡诺阿斯住宅建造之时,这片山区只有它孤零零一栋房屋,后来逐渐成了富豪竞相建房之地。开车不能到达卡诺阿斯住宅跟前,必须要下车步行通过一条小径。
卡诺阿斯住宅就在一片葳蕤草木的掩映当中。它的周围长满了香蕉树和菠萝蜜树,那些凋落的树叶经年累月为林间空地铺上了一层厚而柔软的地毯。尼迈耶十分喜欢植物,在2000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时间的曲线》中,他写到了年轻时总爱和妻子、女儿去附近的植物园散步。“我有时看着水池里大朵的荷花发呆,有时高大的棕榈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会停下来仔细阅读那些拼写复杂的植物名称,或者在本子上试图用几笔简单的线条描摹下植物的生长。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坚持不懈地光临这里。我们每天上午11点准时到达,那时一天中最好的阳光正透过树枝缝隙倾泻下来。自然是那么完美,值得人类满怀敬畏……想想童年生活里那些果树的命运吧!芒果树、鳄梨树、嘉宝果树……它们后来都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机动车的街道和丑陋的高速路。”
周边的自然环境太美了,尼迈耶舍不得让住宅破坏任何天然景色。从正面看上去,它是一个具有优美曲线的单层玻璃房。3/4的墙面都是透明的,居于其中的人近能观赏到花园,远能眺望大海。玻璃幕墙和一些纤细的黑色钢柱支撑起同样弯曲的混凝土平屋顶,这种奇怪的形状被当地人形容为“像个菜豆(Lima Bean)的豆荚”。房屋门口游泳池也是曲线形的,池边立着一尊尼迈耶好友阿尔弗雷多塞奇亚蒂创作的女人裸体雕塑。阳光下的一池碧水,与屋顶相互映衬。房屋和水池之间由一块巨大的岩石相连,奇妙的是这块岩石还穿透玻璃一直伸进了起居室里。顺着岩石的指引走进去,才发现石头遮挡住了一截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由于地势是斜的,这个顺势下去的楼梯通往的不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而是一组看得见风景的卧房。房间的窗户被设计成向外凸起的飘窗,侧面不是常规的矩形而是梯形,这样室外的葱茏就被最大限度地引入室内。尼迈耶和他的家人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侧门直接进入他们的私密空间,不用经过楼上的开敞平台。
 ( 房子周围出现一块岩石,尼迈耶就让它自然伸展进客厅
)
( 房子周围出现一块岩石,尼迈耶就让它自然伸展进客厅
)
卡诺阿斯住宅让每个来过的人都印象深刻。意大利建筑师厄内斯托罗杰斯永远记得夜晚降临卡诺阿斯的那一幕:“那天太阳刚刚沉下地平线,我们置身于一片橘色、紫罗兰色、绿色和靛青色组成的绚烂晚霞中。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香气,虫鸣组成了一支狂想曲。”美国建筑评论家迈克尔索金将它和另一位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在1920年设计的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做比较,“就好像德国馆在酸性溶液上面融化的样子,它自由流淌的空间是和密斯那种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却同样有力”。巴西现代建筑奠基者卢西奥科斯塔的女儿玛丽亚科斯塔称赞这座房屋“不仅可以用眼睛欣赏,还可以用耳朵聆听”。尼迈耶的建筑经常被比喻成一支活力四射的桑巴舞曲,或者一首活泼性感的博萨诺瓦(Bosa Nova)。
批评的声音也从未止息。德国建筑师、包豪斯设计学校的创办者沃尔特格罗佩斯称赞这里“美极了”,他唯一的疑问是:“这样的建筑可以去复制么?”对此,尼迈耶很不屑一顾。“简直是个傻瓜,就好像我真打算这样做似的!这难道不是因地制宜的结果么?”尼迈耶后来在另外的场合还攻击过这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派:“我讨厌包豪斯,那是建筑史上一个糟糕的时代。他们没什么天赋,所有的只是条条框框,连刀叉他们都要弄出规矩来。毕加索就不会有那么多规矩。建筑就像机器?不!机器太丑了!规矩是最讨厌的东西,它就是用来打破的。”
 ( 卡诺阿斯住宅充分体现了尼迈耶的“混凝土曲线美学”
)
( 卡诺阿斯住宅充分体现了尼迈耶的“混凝土曲线美学”
)
曲线的诱惑
尼迈耶在设计卡诺阿斯住宅时46岁,正处于建筑师生涯的成熟期。他1907年出生在里约热内卢,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平面设计师,家境殷实。“我的母亲说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用手在空中指指画画。等到能握笔时,基本天天都画。”尼迈耶说,但他并不想成为画家,在父亲的印刷厂工作两年后,报考了国立美术学校的建筑工程专业。除了建筑方面的书籍,他平时涉猎广泛,喜欢哲学和诗歌,尤其酷爱读波德莱尔的诗。1988年他在获得普利兹克奖的时候说:“我所有的建筑作品究其根源是出于对波德莱尔一个观念的信奉。这个观念就是: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规则的、突然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是美的核心部分和根本属性。”1934年,尼迈耶毕业后选择在科斯塔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跟随这位在巴西被视为现代建筑奠基人的大师工作,他不但学习到现代建筑的思想,也有了许多实践的机会。
 ( 关于设计,尼迈耶有句简短的名言:形式追随女性
)
( 关于设计,尼迈耶有句简短的名言:形式追随女性
)
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36年。尼迈耶参加了科斯塔主持的巴西教育和卫生部大楼的设计工作。科斯塔聘请现代主义建筑先驱柯布西耶担任这个项目的建筑设计顾问。尼迈耶和柯布西耶进行了颇为深入的交流,并对柯布西耶描绘的新建筑的图景心向往之。柯布西耶评价这个热爱波德莱尔诗歌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尼迈耶就知道如何无拘无束地创作现代主义建筑。”后来柯布西耶离开巴西,由尼迈耶继续主持项目。在这个作品中,尼迈耶将柯布西耶的理念化为一座朴素的高层建筑。在它的内部,充满各种曲线线条,外墙则装饰着海马和扇贝图案的浪漫非凡的瓷砖,在巴西的艳阳下显得非常有个性。
“巴西的建筑师,像所有当代建筑师一样受到柯布西耶的影响,但几年后就出现了另一种趋向……曲线搞得自由,跨度也很大……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气候、习俗和感情与别处不同。”尼迈耶说。进入上世纪40年代,尼迈耶自己的“混凝土曲线美学”逐渐形成:用适量的曲线制造出的轻盈感,开辟出使建筑的主结构逐渐向某种未知形态过渡的想象空间,钢筋混凝土的曲面外壳与大量的仅在美学意义上有效的直线形成奇异的交错。1943年,在他第一个独立设计的位于贝洛奥里桑特市名叫“潘普利亚”的新型郊区住宅区域里,尼迈耶实践了这种美学观念。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这组建筑中最大胆的尝试。弧线是这座教堂的唯一建筑语言。传统的梁柱楼板结构被混凝土薄壳结构取代,屋顶像波浪般展开,内部的两堵墙只是顶部的斜下延伸。不少评论家说这是一个回归巴西殖民时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如果将卡诺阿斯住宅和尼迈耶1942年建造的第一处拉戈阿自宅来做对比,就更能看清楚尼迈耶在将现代主义建筑地域化上的探索。拉戈阿住宅最大限度地实践了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理论。它是一个屹立于陡峭悬崖之上俯瞰湖泊的立方体房屋。按照“五点”之一的“底层架空”原则,住宅底部有立柱支撑,这样住所就脱离了基地的限制,底层也被规划成长满花草的庭院。二层的起居室和三层的卧室都有水平的条状开窗,这是遵循另外一条“横向长窗”的结果。从形式角度来看,住宅只有在底层与自然相联系,一旦进入二层和三层,外面的景色就好像是挂在墙上的图画,可以感受却不能进入。尼迈耶十分谨慎地引入了巴西传统的建筑元素,比如白色的墙面、红瓦单坡屋顶以及蓝色木质百叶窗。等到10年之后,巴西风格的曲线则完全主导了卡诺阿斯住宅的样式。“我意识到平面会将内外世界隔离,曲面才能让内外沟通。”尼迈耶说。也是由于曲线形的、略微突出玻璃立面的巨大混凝土屋顶遮挡,起居室在夜晚就正好处于阴影之下,这样就解决了玻璃房里如何保护隐私的难题。“我喜欢通透的房屋,不想增加窗帘。”
曲线建筑的发展是和钢筋混凝土技术的日臻成熟分不开的,之前的混凝土在强度与弯曲韧性上还达不到要求。在巴西,钢铁是一种稀少昂贵的建筑材料,混凝土则便宜得多,一般工人就能胜任混凝土浇灌的工作。“混凝土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它允许我去追求一切纯粹的形式。它给了我一双不受任何拘束去创造建筑的翅膀,就好像去做雕塑一样。”尼迈耶说。他身边的工程师胡塞卡洛斯苏瑟金说:“我们每次在一起讨论项目,尼迈耶的问题总是混凝土结构的极限在哪里,能完成多大弧度和跨度的创造。”尼迈耶的工作团队里还经常有一些著名数学家的身影,包括巴西的若阿金卡多佐和意大利的皮埃尔卢吉奈尔维。他们帮助尼迈耶把自由伸展的空间之梦牢牢地固定在钢筋混凝土的稳定性之中,使得他的建筑在造型奇异的同时还以稳固结实著称。
“柯布西耶说在我设计的建筑里他仿佛看见了里约热内卢的山脉,但是我更喜欢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评价自己作品时所说的:‘我一生珍爱之物,都在我的私人博物馆中。’”尼迈耶说。卡诺阿斯住宅就是他为自己建造的那座“私人博物馆”。在他自传的扉页上用一段话解释了自己为何如此迷恋曲线:“吸引我的并不是直角,也不是坚硬的、顽固的、人为的直线条,吸引我的是自由、性感的曲线。那是我在祖国的群山中,在河流的蜿蜒流淌里,在大海的波浪顶端,在天空的云彩边沿,在完美的女人的身体上看见的曲线。曲线构成了全部的宇宙,一个弯曲的、爱因斯坦的宇宙。”
尼迈耶还有句更简短的名言:形式追随女性。到他里约热内卢工作室拜访的人对这句话都会有直观的感受:他的工作室设在一栋奶油绿色的具有起伏波浪状立面的大楼顶层。这座楼在当地的绰号叫作“梅韦斯特”大厦,梅韦斯特是好莱坞凭借身材红极一时的明星,有一双异常丰满的乳房。从尼迈耶的工作室能看见整个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景象,那些穿着比基尼在海滩漫步的女孩近在咫尺。一次德国建筑报道记者尼克拉斯马克前来采访,追问他到底那座“私人博物馆”里都有什么心爱之物。“尼迈耶没有回答。”他写道,“他转而在房间里搜索纸笔,说还是画画更容易解释。他问随行的女摄影师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叫安。然后尼迈耶随手画了一个线条,看上去很像他最新设计的巴西尼泰罗伊博物馆门前那尊裸女塑像的轮廓。‘我不知道你躺在沙滩上是什么样子,但这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摄影师一下脸颊绯红。”
尼迈耶从未掩饰过自己对女性身体的热爱,那是他不竭的灵感来源。虽然他21岁结婚,和妻子安妮塔巴尔多一直厮守直至2004年她去世,但他的风流韵事一直没有中断过。2006年,尼迈耶99岁的生日刚刚结束不久,他和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女秘书、60岁的维拉卡布雷再次结婚。英国爱丁堡大学视觉文化系教授理查德威廉姆斯曾在2000年因为要写作一本巴西文化方面的书前来采访尼迈耶。“我惊讶于他表现出的‘力比多’,要知道他已经93岁了。在他的桌子旁边挂着一幅日光浴者的照片,我们的谈话一次又一次回到了那幅照片的美学意义上。我想让他回到正题,似乎是件绝望的事。”后来威廉姆斯将卡诺阿斯住宅作为他《欲望的空间》(Room for Sex)一书的案例。由于那片曲线柔美的游泳池和玻璃房,卡诺阿斯住宅成为当代许多MTV、电视和电影的取景地。在这些片子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身着泳装的热带美女在池边或坐或卧,或在阳光下撩拨池水。“毫无疑问,卡诺阿斯住宅、科帕卡巴纳海滩以及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一起建构了人们对巴西是情色天堂的想象。”威廉姆斯这样写道。
乌托邦的梦想
1953年,卡诺阿斯住宅建好之后,尼迈耶和家人搬到了这里。这个僻静之所不久就成了文化圈名流经常聚会的地方。1956年9月的一个清晨,卡诺阿斯住宅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刚刚上任的巴西总统库比切克。两人结下友谊是在“潘普利亚”住宅区建造的时候,那时库比切克是贝洛奥里桑特市的市长。总统激动地对老朋友说:“我将为这个国家建造新首都,而我需要你的帮忙——奥斯卡,这次我们将一起创造巴西的首都!”库比切克决定把巴西的首都从东南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中部高原上的一片荒凉之地,以带动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中西部高原实现现代化。那时候的巴西处于经济腾飞、文化繁荣、言论自由的盛世,文学领域的“具体诗歌”、音乐领域的博萨诺瓦、电影领域的“巴西新电影”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巴西人民在工业现代化和文艺现代主义两个维度上同时飞奔,梦想着巴西能够迅速崛起为大国。尼迈耶欣然应允,因为这一计划也高度符合他的老师柯布西耶在其《灿烂之城》一书中所表达的观念——现有的所有城市都是垃圾,混乱、丑陋、毫无功能性,必须从零开始按照严格的功能规划和非凡的美学诉求缔造全新的城市。
科斯塔执掌新首都的整体规划,尼迈耶负责设计其中主要的公共建筑。为了建设新城,尼迈耶离开了卡诺阿斯住宅,搬到了巴西利亚的工地上。“我和一些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被称为“甘坦戈斯”(Candangos)的建筑工人一起住在简易房里。一张床,一个壁橱,一个小盒子,一张沙发,一张桌子以及四把椅子,那就是房间里可见的全部。”那段时间尼迈耶工作辛苦又很快乐。“我们和工人们一起跳舞,去同一家小酒馆。那是一个解放的时刻。似乎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孕育而生,所有传统的藩篱都消失了。”1960年4月21日,库比切克在这座城市的落成仪式上将职位转交给了下一任总统。也就是说,巴西利亚从开始建设到落成仅用了三年零一个月。
尼迈耶将脑海中更多的曲线建筑化为现实:巴西国会大厦,意为“人”(Humano)的H形主楼的前面是两个巨大的碗状曲面,向上的碗是众议院,象征民主,向下的碗是参议院,象征集中,而H形主楼中缝的“一线天”恰好可以看见其后的国旗塔;巴西利亚大天主堂,由数根纯白的弯曲立柱支撑出一个标准的皇冠形建筑,立柱之间是大片大片的彩绘玻璃,进入它的道路要经过晦暗的地下,但只要一走进教堂,任何一个角落都洒满了耀眼的阳光;总统官邸曙光宫,离奇的曲线外饰颇似一条条吊床相连。除了国家大教堂、三权广场,巴西利亚大多数建筑都刻上了尼迈耶之名,走在巴西利亚街头,你甚至会有些“尼迈耶审美疲劳”。
1987年,这座年轻的首都启用不过27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它给尼迈耶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让他成为巴西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晚年的尼迈耶对巴西利亚充满了失望。当年,他把巴西利亚城区内的居民小区都设计成外观没有任何差别的楼房,因为他是巴西共产党党员、一个根深蒂固的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他认为所有这些居民楼都应该是国有的,国家把它们租给在首都工作的人员,不管是部长还是清洁工,都应该平等地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不能有穷人区、富人区之分。就在迁都4年之后,巴西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军政府时期,独裁者们摈弃了尼迈耶的初衷,在巴西利亚市内那个巨大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南北分别开辟了南湖区和北湖区两个富豪别墅区,并把30万兴建巴西利亚的底层劳动者全都赶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破败的卫星城去定居。当巴西利亚庆祝它建成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102岁的尼迈耶看着电视直播黯然神伤。“新首都巨大的社会分裂让我痛心。”他说。
至于卡诺阿斯住宅,尼迈耶和家人没有再回去居住过。“父亲去建设巴西利亚后,房子一下清冷起来。那又是当地唯一一栋住宅,生活很不方便,我和母亲就搬到科帕卡巴纳的一处公寓里了。”尼迈耶的女儿安娜回忆说。她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之后军政府上台,尼迈耶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欧洲,直到1985年才重新回到里约热内卢。今天,在卡诺阿斯住宅中的陈列没有恢复当年那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而是在木质墙壁的基调上,配上一些尼迈耶在巴黎流亡时期亲自设计的经典家具:起居室里有一张沙发,两把1978年设计的具有未来风格的“ALTA”休闲椅,一张尼迈耶饭桌“Pau-Ferro Wood Table”(1985)以及一张躺椅“Straw And Wood Chaise”(1974)。楼下的卧室里还有一把名为“Rio Chaise Longue”的摇椅,这是他和女儿在1987年共同完成的。
在2010年的圣保罗双年展上,巴西独立电影导演塔玛圭玛雷斯放映了一部12分钟的短片《卡诺阿斯》。它就在卡诺阿斯住宅完成拍摄,片子的创作灵感来自她第一次来住宅参观时联想到的在巴西文艺的黄金时代穿梭于此的香衣鬓影。短片围绕着一次卡诺阿斯住宅中的鸡尾酒会展开:其中既有酒会上跳着桑巴舞的社会精英们关于巴西种族和阶级关系的调侃,也有房子里服务生之间的讨论,借此说明正是这些隐匿于现代主义体制背后的工人维系着此类高雅文化的存在。不过和短片中的批判有所不同,卡诺阿斯住宅在当时的另一惊世骇俗之处是它没有为佣人设计单独的通道和出口,并且它的墙壁和房顶一度还刷成了黄色和红色,用来向里约热内卢那些壮观的、五颜六色的贫民窟致敬。尼迈耶从小就为家里佣人被不公平对待感到耻辱,正像巴西利亚城市建筑的设计一样,这处卡诺阿斯住宅也寄托了他众生平等的乌托邦梦想。
(主要参考资料:文章《100岁的奥斯卡尼迈耶:越老越神奇,越老越强硬》作者胡续冬;The last of the Moderns, New York Times, by Michael Kimmelman;The Curves of Time, by Oscar Niemeyer; Oscar Niemeyer: A Legend of Modernism, edited by Paul Andreas and Ingeborg Flagge。感谢实习记者郭木容和王馨逸的资料整理工作) 巴西文化博物馆设计尼迈耶建筑设计建筑柯布西耶自私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