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搬走的童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戴月(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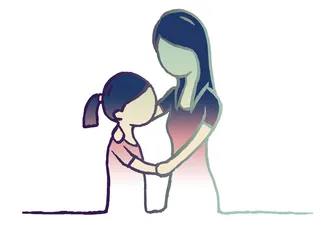
12岁前,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种地方,所有人的生活总是掺和在一起。每天一睁眼,我就能看到全院几十口人在忙活,人们蹲在公共水龙头边刷牙洗脸,大声地咳嗽吐痰,煤气灶上的烫饭被煮得咕嘟咕嘟翻滚,清晨的阳光刚刚照进东边的小门,不停地有人穿过这稀薄的光线进进出出,出去的端着马桶,回来的手里拎着金黄的油条。
“海鸥啊,烫饭都潽了,不晓得关一下啊,这么大的人啰,死尸啊!”
哈跃美又在骂她二女儿。
我们两家是隔壁,当中有一间共用的堂屋,也是两家的厨房。基本上他们家的烫饭煮潽了,我就知道应该起床了。而一到周末的夜晚,我必将在他家哗啦哗啦的麻将声中沉沉睡去。我一点也不嫌吵,和地板下老鼠的啃啮声比,虽算不上天籁,但足以让我幸福地睡着。半夜醒来,耳边仍然是这哗啦哗啦的声音,又提醒我不仅尚身处人间,隔壁还人气爆棚呢。于是,翻个身又睡着了,那是一种宁静的吵闹声。可惜的是,他们家一星期只打一次麻将。亲家母来也会打,但亲家母轻易不来。输赢自不用问,全在早饭上。如果一早就差海鸥去买小笼包,笃定赢钱,假使早起只有四碗白烫饭加一碟黑黢黢的大头菜摆在桌上,那就输大发了。
海鸥他爸叫徐金财,明显对她更好些。我经常听到他站在院子里,朝楼上某个方向大喊:“海鸥,下来吃糖哦!”“海鸥,小笼包子买回来咾!”咚咚咚的下楼声中,14岁的海鸥姐姐,乌黑的短发,亮闪闪的眼睛,一阵风般地冲下楼来,笑容在她脸上发亮。倒是她自己更像一块巧克力太妃糖。
“糖呢?”
“来,择菊花脑。”嘴边挂着坏笑的爸爸递过来一篮子菜,再也不提糖的事儿了。
我爱死他们一家人,恨不得从早到晚都待在他们家,他们家的一切我都喜欢。地板总是擦得发白,光脚丫的时间比哪家都长。饭特别好吃,徐叔叔炒得一手好菜,而且他很喜欢做饭,每天都会弄一样好菜。不像我们家,周末都不见得有好菜。他们家里屋还有一台冰箱,我特别享受打开冰箱门,再松手,听它“嘭”的一声关上。我喜欢冰箱,因为它总让我感觉自己和“高级”有了某种关系。为了争取这样的机会,我总是在海鸥炒菜的时候站在她旁边,一遍遍地问:“要鸡蛋吗,我帮你拿鸡蛋吧?”
徐金财怕他老婆,看见哈跃美就笑嘻嘻的,张口闭口老婆长老婆短。多少年后,当我看到书里有“胁肩谄笑”这个词,立刻就想起他来。别看俩人总骂孩子,他们自己并不吵架。我那时总疑心,要夫妻关系好,老婆就得漂亮,孩子非得讨厌。可我父母偏不讨厌我,他们只讨厌对方。
徐金财爱喝酒,哈跃美不让他喝。他有一个很小的酒壶,藏在身上,偷偷拿出来嘬两口。有一次,被他老婆当场捉住。一个上去抢,一个拼命躲,两人扭在一块儿,我们乐得拍手起哄。徐叔叔见势不妙,操起酒壶纵身往门口逃去,哈阿姨哪里肯放过他,撩起大长腿就追。两人一前一后跑出院子,一头扎进大门外的小巷,眨眼间拐进了另一条小巷,不见了。孩子们跟在后面叫着跳着,笑得东倒西歪,海鸥和海燕像拉拉队员,一个劲地喊:“爸爸加油,妈妈加油!”没过多久,徐叔叔被他那美貌的老婆押了回来,人赃并获。“往哪边跑啊,不晓得我以前练过长跑啊?”他们以前好像是中学同学。
孩子们都很开心,看两个大人冒傻气,可不是常有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好玩,笑过以后心里升出羡慕,羡慕海鸥和海燕喊爸爸加油、妈妈加油时的样子。我很清楚,她俩的开心与我的是不一样的,而我心里有一种难过是她们没有的。
如果我能遇见当时的自己,会拍拍她:“没得事,你看,你家姐姐我现在不是蛮来司的嘛。” 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