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蒜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孙君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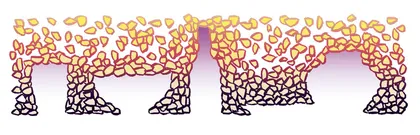
听说一些人一辈子都不愿吃大蒜,我感到怪哉。因为他们觉得蒜味太臭,可是我在吃的时候偏偏觉得其香,只不过单独吃时会觉得辛辣,那种味道是冲,可用两个词来形容:“峻烈”和“粗放”。老家有句话:“葱辣鼻子,蒜辣心,韭菜辣住脊梁筋。”每一次辣到心,我都不知道蒜是怎么做到的。事后我并不恼蒜,也不会抱怨“算(蒜)你狠”,盖因为大蒜对我太亲切了,它伴随我的时间还长着呢,我爱它,离不开它。
小时候,能吃、好吃的东西不多。家里养着猪、羊和牛,但猪羊是用来卖钱的,牛是用来耕田的,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猪肉。炒肉前,母亲都会到菜地里拔来葱蒜韭,没有葱韭,则一定有蒜苗,用蒜苗炒出来的肉毫无例外带有特殊的香,去了肉腥味,还有助于消化。后来才知道蒜苗和大蒜头里含有蒜素,能跟蛋白质很好地结合起来,蛋白质的结构发生变化后,肉类蛋白质就较容易吸收。
母亲至今不了解这个道理,却养成了以蒜炒肉的习惯,她坚持在9月里播下蒜种,在来年六七月间收获品质最好的大蒜,在炒肉时总不忘配上一株最新鲜的蒜苗或者几瓣最出味的蒜头。没肉可炒时,母亲则把蒜苗洗净、切段,拌上盐,滴上芝麻油,当佐菜吃,佐馒头、佐面食,每次都吃得酣畅。这还不算最强悍的吃法,有时候会拔根蒜苗,洗罢也不切,直接用门牙斩断吃掉。乡野里缺少文气,常常遭人笑话,但遍地都是尘土泥、“坷垃蛋”,我们没办法不率性粗放。生吃蒜苗的最佳时间在春天,万物复苏,人体里的毒大概也醒了,而生吃蒜苗最“败毒”。母亲每次要我们吃蒜苗时都爱强调这个词,后来我在中医书里也翻到相关说法,说蒜“下气、消谷、化肉、除风邪、杀毒气”。
我一直相信母亲那样的农民是人世间最忙的人,种庄稼收庄稼、生养孩子、做饭炒菜洗衣、喂养家禽家畜和流浪的猫狗、扫院子擦拭家具、帮自家的男人吵架流眼泪争个“一碗水端平”⋯⋯当农民难,当个做妻子的、儿媳的、母亲的乡下女人更难。我的母亲永远那么忙,做家常菜也极好吃,竟始终没有“休闲心”变出更多花样。这土生土长的大蒜,越到后来我越知道是个宝,是药食两用珍品。母亲认识字,能看书,大概也了解一些“生活小百科”。小时候,除大蒜炒肉、凉拌蒜苗、腌蒜薹外,我却从未见母亲做过什么醋蒜瓣、腊八蒜、大蒜酒。孩子们没吃过喝过,母亲自然更没享受过。很久以后,我在朋友家里吃到腊八蒜,不是常见的白色,而是神奇的绿色,还喝到美味的大蒜酒,也见到有人用蛋黄粉法和乳粉法加工大蒜,说这样的大蒜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臭”,是文明的吃法。我承认食蒜者能够遮一遮口气中的蒜味,的确很礼貌,然而一想到乡下的母亲,我还是感觉心酸。她爱吃大蒜,方法简单粗放,至今不清楚怎么减弱嘴里的蒜味,便那样去接近自己的牛羊、亲人和邻居,好在没人嫌弃她,田地里的庄稼也不嫌弃,乡下天大地大,风刮起来也没障碍,多一口蒜味又有什么关系?
母亲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不知道大蒜是“舶来品”,不知道古人写给大蒜的“赞美诗”,不知道西方人拿大蒜驱邪的传说⋯⋯可是她并不笨,也知道大蒜不单单用来吃,在夏天会咬断一个个蒜瓣,将大蒜汁抹到蚊虫叮咬的地方,让孩子们睡个好觉;知道蜂蜜配大蒜的民间小偏方,煎成汁,叫我趁热喝,几个月后,治好久咳不止的老毛病。她还知道去看望信佛的老人不能吃大蒜,因为他们说大蒜归属荤菜⋯⋯
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葱属植物胡蒜(大蒜),这么多年一直生长在老家的菜地里,没施化肥、农药,长得极好,也依旧那么“臭”,让一些“装蒜”的人三缄其口、退避三舍。不过这能怪大蒜吗?专家也发话了,称强烈“蒜臭”恰恰是大蒜存在效能的一个表现,而生吃的效果最快最好。大蒜性子刚烈,骨子里却讲道理,害怕它的人越使其温驯,它也越不是它。也许正因为大蒜太“臭”,不够“高雅”,古人写给它的“赞美诗”并不多。找来找去,找到一句“山市冰难致,家园蒜自珍”,心头不由一热,仅这一句也比那些“银蒜押帘”的句子好太多。 食蒜大蒜蒜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