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的家乡味道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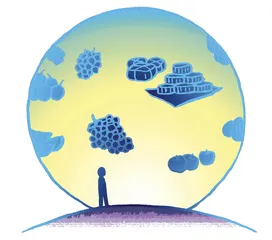
在我的家乡,中秋节简直就叫作“八月十五”,过八月十五是仅次于过年的重大节日。
自古流传下来,中秋都是吃的好时节。小时候,盼八月十五,主要是盼月饼。早早的,家里就开始打月饼了。月饼耐放,不像端午的粽子,吃不了几天,月饼可以连吃一个月。对于一个从未在我的家乡生活过的人来说,家乡的月饼根本不能称之为月饼:没有馅料,碗口大小,一指薄厚,只是面粉、鸡蛋、红糖、胡麻油和好了面,在饼铛上烤熟的饼而已。但这月饼是棕红色的,松软香甜,好像怎么也吃不腻。
印象里,中秋前就会有不少打月饼的铺子。把面、鸡蛋、油、糖提供给打月饼的铺子,再交一笔加工费,月饼就由他们代做了。等做好了,存储在瓷坛里,这就算一个月的早点和闲掰儿了。
除了这种无馅的月饼,还有一种有馅料的,叫提浆,但提浆自己做不了,得到点心店去买。很久,我一直以为月饼就是月饼,提浆就是提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后来到了北京,一次在“桂香春”见有提浆卖,问及服务员,才知道“提浆”只是制作月饼的一种工艺。小时候的提浆,主要是送礼使的。五六块摞在一起,用纸包了,顶上覆一张红纸,用纸绳捆扎了,高高耸起,方便提着,又十分好看。吃了自家的月饼,又吃到别人送来的提浆,这个八月十五过得才算完满。仔细回想,小时候吃过的提浆就是这两年被不断吐槽的五仁月饼,咬开了,能吃到青红丝、花生仁、芝麻之类,有时间或会咬到几粒饼糖渣。可能这提浆是小时候的美食,美好的记忆被胃给牢牢记下了,时至今日,有馅的月饼我只爱五仁一种。至于各种皮薄如纸、馅料甜腻的“正宗”月饼,我是不大敢过问的。
还有一种有馅的月饼,也是五仁的,八寸到一尺大小,叫作“月光”。十五当晚,皓月当空,家家要有拜月的仪式。拜月,早没了实际的意义,只剩下了供月一项仪式,也主要是图孩子们一乐的。供月的主角就是“月光”,天上一个月亮,桌上一个月亮,两相辉映,光这个想法就够美的了。月光清辉洒在桌上,“月光”就放在桌子中央,水果罗列在四围,西瓜要切成花篮形状,苹果、桃、梨、葡萄等洗得干干净净,盛在盘子里。孩子们盼着拜月,一旦供品摆上了,又盼着拜月早点结束,因为急着吃水果呢。别的倒罢了,主要是葡萄。一年中大概只有这时才可以尽情地吃葡萄。葡萄难得,中秋前买来的葡萄一定要等着先供过了月,才能吃。您想想,看了那么久,念了那么久,忍了那么久才吃到的葡萄,那得多香!
八月十五还有一种特别的水果,冰果。这种果子并不好吃,又干又涩的,但样子好看,比国光苹果还小些,颜色紫红透亮,闻着有一股特殊的香味。中秋前买来的冰果,要和打好的月饼一起放在瓷坛里保存,这样月饼就不会发干,吃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果香。等月饼吃光了,把冰果咬开,就不再干涩了,反而有了一点绵甜。
供罢月亮的水果是孩子们的最爱,“月光”却是母亲最重视的。母亲将“月光”按照家人的数量,平均分开,每人一份,不管爱不爱吃,有没有肚子,这份特殊的月饼一定要吃掉。八月十五是团圆的节日,“月光”分食了,说明家里人都在。1999年我离开家上大学,就没有再和家人同时分享过“月光”。虽然供月的程序渐渐免掉了,但分食“月光”一项母亲一直保留着。每年寒假回家,头一天的早点,一定是冰箱里存了好久的“月光”。姐和我先后结婚,母亲的“月光”也越切越细了,因为家里添了姐夫和妻子。等我有了儿子,又有了他的那一份。
母亲去世前的那个冬天,来北京看病,还特意带来了分属于我、妻和儿子的“月光”。妻象征性地吃一些,她爱吃的不是这个口味,儿子还小,不能吃。我知道,这“月光”本来就不在味道,当着母亲的面,我把所有都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母亲离开后,连分食“月光”也免了。家乡的月饼有几年没吃到了,八月十五就再也不过了,充其量是在忙碌的夹缝中,吃一块不知什么味道的月饼,算是过中秋了。
(文 / 白俊峰) 味道家乡葡萄中秋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