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野博物馆
作者:李晶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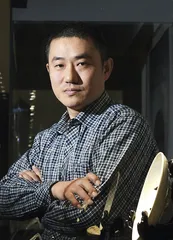 ( 阎焰 )
( 阎焰 )
4年前一次与朋友的会面,让阎焰决定做一个关于山西陶瓷的展览。“当时见到一位相识10年的朋友,聊天中讲到我在山西的经历,他动员我做有关山西陶瓷的展览。”阎焰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他说到“晋善晋美·三晋窑火——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特展”的缘起:“我说试试看吧。之后跟国内外的一些学界朋友,包括一些文博单位的专业研究学者咨询,他们给我反馈就是很难,非常难。”
在阎焰看来,展览的难度在于此前没人做过细致梳理,大家认为山西陶瓷基本上被划入华北陶瓷这个大范畴,同时被划入几个特定的窑系,如磁州窑系、定窑系,山西陶瓷划进去以后就被忽略掉了。同时,阎焰认为,山西陶瓷没有太大的量,包括博物馆馆藏的,如山西省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加起来也就几十件,这样的数量不可能做专题展览。阎焰说:“我重新整理了境内外的出版图录,包括历年一些学术研究的图录和报告,很多东西并非像想象的这样,我突然发现这个量实际上很大,世界范围内收藏的山西陶瓷,明确出版的肯定是上千件,国内的考古发掘报告能确认的大概也在这个数量以上。”
于是,4年后,2013年6月,阎焰在深圳展出了收藏的230余件山西陶瓷,此次北京展出精选出的130余件,贯穿宋、金、元、明、清数个朝代,涵盖了从北向南大同窑、怀仁窑、介休窑、霍州窑、长治窑等众多窑址,重现了12至19世纪山西窑业兴旺的全貌。阎焰说:“从表象上看,普通观众可能一眼分不出山西陶瓷和其他地区陶瓷的区别,但实际上,山西陶瓷的造型、釉色、纹饰、工艺等均有独到之处。如一件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这种粉色工艺的使用多见于介休窑,是山西窑场独特的装饰技法,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山西瓷器大量以煤烧制,不同于南方以柴烧制,山西出土瓷器明显带有北方风貌,窑工技法精妙。如一件金代长治窑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圆腹长颈,通体黑釉,釉面施白色化妆土粉,在白粉表面勾绘红绿彩,这种技法于12世纪时在北方窑场出现,是当时窑场工匠的创新。
阎焰指着一个产自大同窑的黑褐釉贴草叶纹缸说,窑工们会在施釉时随手用花叶遮盖,在釉干前,把花叶从陶瓷上再撕下来,这样,树叶纹理就会留在陶瓷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所以这些陶瓷也各不相同。一些窑工还把剪纸贴上去再撕掉,让剪纸之美与陶瓷之美相得益彰。”阎焰很喜欢山西陶瓷中的老虎枕,这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其中一件赭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还有两句诗:“闲吟古调敲龙角,醉卧青山枕虎腰。”别有一番情趣。
 ( 磁州窑白地黑彩划花卷口瓶 )
( 磁州窑白地黑彩划花卷口瓶 )
阎焰祖籍河南洛阳,他的收藏与家世不无关系。祖父阎少显是国民党报业的负责人,管理着9家报社,包括现在河南《大河报》的前身,民国的时候叫《大河日报》,以及上海的《中国新闻》等。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阎少显因级别很高,获得三张机票,但他提出家人全去他就去,否则便留在大陆,因此将三张机票作废。之后没多久“反右”开始,阎少显被抓,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一九四二》那个故事里有个人物和我祖父很像,他是当时中央赈灾委员会派到陕西去赈灾的主任委员,他代表行政院去的,那里边很多情节都跟他有关联,他当时到西北去一次要几十万银元的赈灾款,中央政府当时不大愿意,他最后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给当时的国民政府。”阎焰说。
阎焰的父亲阎正酷爱书画,自1958年起,创作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十几部,并与众多艺术家和画家相熟,如赵广云、石鲁、何海峡、李可染、李苦禅等。因此阎焰常能看到父亲的朋友在家挥毫做画,耳濡目染,从小对艺术和收藏有了兴趣。
 ( 磁州窑白地黑彩划花篦纹罐 )
( 磁州窑白地黑彩划花篦纹罐 )
阎焰最开始收器物是古钱币。“80年代前,古钱币不要钱,去废旧物资回收站多喊几声老大爷,就能拿到一些。”阎焰说,“当时感觉特别稀奇,以前书上印的‘开元通宝’,和我从废品站要来的一模一样,很有意思。有时也会跑去剪人家卷门帘的钱币,通常这些都会比较特别。”
阎焰在80年代初收获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在今天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这本书叫《废旧物资回收目录》,是70年代中国首饰公司油印的,属于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大型收购站的专业目录。里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我们要大量收购,出口换汇,出口一辆自行车,不如出口一个翡翠”。类目分得清楚详细,阎焰印象很深,超过30余类,如陶瓷、钱币、金银、翡翠、玉、玛瑙、珊瑚、珍珠、碧玺、丝织品、皮箱、皮鞋、皮袄都有,分得很清楚,漆木竹刻都有。这些收购点属于代购,收完后分类,再转售给国家。阎焰说:“现在的玉,一件就卖上几十万、上百万元,以前是用簸箕铲,然后上秤称,论斤卖。”
 (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鸟纹倭角枕 )
(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鸟纹倭角枕 )
靠着这本图录,阎焰知道瓷器也是有价的了。他的第一件收藏是同治粉彩花瓶,当时花了5毛钱跟一个卖冰糕的老大娘买的。“老大娘跟我说,这个花瓶是我妈结婚时留到家里的,我现在绝对相信这个老奶奶没有骗我。下面有一个红色的方戳,我们现在都叫橡皮戳,上面写的就是篆书‘同治年制’,上面画花卉。”
阎焰笑说,自己的收藏和学术研究是从破烂垃圾开始的。“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废旧物资收购站买到很重要的一本研究类书籍,对于我一生都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文物资料》,这是《文物月刊》的前身,‘文革’期间停刊,‘文革’结束后是第一批复刊的期刊。”阎焰通过这本刊发现自己收藏的东西原来有人专门研究,他说:“我买的很多东西在那里面都有介绍过,比如铜剑、钱币、带勾、铜镜、玉璧,书上都有。”于是他开始有目的地对照这些文物的价值和特定的历史材料去筛选。
 ( 磁州窑白地黑花蜻蜓纹倭角枕 )
( 磁州窑白地黑花蜻蜓纹倭角枕 )
有了方向,一切便都光明起来。阎焰生平第一次踏出河南,来到了山西。阎焰说,那会儿朋友带着去山西,东西多到你买不完,只能有选择地买。当年一个30多厘米的青花盘子也就3块钱,现在要卖几万、几十万元,好的卖个几百万元也不稀奇。当年叫瓷器一毛,不值分毫,就是说这个瓷器一旦毛了边,或者有冲线,有磕碰,就不要买了,没有任何价值,不像现在残器都能卖出天价。阎焰的众多藏品中很多都是当年在山西淘来的,也因此对山西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阎焰看来,他的收藏和很多人不一样,是构建在学术基础之上。他说:“我早年收过一件磁州窑的酒瓮,上面因为有天启的纪年,这对研究磁州窑非常重要。以前学术界认为磁州窑系的衰退时间很早,金元以后就没有了,而我这个瓮的出现,可以将磁州窑衰退的时间推迟到明代末期。因此我当时写下学术论文《磁州窑衰退年限考》。后来学术界的同行朋友都非常认同这篇文章。”
 ( 磁州窑白地黑花筒式缸 )
( 磁州窑白地黑花筒式缸 )
2003年,阎焰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天边的彩虹——10~13世纪釉上多色彩绘陶瓷研究》,这是一本关于12到13世纪彩绘陶瓷的专业书籍。“彩绘陶瓷亦叫红绿彩,这本书在国内外学界影响非常大,我今天在学界的位置,实际上和那本书是有绝对的关系。”阎焰很自信地说,“红绿彩在全世界收藏得很少,我们的收藏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并且得到国际学界公认。”
现在,阎焰在深圳有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望野博物馆。除陶瓷收藏外,还有佛像、玉器等。而阎焰也全身撤出互联网行业,专职经营博物馆。他赞同文物收藏一定要以商业为衡量,因为老百姓未必知道学术价值,他们更容易理解东西价值多少,以此为引子来启蒙百姓,踏过了这个门槛,再回头来看时,才知道文化的价值。
 ( 山西白地黑彩赭粉花圆枕 )(文 / 李晶晶) 博物馆陶瓷陶瓷行业望野磁州窑文化山西文化
( 山西白地黑彩赭粉花圆枕 )(文 / 李晶晶) 博物馆陶瓷陶瓷行业望野磁州窑文化山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