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问世500周年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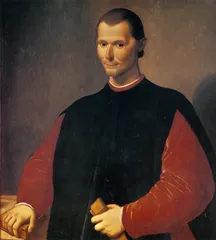 ( 马基雅维里 )
( 马基雅维里 )
《君主论》与奥巴马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写于1513年,直到他去世五年后的1532年才出版,但该书写成后就开始在佛罗伦萨人中流传。即使是如此小范围的传播,已经使马基雅维里成了“犬儒主义”的代名词。他的一位熟人在他去世时评论说:“普通人因为《君主论》而恨他;富人认为《君主论》教导君主拿走他们的全部财产;拿走穷人的全部自由;好人认为他有罪;坏人认为他更坏。”在19世纪以前,《君主论》的内容一直被视为谬论。1559年颁布的教皇禁书目录中,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排在第一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一般人惊讶于马基雅维里的荒谬绝伦,已成惯例,他有时候也的确是荒谬惊人。”但到了20世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较会赏识马基雅维里,因为当代有一些最可注目的成功,都是仗着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使用过的那些卑鄙的方法取得的。”
2013年1月,《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问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如果他可以要求奥巴马总统看一本书,会是哪一本?他说会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今天马基雅维里经常被斥为一个不道德的犬儒,认为目的能够为手段辩护。实际上,马基雅维里是知道权力的界限和用途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基本点是,区分了意大利语中的Virtu和Fortuna,它们的意思不是美德和运气。Virtu指的是政治家通过他的行为能够影响的范围,Fortuna指的是政治家不能控制的意外。马基雅维里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后者好比无法控制的洪水,前者好比预见到洪水后采取的保护性措施。面对霉运我们并非毫无办法,政治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预见到哪些会出问题,并制定应急方案。每一位总统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读马基雅维里的书,吸收他的思想。”
接着,2013年2月7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说:“传统观点认为,马基雅维里说,既然人们很残忍,那么怎么做都是许可的,领导人应该不计一切地保住自己的权力,目的能够为手段辩护。但实际上,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很讲道德的思想家,他很动人地写到了他对佛罗伦萨的爱,他关于伟大、统一的意大利的展望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他几乎每一页都会呼吁荣誉和美德。”
布鲁克斯说,马基雅维里只是拥有一个不同的政治美德观。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实践基督教的美德,如慈善、宽容和温和,又能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那当然很好。但是在现实世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在真实世界,领袖要创建文明秩序,为了创建秩序、击败无政府和野蛮力量,领导人被迫要做出艰难的抉择。由于领导人因环境所迫,要做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事情,马基雅维里希望他们做得有效率。马基雅维里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如果你不得不做一件残忍的事,那就迅速地做;如果你要做一件慷慨的事,那就慢慢地做。如果你要领导一个国家,你更应该担心诡计多端的精英们而非大众,你要努力跟人民结盟对付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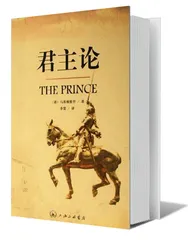 ( 《君主论》 )
( 《君主论》 )
布鲁克斯写道:“现在仍不可能两手干干净净地统治,仍然存在着恐怖分子,藏在暗处,所以,今天的领导人也面临着马基雅维里般的选择:为了保护我服务的人民,我要不要很残忍?我要不要使用有时会杀害无辜儿童的无人机来挫败恐怖分子,拯救自己人的生命?当奥巴马还是一位议员时,他无需面对领导人的残酷逻辑。现在执政后,他被扔进了马基雅维里式的世界,他正确地决定了,无人机是打击恐怖分子的有效手段。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有一个核心缺陷,他过于相信领导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他对我们说,人是腐败的自欺者,但他又允许君主干坏事,相信他们不会变成恶魔。美国的国父们更加小心,他们知道领袖很腐败,不可信任,他们讨厌集中的权力,建立了权力的制衡制度以分散权力。”
《君主论》中的两种世界观
30多年前,以赛亚·伯林说,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的解释浩如烟海,且迅速增加,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说柏拉图、卢梭、黑格尔的观点会令人们感到困惑,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这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柏拉图的著作距我们更久远,用的又是一种我们说不准的语言;卢梭、黑格尔都是多产的理论家,他们的著作不是明晰、融贯的代表。但对《君主论》的解释如此纷繁就令人不解了,首先它很薄,其次它是典型的清晰的文艺复兴文体。伯林认为,马基雅维里之所以不停地引发各种解释,是因为他在读者头脑中并置了两种世界观、两个不相容的道德世界。“他非常诚实、清楚。选择了政治家的生活,甚至公民的生活,希望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地成功、繁荣,人们就要拒斥基督教的道德观。除开社会和政治背景,基督教关于个人灵魂幸福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是国家的幸福不同于个人的幸福,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统治。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唯一的罪行是导致你中途退却的软弱、怯懦、愚蠢。”
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里是教授邪恶的老师,但有许多学者认为马基雅维里是共和主义理论家。美国学者菲利普·伯比特就属于后一个阵营。菲利普·伯比特2002年出版的《阿基里斯的盾牌》厚达900页,2008年出版的《恐怖与赞同》也有近700页。他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新书却只有200来页。为什么他在《朝袍和龙袍》中对马基雅维里的处理如此简洁呢?加里·威利斯说,这是因为他经常引述他自己的旧书,论述马基雅维里如何跟他更长的著作一致,就像马基雅维里500年前读过他的书一样。比如伯比特在《阿基里斯的盾牌》概括了自1500年以来的六种政体:君主、国王、领土、帝国、民族和市场。他认为马基雅维里解释了第一种政体。他认为,法律体系是通过军事策略来改变的,通常是军事技术。所以,在1494年,当查理三世把大炮带到意大利,威胁城墙以及以城墙为基础的政府时,马基雅维里提议建造新的城墙,以及保护它们的新政府。伯比特认为,这意味着马基雅维里对新的战争技术感兴趣,实际上他对要塞不感兴趣,认为要塞更易受到内部叛乱而非外在围困的攻击。马基雅维里在《战争的艺术》中提出了一些改进要塞设计的方案,但他关心的仍然是内部的叛乱。
马基雅维里感兴趣的是旧制度,尤其是罗马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强大,靠的不是新式武器,而是因为它们以Virtu为基础,即它们的宗教。这些宗教跟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要求人们谦卑、追求进入天堂,罗马的宗教却灌输对现世光荣和自由的渴求。基督教的仪式“装腔作势而不壮观,缺乏残忍的、充满男子气概的力量”,罗马的仪式则非常壮观,而且拥有残忍的牺牲精神,在仪式上会宰杀许多动物,以这种吓人的方式使人们受到惊吓。
伯比特说,《君主论》是一部宪政论文,探讨的是从封建主义向君主国家的转变。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之所以很现代,是因为它的国家观,是封建主义所缺少的,封建主义是一个缺乏主权的体制和权威网络。马基雅维里提出的建议适用于政治领域,君主的最高义务是保护和促进共同善,现代君主不能根据他们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来统治,他们运用的权威要求他们放弃普通的道德。马基雅维里鄙视美德,是由于他肯定了统治国家要求的义务。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伯比特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种解释很新颖,关心现代政治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启发,但是伯比特显然把现代尤其是美国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投射到了一位古代作者身上。他像福山一样,认为现代历史必将走向以美国式的世界秩序。跟福山不同的是,伯比特强调只有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战争才能推进这一过程。
福山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对伯比特新书的评论。他说:“马基雅维里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因为他是自由宪政的先驱。他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跟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一样,指出了自由宪政的局限,指出它最终要依赖于有品德的君主,依赖于审慎而非政治决策中的规则。曼斯菲尔德好像是多年前就瞄准了伯比特现在提出的解释:我们乐于认为可以在保留马基雅维里的洞见的同时,丢弃他的极端主义。马基雅维里也许发现了执行权的现代原则,但是他没有提出分权的原则。不能因为马基雅维里谈到共同善就说他是道德的,因为那种善的基础不是一种幸福生活观,它只是控制他人的手段。” (文 / 薛巍) 500君主君主论问世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