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 有时候“粉丝”让我很难为情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 罗永浩 )
( 罗永浩 )
罗永浩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但由于骨子里尚存一丝善良正直,因此他不得不为这一特质付出代价,他把更多的才华消耗在他成为网络明星之后的网络口水战中。他精力充沛地加入到每一次与其有关的争论中。从他这几年的经历中不难算出,在中国,你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能坚持做正确的事情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多少。但从他偏执倔强、出了名的小心眼儿的性格来看自己的言行,他的一套换算公式算出的结果告诉他:值得。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粉丝”了?
罗永浩:教书的时候吧。我2001年开始在新东方教书,上岗教书很快就发现有所谓的“粉丝”了,那时候还没在互联网上得瑟呢。是这样,每个班无论讲得多烂的老师都有“粉丝”,因为大班上课,300人,总有几个人看上你,即使你是个歪瓜裂枣。我当时头几个班讲得都不怎么样,下了课就有学生拿个笔记本上来说罗老师给签个名,我当时就脸红了,我想我又不是歌星影星的,怎么还签名呢,签什么名啊?我说不给签。我发现其他老师都给签,学生就说我装,结课了留个纪念都不给签名,太能装了。我就特别分裂,觉得签的话特傻,不签的话特装,就给折磨得不行了。后来三四期班下来以后就习惯了,觉得不好意思不给签,就给签了。签的时候还有男生起哄,比如围着几个女生签,男生就说,围着一群姑娘签名是不是感觉特高兴特得意啊。我感觉里外不是人,怎么都得让你们恶心一通。这是我最早对“粉丝”的印象吧。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候你对待“粉丝”的态度是抵触,还是说觉得别扭?
罗永浩:就是觉得别扭。既不喜欢也不烦,就是别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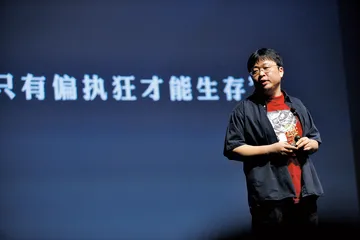 ( 老罗教学风格幽默诙谐并且具有高度理想主义气质的感染力,极受学生欢迎 )
( 老罗教学风格幽默诙谐并且具有高度理想主义气质的感染力,极受学生欢迎 )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时候觉得不别扭了?
罗永浩:后来讲多了,就跟别的尴尬一样,麻木了。后来课越讲越好,结课的时候“粉丝”就越来越多,有时候300人的班能围上100人签名,说实话挺烦的。我后来包括卖书给人签字的时候,会觉得出窍、走神,觉得我在别的地方旁观自己干这事儿。围着一堆人,你拿着笔,不停地写自己名字,这事儿细想特别像精神病,虽然这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仪式性的东西。
 ( 2011 年1 月22 日,贾樟柯(右)携《语路计划》主演罗永浩(左二)、周云蓬(左一)、张军(右二)做客《鲁豫有约》 )
( 2011 年1 月22 日,贾樟柯(右)携《语路计划》主演罗永浩(左二)、周云蓬(左一)、张军(右二)做客《鲁豫有约》 )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觉得像精神病?
罗永浩:拿着笔不停地写自己的名字本身就是特荒诞的一个事儿。你干吗拿着笔不停地写自己的名字呢?你既不练字,练字也可以练别的字。他们有需求,所以你就做了,但是重复的过程中会产生很荒诞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并不享受这些。
罗永浩:不享受。有享受的时候必须承认,比如说,跟一些朋友在外溜达,心情也好,又比较闲,过来个人打招呼说你是罗老师吧,能跟你合个影吗?等他走了,我就可以和朋友吹吹牛——你看,到处都是“粉丝”。这样的乐趣也是有的。但是我没有那么闲的时候,比如我急急忙忙赶路,追上一个人说能合张影吗,肯定是感觉被骚扰,这时候挺烦的。我要是自己走路,也很闲,过来个要求合影的,跟朋友吹吹牛的乐趣没有了,那就没什么意思。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理解现在“粉丝”的现象,过去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现在都是一撮一撮的“粉丝”。非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的“粉丝”有什么不一样?
罗永浩:我觉得没啥区别,非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的“粉丝”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网络时代的变化就是,在非网络时代,如果“粉丝”很傻,他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少跟你交流的机会的。比如围着一圈人跟你签名、合影什么的,可能有些孩子特别傻,然后你也不跟他产生对话,也不交流,就是场面上的东西,对付过去就完事儿了,这时候很多东西暴露不出来。到了互联网上,你发一个贴也是围上来一大帮,每一个人说的都被留在网页上,这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有这么多特别怪,特别傻,特别人品糟糕,特别逻辑混乱的……各种各样的人就暴露出来了。但如果在围着一堆人合影的时候他并没有机会和你交流,所以没有问你傻问题,你回答了以后他也没有给你很糟糕的反应。这些体现不出来,它被掩藏了,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说这个我还想起来,很多人看到网上“粉丝”说的傻得没边儿的话,原则性、常识、基本道德底线都没有的话,老觉得互联网上冒出了很多妖魔鬼怪,实际上妖魔鬼怪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互联网给了他们一个表达的机会。过去他们也是有表达欲望的,他们的表达欲望可能表现在给电视台、电台或者杂志,给自己喜欢的专栏作家写信、发邮件,但这些东西是没有机会被发表到传统媒体上的,因为写得特别糟糕或者特别愚蠢,在处理读者来信的部门里就已经把它给过滤掉了,就显得没有这么多妖魔鬼怪。我倒是觉得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妖魔鬼怪的数量变少了,大家毕竟接触的信息多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过去变强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妖魔鬼怪就是因为他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罗永浩:对。有表达的欲望但又没有表达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谈到的,你有时候可以接受“粉丝”,有的时候又讨厌“粉丝”,你理想的状态下,希望跟这些“粉丝”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永浩:我希望是正常的人际关系,有常识的人际关系的相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也有很多偶像,我要在公共场合见到他,比如我在机场扶梯看到我的偶像,我看他显得心情还不错,手头也没什么事儿,既没在打电话,也没在东张西望找人,这时候我可能上去搭个话,这样我也挺高兴,这个心理我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他很忙碌,或者显得很烦躁,或者在东张西望找东西,或者在打电话,那我就不去骚扰他。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学,这是人际关系的常识。首先你上去跟他打招呼肯定是跟陌生人打招呼,不管你多熟悉他,他并不认识你,所以这是一个陌生人关系。你要去打招呼,或者搭一两句话,可能要考虑给对方造成的麻烦和不适感,我会去考虑,我希望别人也都有这样的常识就好了。我有时候碰到的情况是,比如参加文化交流,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进了卫生间,我在解手提裤子呢,就进来人打招呼。我想起来最悲催的一次是我在健身房,健完身体,冲完淋浴,一丝不挂去更衣室穿衣服,突然冲过来一个小伙子跟我伸手,说:你是罗老师吧,以前我上过你的课。要跟我握手,我就特别尴尬。你就不能等我好歹把裤衩穿上了再说这个话?这时候你就觉得他这件事处理得特别没有常识。
还有一次,我跟老婆出门路上吵架了,俩人都是鼻青脸肿,一边走一边还你一句我一句,傻子都看出来是明显两个人不高兴的状态。这时候正面过来一个人,还看我,我眼角看了一眼,也没理会。我感觉可能是认出我来,我和老婆还吵着架,结果他被我们甩在后面以后又追过来,在我侧面一边看我一边走,我眼角看见他了,但我还在和老婆吵,结果他还是冲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罗老师吧,能不能合个影,那次我就很难控制情绪,但我也没骂他,我就说你看错人了。我俩就继续往前走。他在后边犹豫了一下又追过来,我只好一路小跑,然后他就没再追。我希望大家相处上有人际关系的基本常识的话,就不会有这些尴尬。
三联生活周刊: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粉丝”跟他的偶像都能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状态。
罗永浩:我觉得没问题啊,我也有很多偶像啊。所以说他配套的还是缺乏人际关系常识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网上可能因为语言天赋,幽默感,以及当初录音传到网上,很多人喜欢上你了。当你看到纯粹是赞美你的话,心理上什么感觉?
罗永浩:当然高兴啊,又不会骚扰到我,谁不爱被夸,很高兴,非常高兴。
三联生活周刊:一被夸很高兴的这种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罗永浩:天生的吧,大家都有吧,小孩儿也是,大人一夸很高兴。谁不爱听好话呢。我会尴尬的是那种,你做了件事儿本来挺好的,结果下面围着二百个人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永远支持你。这时候我就会很尴尬,因为我是教书的,我老跟学生讲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结果讲了半天,围着一堆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就觉得被讽刺了。我办牛博网,这个网站两大主题:一个是科普一个是民主,这两个做了半天好多人还是说无论怎样我都永远支持你,我觉得挺尴尬的。这种好话我是不爱听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听好话的时候还有选择。
罗永浩:对,还挑挑拣拣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多数人在被崇拜的时候没有这种挑拣,觉得夸我的就是我这拨儿的,骂我的就不是我这拨儿的。
罗永浩:也分群体吧。娱乐圈可能顶他的他就高兴吧,通常是这样。但我觉得,像作家、知识分子这帮人也不一定这么没出息,可能也像我这样挑挑拣拣的。比如我跟人家论战的时候,只是基本观念不同,沟通或者吵起来,没有价值观对立,就是有个争执,我的“粉丝”扑上去就问候人家祖宗三代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尴尬。但是其实他也不是听你指挥的,因为他扑上去不是听你指使的,你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他也不会听你的,一个人和“粉”他的“粉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怪的。我跟一个人争执,那个人被我的“粉丝”骂了他会认为这些人是被我派去的。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不可能说:去,你们去干他。这种话既说不出来,客观上也不会那么做。但有时候公开说了产生了这效果的时候,也不是我劝他们不要怎么怎么样能解决的。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潜意识里你还是希望“粉丝”跟你站在一起的。
罗永浩:前提是大家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那我看到支持我的人会高兴。有时候我跟一个人争执,那人“粉丝”比我还多,这件事上我没什么不对,但他那儿扑上来很多人骂我的时候,我不会认为是那人的错,是他的“粉丝”的错。相应的我也希望我跟别人产生争执的时候是那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我有时候也是蓄意引导我的“粉丝”去骂对方的。他上来也没跟我讲理,就跟我直接骂娘,我要是对骂娘就会很吃亏,给人感觉,特别是我又做教育的行业,结果是,大家不看道理,就看谁风度好看,谁说话难听。所以我可能讽刺一句,根据以往的经验就会有很多人扑过去骂他,考虑到这个,我有意识做过这种事,这是必须承认的。对方有时候不是用真实姓名跑江湖的,有的人已经有了十几万“粉丝”了但只是个ID,根本没人知道这人真实身份是什么。那我用自己名字骂完了以后,别人会说你当老师的怎么这样,或者你公众人物怎么这样,各种指责就来了。所以我不回骂,但我会讽刺他一句,这样会有很多人过去骂他,会让他心情不好,这是我有意识地干过的。
三联生活周刊: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想没想过:我有一些影响,我稍微有一个眼神儿就会有一帮人扑过去替我去办什么事儿。
罗永浩:这样的时候肯定有啊,那个人来就不是和你讨论问题和沟通问题,他就是想羞辱和激怒你,但你被激怒以后回应他,人家就来骂你,因为他是个乌龟壳,没人知道他是谁,就围着骂你,我要是回骂就会很吃亏。但我又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不刺儿他一句我又难受。我就不带脏字的那种轻描淡写地讽刺他一下,回复一下,就会有很多人去骂他,这时候我是挺高兴的。这时候不是沟通问题了,他蓄意让我难受,我就以对我伤害最小的办法蓄意让他难受。
三联生活周刊:你开了学校之后,你必须考虑到一点,作为公共人物可能不能像以前那么自由奔放了。必须考虑商业利益和公共形象,这样你在对待“粉丝”的态度上跟过去比有没有变化?
罗永浩:肯定有啊,有些话原来可以说现在不方便说了。有些是政治的东西,还有一些跟政治无关的也是。比如过去在我的博客里,有人到评论里不讲理、胡搅蛮缠我会跟他对骂的,现在明显少了很多了,这是因为我做的职业,我被迫的。我不觉得脏话里有什么是非问题存在,你主动人身攻击对方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他人身攻击你,你用人身攻击回应他本身没什么错。其实正常人在生活里都是这么做的,包括指责我喜欢说脏话的那些笨蛋,其实在马路上被陌生人无端骚扰最后逼急了都会说脏话。我见过无数次从来不说脏话的人,碰到真正的流氓以后都会说脏话。结果他现在跑来指责我,在我被人家用脏话骚扰后以脏话回应时来指责我,我明知道这是没任何道理的,但如果这种笨蛋足够多,我就要为我的董事会、我的投资人和我的同事们负责。所以我说的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觉得心里堵得慌?
罗永浩:当然堵啊,憋屈啊。所以我希望我做的是另外的行业。比如我要做个艺术家,就没事儿。你要是个艺术家,整天骂骂咧咧的,大家还觉得这是性格。但是你要是搞教育培训的,要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人有问题。所以我就只能克制。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怎么去平衡这些?
罗永浩:就只能想开了呗,职业需求嘛,这很正常。就好像我们有些老师,她平时可能穿得很性感,很暴露,私下里没事儿,但讲台上可能不得体。我们对老师也有一些着装要求,让他们穿得相对朴素大方一些,不要上课穿个渔网装,上去亮肌肉,亮乳沟什么的。我把这个也理解成职业需求,就相对容易接受。但确实不舒服,不痛快。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连续几年成为搜索引擎里搜索率比较高的人物,这六七年究竟给你带来什么东西?面对越来越多的“粉丝”,你想没想过,一个小地方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了?
罗永浩:没有。我打小就自视甚高。就是啥也干不了也觉得了不起的那种,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就啥也不是的时候,也肯定是个什么玩意。打小就这么觉得。
三联生活周刊:当互联网逐步关注你的时候,是否对你曾经心里想过的东西是一种事实认证?
罗永浩: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在哪个领域取得一点成就,里边都有很大一块是自己的性格、实力的部分,也有很大一块是运气的部分。所以我特别讨厌那些成功学的大骗子,出来讲他的成就完全取决于他的一二三,他跟你讲他怎么努力,他怎么聪明,他怎么处理问题。这些可以谈,但回避运气偶然性这一部分对现实意义上的成功产生的影响是不诚实的。所以我这里边也有很大偶然性,我要去当歌手、当演员,这是奔着成名的路去的,最终成名的结果也是有合理性的。但你跑到一个教育机构去教英语课,这个肯定不是成名之路,对吧?但是竟然就有学生把你讲课内容录音并且把讲题部分全删掉,留下扯淡的、调节课堂气氛的那一部分,然后剪成了段子,还起了名,还打包一个文件夹,放到网上去。这些事本身是有巨大的偶然性的。第一个做这件事的孩子就很奇怪,后面人们去拷贝的不奇怪。我一直很好奇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直到今天,传的我早年的还都是他剪的那个版本。他如果没有做这件事儿呢,可能就没有后来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有很大的必然性。因为在他之前,录音在GRE考生论坛中,在清华水木BBS上等等那些地方,早就有了。是这个人相对无聊,把讲题全删掉,掐出来扯淡的部分,并且做了标题,才有了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剪出来的这个在校园BBS上也有了一年多,但也没有扩散开。但是,其中第一个爆发出来的那段是我批评户口制度的。刚好2002、2003年媒体有一阵集中在谈城市取消户口制度问题。它是社会的热点,同时讲得又很痛快,符合那时候很多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所以那一段是先扩散开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突然听我的朋友都跟我说,你红了,我在网上听到你的录音,到处都在传。我顺着他们说的链接去看,全是这一段,没有别的。但是这一段很快就带动了大家说“这人还有没有别的录音”。这样才全部扩散开了。所以你现在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看到,偶然性是特别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在新东方,那么多老师,为什么他们讲课的内容没有被当做段子传播开?
罗永浩:因为他们讲的不灵,根本就很烂嘛。他们还不服气。其实有很多老师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很得意的把自己最得意的部分剪了放到网上。而且他每年接触的学生也有几千人,自己的博客、微博“粉丝”也有上万,有一个很好的推广的基础和平台,但都没有扩散开。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怎么讲?
罗永浩:也是扯淡的。比如他要么是抄来的笑话,要么是自己编的笑话。但它只是个笑话。我的扩散开来的原因其实很复杂,除了听着好玩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也谈了一些社会问题,有实质的内涵在里边,并不深刻,但还是有内容的。他们可能只是个段子,就跟网上传的任何一个段子没有本质区别。我怀疑是这个原因,我也不能确定。但他们的东西我是听过的,包括他们讲的很多也被讹传套到我的头上了。比如说我见过文字版的老罗语录里有好几条都不是我讲的。比如上来跟学生说日本男人喜欢看什么,暗示是毛片,然后说日本女人喜欢拍什么,暗示是毛片。这根本就不是我讲的,但所有文字版的老罗语录里都有这一条。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心里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
罗永浩:话语权方面肯定是啊。
三联生活周刊:想去领导“粉丝”们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吗?
罗永浩:没有,不好意思,丢不起那个人。比如我要跟人争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他们帮腔的。但是我刚才举的那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过来辱骂我,也不想讨论问题,就是纯辱骂的时候,我小心眼生气了,被骂急了,但又不方便自己骂的时候,可能有意识地会引导。除了这个以外,我不觉得有任何需要他们帮我做什么事情的。从来没有。因为比如我和人论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灵,逻辑性、口才什么都很差,所以我不需要他们帮这个忙,帮的话只会更糟糕。
三联生活周刊:那如果说抛开这些,比如你在做一些别的事,比如维权?
罗永浩:那当然是需要啊,我需要一些信息。比如说我想到德国去,了解一下德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如何运作的,那首先我查到的英文资料就挺有限,我想看看德文资料我又看不懂。那我就想,我有120万个“粉丝”,这里边是就有在德国工作和留学的人,我发一个求助帖,他们如果给我一些相关信息,我就会觉得很好。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你潜意识里还是有一种领导意识的,只是你是用一种过滤的方式去领导。
罗永浩:当然。因为你在网络环境里,就已经跟他们有了一个认识的关系了。有这么个基础。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求助也会帮。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或别人认为,在公众中你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罗永浩:我觉得我做得最好的就是我原则性比较强,这是我自己最看好自己的地方。然后……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这是我自己比较认可自己的地方。公众眼里看,这个其实就很千差万别了。在很多“粉丝”眼里,他们只是喜欢我跟人吵架的时候凶巴巴的样子,就围着一堆乱喊“彪悍”什么的,这个我自己觉得是特别无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我跟人家吵的时候表现得凶巴巴,可能是我性格就那样。这个在我看来不是坏处,也不是好处,只是一个特点。这个我自己看着很不重要,但是认可这个的人特别多。但我注意到这样的人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他看到一个不讲理的人,说话特别掷地有声地不讲理的时候,也特别欣赏。虽然受到认可,但是完全没有价值。还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好玩儿”。就是幽默啊。因为喜欢我的人,我其实并不觉得他特别无聊、无意义或令人反感,但相对于我自己认可自己的优点,这个就不算什么了。大概就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自己在事业上和公众影响上有没有成就感?如果你有的话,支撑你有这些成就感的意识都是来自哪些方面?是你公司每年都会有进步还是“粉丝”在你身边越来越多?
罗永浩: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传播力方面的增加,这个对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商业上的不用提了,你在做公司,传播力越强,效益就越好。另外还有一些跟商业无关的,你原来想做做不成的,现在都做成了。我举今年感受比较深的一个例子,《美国种族简史》那本书,我在教学中发现特别好,总想推荐给我的学生。但这本学术书很多年前在中国出版过,只印了5000册,大部分都流传到二手书渠道上成废纸了。我总想让这本书再版,但是我没有能力去运作一个外版书引进出版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粉丝”多,影响传播力比较好,去年的海淀演讲结束后,我推荐过的几本书都成了畅销书。所以今年中信找我谈合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本书,我说“我不跟你们商业上的合作,这本书听名字就是本学术书也不会好卖,但我保证你们赚钱”,就要求他们把这本书在国内引进出版,他们就在我的要求下引进了这本书。这个书听名字怎么运作也就几千册的销量,了不得了,但是我在海淀剧院演讲后到现在已经加印了4次,印了8万多册,眼看就要印10万册了。基本上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一个外版书,又是非小说类的,到10万册已经是非常畅销的书了。在这方面我的“粉丝”多,影响传播力广,我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后面有一堆人支持你做事的话,会让你更亢奋,或者说,想把一个事情做得更有影响。
罗永浩:更亢奋其实倒通常不会吧。如果我在做一件事情,很多人嘴里很难看地在后面摇旗呐喊,我会因为他们而感到自己难为情。我经常会有这个警醒。
三联生活周刊:你心里有没有自卑感?
罗永浩:有时候会有。比如说我自己对自己胖瘦是不介意的,我平时穿得也很邋遢。其实是因为胖了才邋遢,我瘦的时候穿衣服还挺好的。我胖了就懒得穿了,因为胖了以后身材走样了,穿得很讲究就会显得很滑稽。我索性邋遢了就无所谓了,这个一旦放松了以后就很舒服。但是如果有一个正式场合,比如腾讯教育搞一个年度颁奖,上去10个人领奖,我也没当回事,吊儿郎当就跑那儿去了,上去一看大家都穿得西装笔挺的,50多岁了身材还保持挺好,人模狗样地往那儿一站;我上去一站呢,我想象从镜头里看过去会很怪异,和那个场面格格不入。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穿一身好衣服就好了,最近减减肥就好了”,这样的时候是时不时有一些的。
三联生活周刊:除此之外呢?
罗永浩:剩下应该很少。我大部分时候的问题是太自负了,而不是自卑。
三联生活周刊:你经常说你自负,你这种自负是怎么形成的?
罗永浩:我觉得我放在哪个群体里都是中间偏上一些的,所以我就会忍不住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又觉得表现优越感是很愚蠢的事情,同时也是我非常反感的,所以我就会经常自嘲,嬉皮笑脸地自己把这个东西化解掉。但我骨子里是很有精英意识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越是自信的人,心里面往往存在着一个特别大的自卑感。
罗永浩:一个人特自信,和自恋有什么区别?以前柴静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我觉得真正自恋的人是永远不会拿自己开玩笑的,别人开玩笑他也不乐意。他不好意思表现,他会不笑,会那样端着,但明显是不高兴了。你看他平时写文章、开玩笑、朋友之间聊天,从来不自嘲。我觉得这种人是真自恋的,他是崇拜自己的,所以不能以任何即使是友好的方式去亵渎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自信和自恋的关系不是很大,倒是自信和自卑的关系很大。比如说芙蓉姐姐,她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从自卑走向盲目自信的结果。你这么自信,内心也会有自卑。
罗永浩:你说这些话,我还能想到我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虽然没有某些人表现出来的表演型人格障碍,但也是表演欲比较强的人。一般你如果能当众讲话,很好玩或者很煽情,都是有表现欲的人才会去做。所以我的表现欲肯定算比较强的,小时候在孩子里也算比较喜欢显摆自己的那种。但我注意到在某些方面,比如我是朝鲜族,我会讲韩文,但是因为我没有读过韩文书,所以我的韩语水平基本上是一个韩国文盲的水平。所以我离开家乡来北京,有些时候接触到中国朝鲜族或是韩国人的时候,我通常不愿意讲韩文,尽管我听说没有任何问题,读写有点费劲。我不愿意说的原因是一说出来就显得是一个韩文文盲。同样的也表现在,我虽然是一个英语老师,但是我的英语基本上是哑巴英语,是自己学的、读写为主的,听说比较差。听没有问题,因为美剧看多了,说有问题,就是发音不好听。全是老外的时候我还能讲一点儿,因为我觉得老外不会笑话我英文差。但如果有中国人在场,我又是英文老师,他可能会笑话我英文差,所以我就有意识地不说。在我的生活里我能找到很多这样的细节。我不知道这跟你说的自卑有没有关系,我发现当我在某一方面跟常人一样,或优于常人的时候,我是愿意表现它的。即使不比常人强,那都没事。但如果有些方面我比常人还差,那我就会有意识地掩饰这些方面。
三联生活周刊:有时候你在网络上、媒体上表现出强悍的那一面是否跟自卑有关?
罗永浩:我不觉得有。我有些凶巴巴,是因为我脾气暴躁,我爱憎比较分明,如果我特别讨厌一个人,我会显得特不留余地。另外,有时候我和人凶巴巴的是因为我无权无势,我又想要做成一些事情,我得让人怕我,但我又不能以不讲理的方式。比如我和企业沟通的过程中,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把它弄得特别不留情面的话,将来任何一家机构和我们产生合作关系的时候,比如他想违约或者耍无赖、耍流氓,他的顾虑会多很多。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所以有一些我表现出来也是策略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你要给你的“粉丝”分类,你大概能分哪几类?
罗永浩: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就是觉得我好玩的,在他们眼里我和郭德纲、周立波,或者任何一个笑星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算相声听众吧;能理解我的“粉丝”应该不到10%;还有另外10%,甚至更多,将近20%,可能是完全基于误解。由于我在过去表现出的某一个特质正好符合他的胃口,他就喜欢上我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就是在我长期写博客的过程中时不时蹦出来,说“我对你很失望”,然后消失;又冒出来一批说“我对你很失望”,然后又消失。我从2006年在互联网上公开写东西到今天,不停地冒出来一些表示失望、离开的人。比如说他上一次喜欢上我只是看过我写的一篇回忆类的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煽情,他被深深打动了;下次一看我吵架,他说“哎,你这人怎么能吵架呢”,然后就走了;或者是上次看我吵架吵得特别凶悍,然后一下喜欢上我了,结果下次一看我就一个事情有理、有据、有节,特别温和地沟通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怎么不直接干他娘然后就完事了呢”,表示失望就走了。各种各样。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网络社会关系,跟过去的社会关系不一样,过去是熟人社会关系,圈子很有限;但现在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关系,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但感觉上都是零距离。但它存在着一个信息不对等问题。
罗永浩:对,更容易有误会。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傻啊”或者“这人怎么会这么想啊”,你可能是在按一个熟人社会的标准想这些事情。
罗永浩:对,因为互联网这种陌生人这么大规模地、上来就自来熟地讨论、交流、吵架、沟通、抒情,这种东西是完全的新生事物,对人类的人际交往来讲。大家都是在适应和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喜欢你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你有没有过回家单独严肃时,突然产生一些幻觉,觉得“我很强大,我后头有很多‘粉丝’,我可能有很强的力量”?
罗永浩:当然有,客观上就是有,比如话语权方面。■
(实习生魏玲、谢宁馨对本文亦有贡献) 罗永浩有时候难为情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