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的谋杀
作者:陆晶靖 ( 油画《刺杀马拉》 )
( 油画《刺杀马拉》 )
19世纪的英国散文家德昆西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谋杀,一种优雅的艺术》。他说:“谋杀同雕塑、绘画、宝石、凹雕一样,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状若冷漠的态度让许多怀有正义感的人愤怒,可是从19世纪到现在,人们对谋杀这件事的兴趣并没有减退。每年依然有许多小说、电视剧、电影热衷于谋杀题材,这是为什么呢?
大多数人喜欢谋杀,只限于某一程度,并不想对这个行为了解更多。对谋杀行为越了解的人,对这件事越提不起兴趣。这清楚地解释了我们的疑问,即:对谋杀的爱好和对谋杀行为的爱好不是一回事。大多数作家和导演喜欢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谋杀,只是因为这是一种极好的智力游戏,并且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绝无可能去了解这件事情。这和《加勒比海盗》拥有许多“粉丝”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些人都向往海盗的自由自在,但从来不会把杰克船长和索马里海盗联系在一起。一旦触摸到日常经验,“谋杀”和“海盗”都会立刻失去魅力。许多日本推理小说家的做法证明了这一点,流行的“密室杀人”直接挑战日常世界的逻辑,凶手通过一系列手段,使被害人被杀的证据全部指向被害人所处封闭的空间内。没有第二个人,而被害人又不是自杀。谋杀行为的残酷性和杀人的动机都被抽象化,“如何做到”成了一个大谜语。侦探最后总能够找到凶手,说明侦探小说家都信奉一个道理,即不管布局如何精密,相较于神,人类终究是一种有限的生物,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是无法达到完美的。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在《牛津迷案》里说,完美犯罪不是那些没有被侦破的无头案,而是找错了凶手的案件:一个叫格林的医生想杀妻子,用绝对科学的态度事无巨细地在日记里总结了14种不同的方法,想研究出警察无法找出痕迹的手段。有一天晚上医生的妻子发现了日记,在扭打中妻子自卫把丈夫刺死,陪审团判妻子无罪。此后妻子迅速而低调地改嫁给了一位古代绘画的临摹师。在她去世多年后,几个研究笔迹学的学生发现,日记本上的字迹并非医生所写,而是几可乱真的伪造。
有些文学评论家非常不喜欢这种游戏,桃洛赛·赛伊尔斯在《犯罪选集》第一卷的前言中说,侦探小说永远也达不到文学造诣的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一种“遁世文学”,独立于日常经验之外,不是“言志文学”。雷蒙德·钱德勒对此颇为不屑。沿袭这样的观点,《麦克白》和《罪与罚》虽然也主要以谋杀为题材,但对于谜并没有兴趣,人们对这两部作品的喜爱和对《莫格街谋杀案》是不一样的。在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谋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状态,情感和思想都在这种状态下急剧翻腾,如果说这种状态不属于日常世界,那也是因为它们是从日常经验中千百倍地提纯出来的。麦克白和拉斯科尼尔科夫证明,杀死自己的同类绝不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尽管凶手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这一行为依然会对凶手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刺激。麦克白夫人因为潜意识里的罪恶感得了不停洗手的强迫症,拉斯科尼尔科夫发烧不止,不停地说胡话。罪行的后果会很快到来,德昆西在《麦克白中的敲门场景》里写道:“当谋杀行为结束时,当黑暗的状态达到完满的境地时,它就会像天空中华丽的彩虹一样突然消失。我们听见了敲门声,通过声音的方式让人们感知谋杀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了,人性从魔性中退却出来了,生命的气息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又回来了,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生活停滞的可怕间隙。”通过谋杀行为,凶手对自我感到陌生,伴有恶心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害者通过自己的死亡也谋杀了凶手。麦克白说:“拇指的刺痛告诉我,邪恶的东西向我走来,打开来吧,门锁,不管来敲门的是谁。”这和《罪与罚》里拉斯科尼尔科夫最后的选择是一样的,当他向索尼娅忏悔了之后,觉得如释重负。
最早关注谋杀的文学作品可能来自于神话和巫术。英国学者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研究了意大利的一个神话:“内米的圣林中有一棵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他是个祭司,又是个谋杀者。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在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而他要搜寻的那个人迟早总要杀死他并取代他的祭司职位。这就是这儿圣殿的规定:一个祭司职位的候补者只有杀死祭司以后才能接替祭司的职位,直到他自己又被另一个更强或更狡诈的人杀死为止。”在这个传说里,被杀死的祭司成为新祭司的祭品。这是一种鼓励人们挑战君主的机制。弗雷泽认为这种弑君模式可能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具有普遍性。弗洛伊德在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里也谈到了谋杀,他设想,在原始社会里,存在着一个专制的父亲,他占有所有的女性,却驱逐已长大的儿子们,迫使他们禁欲。终于儿子们一同回来,杀死父亲并吞食了他。这就是俄狄浦斯神话的社会原型。图腾制即是这一过程留下来的仪式。图腾代表着专制的父亲,人们既恨他、怕他,又爱戴他。儿子们尽管希望拥有所有的妇女,但谁也没有父亲那样的超人力量,为了不致在混战中同归于尽,他们便制定了禁止乱伦的法律。这样,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契约从原始部落中产生了,这就是文明的开端。
弗洛伊德关于谋杀的学说遭到了教会的激烈反对。在《圣经》文本里,很早就出现了基督教世界里第一起谋杀案(《创世记》4:1-12),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耶和华便判他“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亚伯拉罕从命献子,与弗洛伊德的主张完全相反,“亚伯拉罕”即意为“众人之父”,也是犹太民族的祖先。犹太人命运起于一个听从神谕打算谋杀自己孩子的父亲,听起来像是一个隐喻。谋杀的动机似乎决定了应该如何判决。但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对于谋杀的判决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第一部系统的刑法典,其中就规定杀人应得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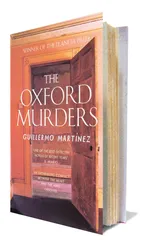 ( 《牛津迷案》 )
( 《牛津迷案》 )
最初的谋杀没有任何诗意。附着在这个词上的意义都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而谋杀的动机千奇百怪。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宋之问谋杀侄子刘希夷,就是为了抄两句诗:“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聚斯金德的《香水》里,畸人格雷诺耶为了提取香味,谋杀了26个少女。更离奇的是一起和康德有关的案子,一个杀手本来要杀这位哲学家,但临时改变意见杀了一个小孩。德昆西的解释是,杀手觉得杀一个年迈、无趣又忧郁的形而上学人士获得的感觉和体验太少了,康德的生活已经很像一个木乃伊了,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奥威尔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还为一个杀人犯辩护:“他犯谋杀罪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起被察觉通奸来似乎是不那么丢人,对他的事业不那么有害,有了这种背景,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气质,使它令人难忘,并且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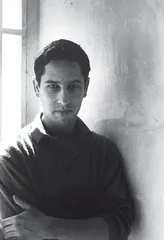 (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
(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
(文 / 陆晶靖) 文学作为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