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像汽车的安全气囊
作者:孙若茜 埃特加·凯雷特
埃特加·凯雷特
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短的两三页,长的十几页,紧凑,奇异。不写长篇,他的理由是:“我的小说就像爆炸,我不知道怎么把爆炸变慢。”有人形容,他笔下那些的主人公虽然存在于我们熟悉的现实,却像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次元。
如果你记得他很有名的那篇小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那个被人拿着枪和刀威胁,必须讲出一个好故事的作家,那条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会说话的鱼,还有那个被送回童年时代的中年男人,应该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不过凯雷特并不认为他的作品超现实,他说自己只写主观的故事,不知道怎么写客观的故事。只有在客观世界中,才存在现实和超现实的区别,而在主观世界中,只有真实和非真实之分。他只对故事表达了什么感受和想法有兴趣,而对它是否在科学上正确并不感兴趣。
埃特加·凯雷特全新的短篇小说集《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借由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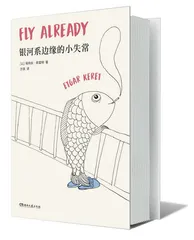 短篇小说集《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短篇小说集《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短篇小说集《FLY ALREADY》,中文版的名字是《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你觉得怎么样?“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是书中唯一一个没有标题的故事,它被处理成了一封封穿插在其他故事之间的邮件,为什么?
埃特加·凯雷特:“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是原希伯来语的标题(美国的版本更改了标题,但中国出版商选择忠于它)。我之所以选择它作为标题,是因为从普遍的角度来看,故事中那些使人震撼的,让角色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戏剧性事件,放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都是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就比如说,作为个体而言,书中的某个角色丢掉工作或者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就会彻底摧毁他们的生活。但是,放在更大的视角之下,这些事并不会威胁或改变我们星球的命运。这个故事是试图呈现同一件事在个体主观的叙事之下与其在冷漠且遥远的宏观视角之下的差异及张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里的《托德》让我想起那个题目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故事,它们当中的人物都认为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故事。你想以此表达什么?
埃特加·凯雷特:作为作家,我问自己,写小说有什么意义?编造这个世界上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或发生在不存在的人物身上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你提到的这两个故事试图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假设一个故事是有实际用途的,就像一把剪刀或者一个锤子。当然,这是很荒谬的,因为文学并没有真正的实际的功能,而是超越现实的。因而,对文学作品中永远无法传达的一些东西怀有期待,就好像搭建了一个平台,使我和读者能够了解到故事能做什么,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即使故事中的角色对此并不完全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说中,有很多谈到写作、讲故事本身的篇目,里面借人物之口表达的观点,可以代表你对写作的真实态度吗?
埃特加·凯雷特:每当我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在唠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坚持写作而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帮助别人,建造庇护所或者桥梁,做那些真正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并且可以对它产生影响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和想象中的?这些隐藏在我头脑中的想法,有时候会突然将我的故事推进到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并且成为我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内部讨论,讨论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为什么选择读这本书。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小说中写过一条“会说话的鱼”,你希望通过它表达什么?
埃特加·凯雷特:那条“会说话的鱼”给我带来一种渴望,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都希望如此,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渴望很模糊,比如,我想变得更快乐,少一些焦虑,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更多的钱会减少我的焦虑吗?吃更多的食物或者更频繁性生活会让我更快乐吗?我很肯定并不会。在我看来,一条“可以满足我们所有愿望的鱼”的故事是以一种最好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在散文集《美好的七年》里,你曾经提到过“逆着生活之流的写作”,能不能解释一下?
埃特加·凯雷特: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随波逐流,而不是去花时间或精力定义或区分不同种类的“对”和“错”。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不会使我们变得善良或纯洁,但是它可以告诉我们,比如,当你的孩子犯了错,你大声训斥他和动手打他是有区别的。理想情况下,这两种事父母都不会做,但是能够区分对孩子说些冒犯的话和打他耳光之间的区别,可以帮助一个人在生活中建立某种清晰的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那本散文集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你父亲对生活的那种热爱,你也曾在一些采访中提到过母亲的乐观。你认为他们的乐观源自什么?以及这对你有怎样的影响?你是同样乐观的人吗?
埃特加·凯雷特:我的父母都是幸存者,作为犹太裔的孩子,在“二战”期间的纳粹政权之下,在欧洲生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在犹太聚居区或他们的藏身之处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能力,能帮助他们不陷入绝望,即便在事情看起来毫无希望时也能坚持并且享受生活,继续向前走。
在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告诉我,我能想象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有时候,当你无法达到一个理想的、更好的现实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想象一个,并与其他人讨论它,这会使那种可能性保持活力并得到延续。我不仅仅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且还发现了这种乐观之中具有的颠覆性的立场,以及一种有助于我生存的品质。
三联生活周刊:《美好的七年》以儿子的出生和父亲的去世作为写作的时间界限,这两件事对你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埃特加·凯雷特: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发表了很多关于父子关系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从孩子的视角写的。成为父亲之后,尤其是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我依然会去写同样的关系,但是是从父母的角度写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的脑袋里总是有故事需要被写出来,这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你是否知道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成为作家以后,你有过写不出故事的阶段吗?
埃特加·凯雷特: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从来不会为它烦恼。故事来到我的脑子里,帮助我理解我的感受和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我来说,故事就像汽车的安全气囊,它们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但如果一切都好,它们就根本不被需要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些一开始没有被你写出来,但多年之后又再次从你脑袋里冒出来的故事,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埃特加·凯雷特:那些故事就像谜语。当你坐下来写它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不可能完全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直到几年后,你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填补了某些缺失的部分,完成了故事。比如说,我在写那个关于希特勒克隆人的故事《白板》(Tabula Rasa)时就总是不停地卡壳,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直到我去了一个博物馆,看到墙上的图片,我才突然意识到,给克隆希特勒注入思想和意识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他对绘画和艺术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白板》里面的克隆人,《窗户》里面的AI,这些既存在于现在又存在于未来的角色是你过去的小说中没有提到过的。在你的设想中,被它们改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埃特加·凯雷特:我对新技术着迷,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带来什么,还因为它们暴露了人性中的什么。看看互联网:这个平台可以让读者接触到几乎所有的文字或艺术作品,但是大多数人却用它看色情电影。在我的科幻小说中,我想看看那些实体,人工智能或者克隆人,当他们拥有与人类同等的心智和能力,却没有拥有和人类同等的权利时,人类会怎样。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窥探人类黑暗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肺炎的疫情暴发以来,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它使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有没有打算写些关于它的故事?
埃特加·凯雷特:过去的六个月是很艰难的,但是困难往往会激发创造力。事后来看,过去的六个月是我灵感最丰沛的一段时间,用来写作是很明智的。隔离给了我所需要的时间,对我而言无聊始终是开始创作的好引擎。并且,当生活停滞不前的时候,想象我们的社会和世界可能发展的新方向似乎更加容易。
(实习生印柏同对本文亦有帮助) 文学小说埃特加·凯雷特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