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的故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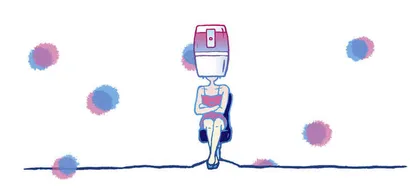 (图 陈曦)
(图 陈曦)
文/阿董
单身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由时间很多,我在很贵很远的一家店剪头发。多贵呢?十年前剪一次头发480元。多远呢?离住地二三十公里。当时我住北京西三环,理发店在东四环,每回开车都需要纵贯大半个长安街。印象最深的有次约9月30日晚上7点剪发,5点半下班从西三环出发,10点时我的车刚开到天安门。
我的发型师是位人淡如菊、气质优雅的女士,名叫珍妮,相当励志,十几岁北漂进京,手艺实在好,积累了一大批客人,自己单干做了合伙人。后来自费去日本、意大利进修服装设计,现在开了一间真正的造型工作室。
讲真的,我找她并不适合,不是她手艺不好,而是我用不上。不论前一天珍妮给我凹的造型多么精心,作为上班族第二天我照样手忙脚乱顶着一头乱发去上班。
婚后,有次烫完发,老公去接我,看到我高价凹的新发型,整个人都变得高贵了,他便气势低了很多,小心翼翼地问:“你这头发得花好几百吧?”老公艰苦朴素,常年在小区的“小王理发”剪,年后从15元涨到20元都耿耿于怀。我当然不能说那回烫发花了2000多元,少说一个零,省却很多烦恼。
等珍妮涨到780元时,我生孩子剪了短发,以没时间为由果断换成了小王理发。体验价90元,感觉非常好。
这回是位男发型师,姑且叫他Tony吧。Tony有点黑,虽然剪发是一项体力劳动,但他有点过于像一个体力劳动者。土是土了点,但手艺不错,话也少——并没让我变得更难看。
好景不长。等我再去找Tony,他话仍然少,但意思非常明确:我必须办卡。店和他都跑不了,短发一个月就得剪一次,办一个最低面值(1000元)的储值卡,不到一年就用完了。
妥协的当然是我。没想到第二个月,店还在,他就跑了。Tony说老店租期到了,店名店长都换了,选店就不能选他,选他只能到另一家店。不善言辞的Tony结结巴巴跟我说了一个小时:想把原先卡上的钱转到这家店,必须再花钱,办新卡才能转过来。
他一口一个姐叫着,后来为表示亲昵,还把手搭到我肩上,我倒没觉得多冒犯,更多的是滑稽。Tony套近乎的方式生疏而笨拙,竟让我产生了怜悯。大家都是讨生活,都不容易。
除了宽容,我还有中年人的精明,迅速评估一下:找一个固定的还凑合的发型师和一个不太远的理发店不容易。
结局就是我跟Tony见了三面,办了两张卡。再精明的猎人也斗不过好狐狸。我后来发现办新卡转旧卡是个伪命题,旧卡面值只能用来做鸡肋般的营养护理。真实情况是Tony和上家店闹翻了,自己出来单干,自编自导了这场戏。
除了Tony,我还遇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洗头小哥。和别人一张嘴就推销不一样,他一直跟我聊文学。喜欢日本作家,头一个当然是村上春树,他还爱看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虽然文学是一桩雅事,但我仍然被问得心烦。
我把这件事发在朋友圈,有朋友替我解围:下次可以谈谈夏目漱石的《猫》,或者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那段时间,这店文艺过了头,连不谈文学的Tony都成天戴着一副金边平光眼镜,每次剪发让我如临大敌。
这家店我大概去了三年,Tony这回创业有点仓促,门店选址欠佳:北京夏天下大雨,店里下小雨。郭德纲相声没瞎说:雨大了全家人都得街上躲雨去。相对于漏雨,我更害怕漏电。毕竟漏雨可以穿雨衣剪发,但是吹风机烫发机漏电是要出人命的。
还好,Tony没撑到夏天就跑路了,方式简单有效: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从此和他的老客户们相忘于江湖。 理发tony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