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文学的邀约(2)
作者:朱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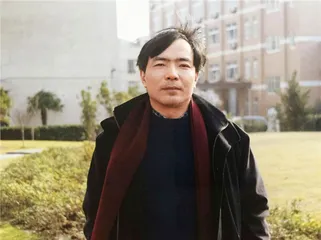
大约1987年的下半年,我就认识格非了。1987~1989年,暑假他就到北京,我们来往较多。他对各类小说家的先进叙事技巧都研究颇多,讨论时较真儿。他经常会说:“这个问题嘛,我以为是这样的。”常以停顿,加重阐述的分量。遇到反驳,会略皱眉凝思,随后就会极认真地延伸。他是小说结构的研究专家,但再激烈的争论,他也斯文。他的倔强是在内心。
1988年他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一篇是发表在年初《钟山》上的《褐色鸟群》,另一篇是年底发表在《收获》上的《青黄》。对《褐色鸟群》的界定,我以为还是吴洪森当年的说法最靠谱。他大致说,这小说要表达的,是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按格非自己的说法,其构思来自他和朋友去小卖部买火柴,朋友拿出一个火柴盒,小卖部老板说,你有火柴,为什么还要买?朋友推开盒子,里面装着几枚硬币。这就是是与非纠缠的趣味,格非早期小说寻找曲径通幽的起点。

其实是微妙的时空关系。这小说里,格非先告诉你,时间是含混的,“褐色鸟群”代表时差。作为候鸟,小说交代,“我能根据这些褐色的鸟飞动的方向,隐约猜测时序的嬗递”,但小说开头,强调的又是,“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这暗示你,要表达的就是,是/非的意义。小说中,“我”在水边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棋抱着画夹来访。预言即“我”的小说的想象,所以,其中角色关系,都可看作是“预言”的构思。小说里,来访的棋说,这些画是一个叫李朴的男孩画的,李朴是李劼的儿子。她对“我”不认识她很生气,她说,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李朴,难道李劼也不认识吗?李劼正是生活中,那时格非的朋友。晚上,棋就留在“我”的寓所,“我”给她讲,在企鹅饭店被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步态招引的故事,形成套装结构。格非细致描写这女人胯臀移动时裤子皱褶赋予身体的弹性,他的欲望似乎是由线条、几何图形构成的。
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中,这女人在“买木梳吗”的叫卖声中向“我”走来。“买木梳”是昔日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她走到“我”跟前,捡起一颗靴钉,就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电车。“我”租一辆自行车(时间错位了)追到城外,下起了鹅毛大雪,时间彻底变换了——因为,刚才走在风中的女人,交代是四月。我在漫天大雪中跟踪女人的背影,上了一座木桥,背影消失了,“我”却被一个提马灯的老人叫住。老人说,这是一座断桥,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也不可能有一个女人从这桥上走过去。这是故事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第一人称继续叙述:“我”与这女人重逢,是因到郊外湖边修改长篇小说,时间又是早春。“我”沿湖散步时,看到一对男女从坡上滚下来,正是那个女人,丈夫是瘸子。在村里小酒馆,我又见到这女人与她丈夫,丈夫喝醉了,女人扶他,被啐了口痰,推倒了,“我”就帮着把醉汉背回家。女人请“我”坐下喝杯茶,“我”对女人说,七八年前,在企鹅饭店门外跟过你。女人说,你是不是记错人了?我十岁起就没进过城。不过,我们这里通往城里,倒是有一座断桥,有一天下大雪,我男人提着马灯,看到桥上有自行车轮辙,第二天雪晴,村里人在河里捞起了一辆自行车与一个淹死的男人。
故事再发展,一天雨后,那女人来敲门,说她丈夫死了。此时是梅雨季节了,女人说,她丈夫是晚上喝醉酒,掉进粪坑淹死的。“我”跟她到家里,入殓时,看到那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未死,就钉上了棺盖。送葬后,女人说她害怕,让“我”至少陪她三天。第三天晚上,他俩上床时,“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声,推门见到,闪电中一个赤裸少女站在院子里,“她婴儿一样的脸上挂满泪珠”。“我”把所见告诉女人,女人说,那是你的幻觉。“我”说,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你的尸体漂浮在断桥下的河面上。她苦笑了一下,我就说,我们结婚吧。女人婚后不久就死了。
最后结尾,“不知过了几个寒暑春秋”,棋再走来,是棋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什么李朴、李劼了。她说,我不叫棋,您一定记错人了。她打开怀抱的夹子,里面是一面镜子。有些读者埋怨格非的小说无故事,其实,他的悬念是需要你去寻找的。用传统的故事来衡量,他的故事可能相对抽象,有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或者玄学的味道。此她非彼她,之间相隔着时间,时间是具象——小说结语是,“这些褐色的候鸟天天飞过水边的公寓,但它们从不停留”。这就是格非要告诉你的时间差。在时间的轴线上,如棋所说:“你的故事是一个圆,它在展开的时候,也意味着重复,你可以永远讲下去。”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结构。我读到过一些解读这篇小说的文章,比如说到那女人应是谋杀了丈夫。其实,在这结构中,事实即非事实,都是错位的趣味。本来,小说就是虚构。
《青黄》讲寻找所谓“九姓渔户妓女船队”上岸后下落的故事。小说开头就交代,这船队早在40年前就已经消亡了,提出悬念。有意思的是篇名的含义。《中国娼妓史》的作者本是王书奴,格非改为谭维年,按谭教授的说法,“青黄”是一部流落民间,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小说也就是我寻找“青黄”的过程。九年前,我先到过麦庄,与一位换麦芽糖的李贵老人同宿一位外科郎中家,郎中的说法,“青黄”有可能是从年轻到年老的妓女,“女人像竹子一样,青了又黄”。而最后,我到李贵老人家里,发现“青黄”实际是他家的狗。格非的结语,从《词综》上查到,“青黄”又是一种草本植物。《词综》本是朱彝尊编的词总集,这显然是格非杜撰。从词典上查,“青黄”指四时之乐,《汉书·礼乐志》记:“灵安留,吟青黄。”也指是非、黑白。
这小说是有意营造扑朔迷离,营造的目的是消解。表面的扑朔迷离,比如外乡人死后,连续暴雨将其棺材从墓穴里冲到康康家门前,里面没尸骨,什么也没有;他出现在女儿小青家门口,小青的儿子傍晚就掉进冰窟窿淹死了。其实与换麦芽糖的李贵在雷雨夜神秘失踪一样,这些都只为通过悬念,营造氛围神秘的外壳。内核是什么呢?是跟着父亲上岸的小青经历的意味。“我父亲也可能不是亲生的。”上岸第二天,村里收留他们的老艄公,就把小青叫到船上,“把我咬得浑身是血……后来,老艄公的船就翻了”。父亲死后,一个黑影强奸了她,然后她就嫁给了木匠。她惋惜的,只是为她而死的二翠,二翠是她的后母,她说:“二翠当初真不该那样拦他,这种事我从小就在船上看多了。”她说:“所有事情全都会过去,只有人死了不能复生。”格非在小说中有感叹:“美丽的容颜像一支歌谣一样消失了,又如一只鸟飞出了它的巢穴。”这才是“青黄”的真含义。
在1988年,我曾为它的结构陷阱叫好。那时候,我在《读书》杂志开一个“最新小说一瞥”的专栏,推荐各种“先锋”实验小说。那时候,“解构主义”是时髦。(待续) 文学格非小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