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8)
作者:朱伟
2006年写完《兄弟》,2012年写《第七天》,中间隔了六年。《兄弟》篇幅最长,《第七天》篇幅最短,余华自称是写一个“历史地标故事集”,社会历史地标。他巧妙地用了一个七天的构思。《圣经》里,上帝在第七日造齐了万物,第七日是安息日,上帝赐福于安息。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七是生命的数字,七日来复,故星期日也称“来复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余华的“来复”是什么呢?这个长篇的结尾,伍超晚来一天,错过了“鼠妹”。“鼠妹”已经安息了,她却不会再有墓地。没有墓地就没有归宿,但小说中的“我”对她说,走过去吧,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那里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她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答:“死无葬身之地。”
这部小说就如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安魂曲》,有意抹杀了经文中本应有的末日审判、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上帝的权力意志,死也就抹杀了生的阶级关系,抹杀了善恶。不再有天堂地狱、因果等级,也就无须尔虞我诈,有墓地者均可安息,无墓地的游魂也可在青草遍地、流水潺潺、树上结满硕果、到处盘旋着夜莺般歌声的彼此亲爱中永生。这样美好的永生,无非是肉体腐烂,都变成身材不一的骨骼而已。余华是有意将死后的“这边”与《创世记》第七日之圣联系起来——死无葬身之地,也就无忧无虑,重新回归了自然怀抱的“伊甸园”。“这边”与“那边”,自身、人为的罪带来的苦痛,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这部小说中展示的现实是夸张的,充分戏剧化的,这夸张与戏剧化就为了表达“罪”——社会机器造就的种种生之卑微,及因卑微造就的,到了“这边”才看清是荒谬的悲剧。这部小说,余华采用极简的表现主义方法,因此导致有些读者因其中使用了一些类似恶意拆迁、刑讯逼供、隐瞒死亡人数的社会新闻元素,便以为是“串烧”了社会热点,用小说创作参与了表达社会宣泄。其实,表现主义是将现实提炼为表现的结构,现实之种种是在冥河的“那边”,用余华自己的说法,只不过是投射在“这边”的倒影而已。
余华说,他是因获得了那个火葬场来的电话“你迟到了,还想不想烧”的奇思妙想,才找到了通向这部小说的桥梁。这个第一天写得太精彩了,一个作家的财富,莫过于其想象力。想象一个走向火葬场的死人,身体飘忽着失去了重心,视觉呢?余华写因爆炸,五官错位,眼睛移到了颧骨的位置,“鼻子旁边就是鼻子,下巴下面就是下巴”。他以虚无缥缈,古小说中仙人的轻盈飘忽写温暖的阴间,阳间反而是阳光照着的冷酷了。反其道而锋利,余华捕捉细节的能力太强了,他通过雪花写死人的阴寒,雪花纷纷扬扬,“恍若光芒”,“飘落在脸上,脸庞就有点温暖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顶峰作品,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写“我”走进一个故人生活的村庄,就没有这样的环境营造,只有赤裸裸隔世的真实。
在《兄弟》中,余华用50万字,写一个结结实实的人物——李光头的权力实现。这权力具体体现在对林红的性征服上,富裕权力崛起于贫困被奴役的辛酸之上。《第七天》,他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反身再来关怀这个贫困群体。余华大约是因不愿再重复许三观那样,对沉重的卑微的凝注,才改用这样一种凌波微步般诗意的手段,写他们因难以承受生命之重,才急切地从“那边”走向“这边”。彼岸成了“那边”,本来的阳光明媚变成凄风苦雨;“这边”本来被死神操控于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的恐惧,反而变成了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这当然是余华在追求锋利中,创作途径之必然。
我想,余华是因不愿再写卑微者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的残酷了,才找到这样一种反其道行之的方法。这小说中的“我”是在冠名“谭家菜”的廉价饭馆里,吃一碗廉价的面条而被炸死的。谭老板制造爆炸,是因不堪负债,负债是因各种社会权力的盘剥,生意惨不忍睹。谭老板一家到了“这边”再开张,就不再有欺压敲诈,在到处欢声笑语中,不用愁容满面了。“我”在饭馆,之所以没有逃跑,是因看到了前妻自杀的消息。“我”的美好生活是因前妻出轨始,前妻出轨是因向往富裕,富裕生活向她招手后又很快将她抛弃,将她推向出卖尊严维持生计的绝路。尊严卖光了,就只能自杀,在“这边”与“我”重逢,重温了往昔的温馨。“我”呢?一个从列车卫生间厕所降生到铁轨上的苦孩子,幸得一位铁路工人收养,在养父的艰辛中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与体面的妻子。无奈所有美丽女人都难逃诱惑的罗网,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出走,养父患癌,只能买房辞职尽孝道。养父不愿拖累儿子而出走,儿子就开始了茫茫人海中的寻找,最后他们也只能在殡仪馆相认。这部小说里,这些人物都只呈示各自的类型,余华不愿再累赘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脆弱无助,于是反过来,就写他们在“这边”获得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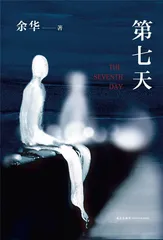
小说中写得特别感人的,就是第六天送“鼠妹”去墓地的仪式。“鼠妹”之死,卑微到只因贫困的未婚夫伍超欺骗了她,送了她一个假iPhone4S后她自杀了。伍超守候病父时获知“鼠妹”的死讯,卖肾给她买了墓地。“鼠妹”下葬墓地前要先净身,余华描写她躺在青草与野花上,青草与野花低头凝视着她,“它们的凝视遮蔽了她的身体,青草就在她身上生长,野花就在她身上开放”。然后,骨骼们每人双手合十,捧着树叶之碗里掬起的河水,排起长长的队列,“青草与野花接过河水,抖动着浇灌了鼠妹”。再然后,制衣厂烧死的几十个女工给她缝出一条曳地的长裙,27个死婴以带笑的歌声伴唱,这些死婴像花环,环绕着发现他们的李月珍,李月珍成了他们的母亲。这真是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里那个走向婚礼的唯美主义场景啊。读到这里,我真的落泪了。这些卑微地生活在社会底层、任意被人践踏伤害的小人物,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光彩与尊严吧?
可惜的是,很多读者看不到作家在叙述角度选择上的无奈。这部小说出版后,遭遇的非议大约是最多的。余华因此而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冷酷,才想赋予温暖。在“这边”,那个被枪毙的“睾丸”才有可能每天与被他杀死的民警下着悔棋,等待他得到烈士的称号,“仇恨被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在“这边”,那个商场大火里被烧死的小女孩说:“我以前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现在有很多爸爸很多妈妈。”余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他是在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
现在,余华还在写那部新作,写写停停。“一部写了近20年的小说,清末民初时的故事。”他说。清末民初,他如何形成自己独到的叙述呢?我好奇,我期待着。(完) 写作文学小说兄弟余华第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