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万·泰松:“我曾是一匹狼,现在则是一头熊。”
作者:孙若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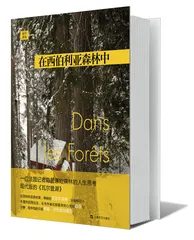
几年前,出于偶然,法国作家西尔万·泰松在贝加尔湖畔的一间小木屋里度过了三天。当时,一位名叫安东的护林员在位于湖畔东岸的巴掌大的小屋里接待了他。“我们晚上下象棋,白天,我帮他拖渔网。我们几乎不交谈,但却大量阅读——我在读于斯曼,他读的则是海明威。他灌下成升的茶,我则去林中散步。阳光泻进小屋,一些大雁趁秋季南迁。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听收音机,播音员正播报索契的温度。安东说:‘黑海应该挺好的。’他不时往炉子里扔一根柴火,等到长日已尽,便取出棋盘。我们一边小口啜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伏特加,一边两军对垒。”离开时,泰松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旅行再也无法给予我的东西,应该向静止去索取:那就是平和。”
19岁那年,西尔万·泰松骑摩托车穿越了冰岛中部,参加了婆罗洲洞穴探险。后来和好友亚历山大·普森一起骑单车环游世界。并且,从1997年起,他就开始以步行、骑单车或骑马的方式游历中亚。他并非是单纯的写作者,还是旅行家、探险者。旅行的状态几乎构建了他全部的写作,他出版了十几本很受欢迎的游记,一本获得2009年龚古尔奖的短篇小说集,题为《居于别处的一生》。“旅行再也无法给予”,对于泰松而言,是一种情有可原的状态或者假设。
于是,泰松向自己承诺,40岁前要在森林深处过一段隐居生活。2010年,37岁时,他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居住了6个月。小木屋距离最近的村庄120公里,不通道路,没有邻居,偶尔有人造访。冬季,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没。他说:“那儿是天堂。”
“我带去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在这片荒原中,我自创了一种朴素而美好的生活,度过的这段生命紧缩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小屋是一个捕捉自然颤动瞬间的理想观测站。”6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冬和春,他每天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而非单纯的流水日记,记录感受,幸福、绝望以及平和。而后,这本日记被集结成书,以《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名字出版并在2011年获美第奇文学奖,后又被导演萨菲·奈布改编为同名电影。前不久,这本书的中文版获得了2016年第8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对于泰松来说,小木屋是一座实验室,一个加速他对自由、经济和孤独的向往的实验台,自创一种慢生活的试验田。2010年2月14日他抵达了木屋,开始建立自己临时的新生活。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木屋是个简化的王国。松林庇护下的生活简缩为一些根本性的行为。从日常杂物中解放出来的时间被休息、凝视和各种小幸福所占据。需要完成的事项减少了。读书、汲水、砍柴、写作、沏茶成为礼拜仪式。在城市中,每个动作的进程都得牺牲上千个其他行为。森林将城市所分散的集中了起来。”3月17日,他写下自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得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我能容忍我自己吗?”“37岁的我能够蜕变吗?”“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少?”3月22日,他总结了把自己幽禁在一座小木屋里的原因:“我太多话。我渴望宁静。有太多信件没回,有太多人要见。嫉妒鲁滨孙。这里比我在巴黎的家暖气更足。厌倦了购物。为了能够吼叫并且赤裸地生活。厌恶电话和发动机的噪音。”
 ( 西尔万·泰松和他的著作《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
( 西尔万·泰松和他的著作《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
“我了解登山者攀登峭壁时的垂直晕眩:深渊的景象令人心惊。我记得旅行者在草原上的水平眩晕:逐渐消失的界限使他茫然。我清楚酒鬼在自认为发现一个天才念头时的眩晕:他感觉这个念头在体内不断膨大,而大脑却拒绝让它正确成形。”
他在小木屋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想起在喜马拉雅山的徒步旅行,骑马跋涉,三年前在乌斯秋尔特沙漠的自行车之旅。征服一座山口的喜悦,打败那些里程的狂人,希望在前行中死去的欲求。有时我像被梦魇附身,一直走到头脑谵妄,筋疲力尽。在戈壁沙漠中,我停下来过夜,径直倒在最后一步所踏下的地方,第二天早晨,眼睛一睁,又机械性地上路了。”而在小木屋的静止的生活的确为他带来了从旅行中无法获取的东西。“我曾是一匹狼,现在则是一头熊。”他说,“此地的神灵助我驯服了时间,而我的隐居生活便成为这些变化的实验室。”当行动事项范围变窄的同时,泰松发现,每项体验的深度增加了。他发现时光的流逝比旅程行走更加纷乱。当他即将离开小木屋回到法国时,他写道:“我离开了城市的墓穴,在泰加森林的教堂里生活了6个月。6个月,好像一生。”“我的小木屋也是一种交通工具”
——专访西尔万·泰松
11月27日,2016年第8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揭晓,《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获新人奖。作者西尔万·泰松应邀来到北京,并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西伯利亚?
西尔万·泰松:我对各种各样的地理环境感兴趣,尤其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保存比较好的无人之地,一些森林、高原、戈壁滩,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它们在逐渐受到人类的威胁。西伯利亚就是其中一片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而它刚好融合了我最爱的几个元素,森林、山和寒冷。从苏联解体之前我就开始去西伯利亚,去过无数次,对我来说那片土地代表一种野性和自然,到那儿我就觉得像回到家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寒冷为什么会吸引你?
西尔万·泰松:寒冷就像鞭子一样可以驱使你去行动,去做一些事情以变得暖和起来,我喜欢一切可以激发人行动的事情。它比炎热更容易让我适应。另外西伯利亚的冷是干冷,它和巴黎的湿冷不同,并不会让人很痛苦,即使零下40多摄氏度的时候我也觉得没问题。并且,西伯利亚的小木屋是非常简单的结构,只需要一点点取暖的材料就可以让整个屋子变得既温暖又舒适,更何况我还有伏特加,内心是暖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寒冷可以让光线变得非常美,各种景象和事物都笼罩在一种漂亮的反光中,冷似乎更可以吸引对美有追求的人,比如一些画家。我前两天在798艺术区看了郝量的画展,画了8个小山(《潇湘八景》),他的画马上让我想到了寒冷,只有冷才能反映出那样的光线。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是6个月?
西尔万·泰松:签证的限制,如果没有这个限制我更愿意待一年。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探险者,在西伯利亚生活的这段时间,以及此前那么多年的探险经历里,或者庸常的生活里,有没有什么让你真正感到恐惧的东西?
西尔万·泰松:在西伯利亚森林的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怕,熊、寒冷或者孤独都没有使我害怕。我真正害怕的其实是人类。你会发现,很少人因为自然而死掉,比如很少的人被蛇咬死,或者很少的人死于一次雪崩,更多的人死于互相残杀和伤害。
我的人生中已经冒了很多的险,包括登山什么的,可以说冒险的时候往往是无知者无畏的状态,什么都不害怕,也根本不会考虑死亡。直到两年前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整个人陷入了植物人的昏迷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说话不是很清楚的原因,我开始考虑到死亡,确实不能离它太近,太近是会受伤的。我其实并不怕死,但是会害怕等待死亡的痛苦,受苦的过程会让我害怕,植物人的状态反而很好,因为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痛苦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介意告诉我们那是一次什么样的事故吗?
西尔万·泰松:那次事故是因为我偶尔淘气爬上了一个屋顶,距离地面有大概10米高,我从上面摔了下来,身上有26处骨折,头颅有5处受伤,导致我现在讲话都有点儿问题,我的五脏六腑也严重受伤,多亏了21世纪的医疗技术,我才能存活下来。医生建议我好好进行理疗复健,但我想通过一种自己的方式得到康复。3个月的时间,我从意大利一直向北走到地中海,穿越了整个法国国土。说来可笑,20多年,我走遍了中国、俄罗斯和南美各个地方,但是我却没有好好探索过我自己的国家,虽然我的国家很小,但是有很多非常神秘、少有人去的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更何况这些年来城市化越来越快,农村越来越少,我希望趁这个机会和最后一批农民进行真正的亲密接触。我把漫长的历程当作复健的过程,并写成了一本书,也将在中国出版。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这次事故将颠覆你的人生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西尔万·泰松:我百分之百同意你的说法,很多人认为经历了一次大难不死,人就会变得更加乖巧、收敛,对生命加倍尊重,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往往改变的不是你的意识,而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三联生活周刊:那木屋里的生活呢,这样的经历会让你发生什么改变吗?
西尔万·泰松:我每次回到日常生活时都觉得无法适应社会,要花很长时间。我寻找的是孤独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希冀,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小木屋里生活,这些是可以完成的,这是一种可以给我强大的内心力量的念头,让我觉得凡事都是有出口的,是有解决办法的。
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收获了一些经验或学到一些东西的话,就是时间,只有你拥有了时间,你才是自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法国之后,穿越森林,或者穿行整个国家,我希望获得在西伯利亚曾经获得的那种自由,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孤独是需要寻找的吗?
西尔万·泰松:社会中的嘈杂环境让你无法安心,无法抓住最美的瞬间,我的最美的记忆都是来自孤独生活的经历,在城市中和社交生活里,反而会完全忘记自己在经历什么。只有在孤独中才会寻找到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友谊。
在小木屋的6个月时间,我没有完全无法忍受的时候,或许因为6个月还不是很长,而且中间时不时地有人来看我。最重要的因素是我有书,如果每天和阅读为伴,人是不会感觉到孤单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样的?我记得你在书里说“友谊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幸存”。
西尔万·泰松:登山的时候,我们都要在腰间绑一条绳子,每一个登山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们能看见对方,但是没有离得很近,不会有过多接触,也不会聊得很多。如果你不小心掉下去,他可以把你救起来;他掉下去,你也可以救他。这就像是我对友谊的理解。我觉得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能让现代人存活下去的方式就是保持距离,甚至跟自己的家人我也保持着距离,人和人之间是否亲近,友谊是否能维持并不是靠身体上的接近和交流来决定的,你可以离一个人很远,但是你还是想着他,情感是存在的。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之前的旅行,这种原地静止的探索,使你收获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西尔万·泰松:我此前所有的经验都是通过骑马、骑单车和走路,但是这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在行走当中还是在静止当中,都有对世界的探索,我的小木屋也是一种交通工具,接近世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工具。
三联生活周刊:这6个月的时间,解答了你带去的所有问题吗?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西尔万·泰松:比如说我发现一个问题,细思极恐。“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少?”我身边没有一个家人、朋友,甚至没有一个人,而我不会不开心。我终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不是喜欢看到人,而是喜欢自己想着他们。新的问题是,我实在是太喜欢那样的经历,但是时间不够。经历了那次事故之后,我发现自己衰老得很快,所以现在就希望增强自己的生命,加强自己的经验,继续这样活下去。(文 / 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泰松小木屋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