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6)
作者:朱伟 我感觉王安忆是通过不断阅读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堂小说课,在文坛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我感觉,开课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这门小说课共13讲,她从分辨“小说是什么”讲起,她说,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构筑的一个心灵世界,一个神界。她的讲稿似乎当时在《小说界》连载,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经典分析体现出优秀的解读能力。
我感觉王安忆是通过不断阅读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堂小说课,在文坛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我感觉,开课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这门小说课共13讲,她从分辨“小说是什么”讲起,她说,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构筑的一个心灵世界,一个神界。她的讲稿似乎当时在《小说界》连载,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经典分析体现出优秀的解读能力。
 比如《巴黎圣母院》,她避开了雨果先描写愚人节格雷沃广场上的市井,甘果瓦与艾思米拉达、卡西莫多的出场,因为市井只是氛围非本体。她避开前两章交代的所有因果表象,居然能从第三卷圣母院建筑与历史的具体描写讲起,看到与第五章开头的联系。因为雨果在原序中就强调,圣母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岩层,因此,克罗德才是结构全局的最主要人物。第五章开头,国王乔装拜访克罗德,克罗德提供的认识论是,建筑是人类记录沉重记忆的结果,而印刷术的“这个”,终究要消灭建筑的“那个”。这看起来只是一种认识,其实是雨果原序中的题意:圣母院镌刻的“命运”,“变成鸟儿一样飞翔”的思想,才永远“无法灭绝”。
比如《巴黎圣母院》,她避开了雨果先描写愚人节格雷沃广场上的市井,甘果瓦与艾思米拉达、卡西莫多的出场,因为市井只是氛围非本体。她避开前两章交代的所有因果表象,居然能从第三卷圣母院建筑与历史的具体描写讲起,看到与第五章开头的联系。因为雨果在原序中就强调,圣母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岩层,因此,克罗德才是结构全局的最主要人物。第五章开头,国王乔装拜访克罗德,克罗德提供的认识论是,建筑是人类记录沉重记忆的结果,而印刷术的“这个”,终究要消灭建筑的“那个”。这看起来只是一种认识,其实是雨果原序中的题意:圣母院镌刻的“命运”,“变成鸟儿一样飞翔”的思想,才永远“无法灭绝”。
王安忆认为,好作品就像大房子,房间再多,只要找到其中一扇门,就能发现所有房间都是连成一体的。她将《巴黎圣母院》的人物分成三个界面:克罗德代表着第一个界面——权力层面,这个层面中的国王、总督、法官、神职人员,掌握着表层社会秩序,克罗德是这一层的代表。雨果要写他与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的关系。卡西莫多是他在圣母院里养大的,卡西莫多以丑陋唤醒了他的温情,这温情是善。艾思米拉达则以美貌唤醒了他的情欲,这情欲的权势表达便是恶。克罗德的命运是他接近神界被塑造的,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是第三个界面:神界。卡西莫多与圣母院融为了一体,其实是神祇,艾思米拉达则是要烧毁凡俗的美神。艾思米拉达使克罗德废掉修炼了一生的神学,露出本质的虚伪;卡西莫多则在艾思米拉达被处死时认清了他的恶,将他推下了钟楼。
王安忆的认识是,雨果是构筑了神界,通过神界与凡界的关系,以神界感人。卡西莫多与艾思米拉达在凡界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他们在美丑的两端,只有在神界才能结合在一起,神界之门一打开,就化为灰烬了。王安忆认为,他们在现实中就叫“爱情”。至于中间的第二层界面,艾思米拉达表面所爱的弗比斯、她表面的丈夫甘果瓦,都不过是外在的情节契机。换一角度,也可认为,从弗比斯、甘果瓦到克罗德、卡西莫多,对艾思米拉达的爱构成着不同层次。凡间的爱,与神界比,都是渺小的。
同样,《呼啸山庄》中,王安忆看到,构成神界的是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她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剖析这部小说,“我们,整个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的说法,“人类”指现实中的悲惨因果,“永恒”指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构成的神界。这样看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爱情之力“消灭肉体”的一个过程。
我们读这部小说,极易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因果,极端的彼此戕害所蒙蔽,不明白那是爱,恨的表象。艾米莉·勃朗特是以“我”——洛克伍德先生拜访呼啸山庄开始叙述,她先通过洛克伍德的视觉,写希刺克厉夫的阴沉,凯蒂的冷漠,哈里顿的粗鲁唐突,写洛克伍德从一家人的怪癖中意识到神秘氛围,然后由女仆耐莉开始讲述故事。讲述几近整部小说,只剩下一年后洛克伍德重回山庄的一个尾声——希刺克厉夫完成了他对死亡的渴望,死了。之前,他就已买通教堂执事,在凯瑟琳身边给自己留下了墓穴,只待他下葬,就可把两边棺材板拉开,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了。耐莉的讲述,结尾,放羊的孩子已经看到他们了。王安忆非常感叹这部小说的结尾——它描写洛克伍德找到三块墓碑,中间凯瑟琳的已经让树丛埋了半截,埃德加有草皮与苔藓装点,希刺克厉夫还是光秃秃的。艾米莉·勃朗特让洛克伍德感叹:我真难以想象,这么平静的墓地底下,有不平静的睡眠。
将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定为神界,凯瑟琳与埃德加错位婚姻带来的悲剧,希刺克厉夫一连串极端的报复行为,就都是表象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艾米莉·勃朗特体现着“一切才力中最罕见的才力”,这才力就是,挖掘出了“潜伏在人性幻象之下,并把这些幻象提升到宏伟壮丽境地的力”。也就是说,极端行为只不过是“人性幻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宏伟壮丽”之力,在小说中是令人战栗的情节——凯瑟琳临终前在希刺克厉夫的怀里告诉他:“我现在心急火燎想逃到那个灿烂辉煌的世界里去,不是透过这颗疼痛的心的壁垒去渴望它。”他俩,彼此撕碎,彼此谋害。凯瑟琳对希刺克厉夫说:“我希望能抓住你,一直到我们俩都死了,我不关心你受了什么罪。”希刺克厉夫就在她下葬那晚去挖坟,要去打开棺盖时,听到了叹气声,“有实实在在的躯体在靠近他”,她就在他灵魂里,带着他回家了。希刺克厉夫最后的死亡过程,他显然看到了凯瑟琳,像是被光芒照亮了。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能使生活摆脱对事实依赖”的“罕见的才力”。王安忆在这极致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无疑启发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她说,有两类作家写爱情题材,“九类作家”热衷这题材,是为制造人生美梦。优秀作家非但不给人生造梦,还要粉碎人生美梦,爱情题材就非常有飞翔力。“要有足够力量,才能飞得特别高。”
相比较《巴黎圣母院》与《呼啸山庄》,《复活》是更平直的叙述。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写聂赫留多夫在陪审席上面对罪犯玛丝洛娃,他要写这两人的纠葛,不同的原罪,写两人不同的觉悟与互相映照的自救复活之路,用的是按部就班特别笨重的线性叙述,写出分别代表贵族与贫民的两个复杂人物的心路历程。走过整个80年代后,重新认识19世纪文学,在90年代初,在一些优秀作家中是不约而同的,只不过认识层面不同。王安忆的杰出认识是,她意识到,我们这代人80年代如饥似渴、争先恐后阅读的20世纪文学,其实多数是一个个期望标新立异的作家,以独特性取胜的特别的小说。这种特点突出的小说,其实易模仿,思想与形式的地盘一旦被占据,就要另辟蹊径。而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其实是没有特点的,越是好作家就越不具备特征性,他们不以特征性取胜,靠的是高度。她认识到,托尔斯泰用最朴拙的方法,呈示出“最巨大、坚实、坚固”的材料,就能构筑出“相距最远的此岸与彼岸”。
对她而言,这真是一次认真的功课,边认真积累笔记,她已经开始写《长恨歌》了。(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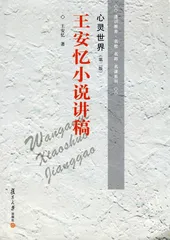 文学朱伟王安忆80年代
文学朱伟王安忆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