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之市
作者:唐克扬 城市里一直都不缺不大像“城”的地方——大部分的“市”,和建筑的永恒品性是矛盾的,也和现代城市的典型期待不同。因其简陋、临时,“市”恐怕是建筑师最头疼的一种建筑类型,是城市内外都有的黑洞。在《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这一类市场、集市就有了最形象的说法叫“草市”,大概是随风而起、随风而散的意思,它是反城市的、非正式(informal)的。
城市里一直都不缺不大像“城”的地方——大部分的“市”,和建筑的永恒品性是矛盾的,也和现代城市的典型期待不同。因其简陋、临时,“市”恐怕是建筑师最头疼的一种建筑类型,是城市内外都有的黑洞。在《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这一类市场、集市就有了最形象的说法叫“草市”,大概是随风而起、随风而散的意思,它是反城市的、非正式(informal)的。我们说的,可不是那种乔装成威尼斯宫殿的现代购物中心。清代皇帝在颐和园、圆明园中设置由宫人担任群众演员的“买卖街”,从货品到商人,从交易到消费,没有一样是当真的,而当代文旅部门为了吸引游客,也刻意打扮出来一些“农夫集市”“夜市小吃”。类似事业一旦有了规矩和成本,不管建筑师和艺术家将它们描画得如何平易近人,再不是这种空间的本意了。“正式”还是“非正式”,因此并不仅是形式的问题。 “城市”可以理解成城里有个市场,也可以是因为集市成就了城市。二者截然不同也有关联。即使在张择端上呈官家的图画里,沿街而建的商铺里,浮屋、欢门、彩楼这些光听名字就知道也是“临建”。你若看懂了这幅中世纪生活的画卷,就能体会画中的各类买卖空间,着力表现的并非永固的建筑,而是人情之盛。如同那艘不降桅杆就将撞上虹桥的河船,使力的船家和诸多“吃瓜群众”,一切都是在“变化”中臻于高潮。乾隆“买卖街”中,甚至有伪装出来的盗贼和小偷,有模有样表演这些事变。到今天,在南北各地的城乡接合部,这一类自发的“草市”精神依然如故,一样的喧杂一样的“临时”,只不过它们绝非扮演而是实况,地点从城门外大道旁换成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河冲交界的野镇——比起努力符合剧情,“演出来”的黎庶生活更一言难尽。
“城市”可以理解成城里有个市场,也可以是因为集市成就了城市。二者截然不同也有关联。即使在张择端上呈官家的图画里,沿街而建的商铺里,浮屋、欢门、彩楼这些光听名字就知道也是“临建”。你若看懂了这幅中世纪生活的画卷,就能体会画中的各类买卖空间,着力表现的并非永固的建筑,而是人情之盛。如同那艘不降桅杆就将撞上虹桥的河船,使力的船家和诸多“吃瓜群众”,一切都是在“变化”中臻于高潮。乾隆“买卖街”中,甚至有伪装出来的盗贼和小偷,有模有样表演这些事变。到今天,在南北各地的城乡接合部,这一类自发的“草市”精神依然如故,一样的喧杂一样的“临时”,只不过它们绝非扮演而是实况,地点从城门外大道旁换成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河冲交界的野镇——比起努力符合剧情,“演出来”的黎庶生活更一言难尽。
千百年来,以集市为代表的非正式空间一直存在。在这种无明显秩序的空间里设计师无法找到支配的快感;平时十块此处八毛,如此消费降级的市场,其兴旺根本不是靠“设计”的。和非正式空间(informal space)紧密联系的,是非正式经济(informal sector),它们逃脱了税收城管,也剥离了官方统计数字,却是人类生计重要的一部分。
应该也没有多少领导喜欢管理市场,即使城市里有管制的市场也和体制隐含冲突,只是程度深浅。不过,这并不妨碍管理者们自己常出入类似市场,从古至今,自由贸易对冠冕堂皇的人性都构成某种程度的侵蚀,“五品之上不得入市”“公主不得游市”(《唐会要》),这种禁令正好证明了此类爱好的普遍。我本人不止一次地逛过北方的大集、南方的墟市,在那个商业文化尚不发达的时代,我们与其说是想买点啥,不如说是一种对枯燥城市生活的逃离和放松。最早,这类集市甚至没有明确的地址,比如著名的白沟,位于北京、天津和保定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人们远远就能看见的不是建筑,而是乌泱泱的人群。一些商铺有遮盖,但大部分没有,很多集市靠着河港泊头,一些场地未经铺砌,下雨天都是问题,至于摊位的摆法更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就是板车、驴车、三轮、农用车……本身成了货架,这和今天的“后备箱集市”如出一辙。入夜,人们惊异地发现,早有人为大家扯好了七倒八歪的电灯电线——那时还没有穿制服的城管,有的似乎只是免费的福利。
在规划的手指不及之处是古代人口中的“隙地”,现代人心目中的则是闹腾、热辣的“草台班子”。草,指的还是“草市”不上台面的质量,但是大众喜闻乐见,“隙地”并非毫厘,而是细微的单体乘以庞大的数量。按说,这个课题根本进不了大学的设计学院。设计了中央电视台大楼而有争议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自己的学生合编过一本别出心裁的书,叫《哈佛购物指南》——它意外地将高冷的学府和通俗的购物结合在一起,绝非指导你如何获取常青藤纪念品,相反,这里凸显了现代人才懂的矛盾:现在,大家明白,就连做学问,服务的也是经济发展了,一方面研究物质的世界,一方面又无法完全丢弃超越的思考——城市里这些不上台面的空间,岂不也是一回事?你无法否认,正是那些满足口腹之欲简单声色的“草台班子”,让本来绝望的空间起死回生。
购物其实并无哈佛、蓝翔之分。大都市里令人眼巴巴的橱窗购物(window shopping)和实在的热气香味,在乡村大集中一样并存:你有可能看到真的也绝对会买到假的,你收获的,同时是票面价值和可能不值钱的眼福,这种错乱,对城市平民的欲望与想象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教会了他们“市场”两字同时意味着风险和机遇。集市的参与者并非都是懵懂的,这里断然存在着索取与供给的同谋关系,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空间中“赶集人”自动变聪明了——牵涉到你的切身利益时,庞大的空间不再仅仅是风格或造型,而是复杂的结构与关系。 从貌似不太高大上的集市中学习具体的空间营造,库哈斯并非第一个。比如,很久以前,欧洲的建筑理论家就意识到,市场中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营造模式:一种尚存最基本的特殊性,拱廊街边缘的商业依然附着在城市街区的大体上,就像“买卖街”的演出取决于两侧深藏的宫室,空间结构存在着正中/侧面、基座/楼上等差别,在这里,人们辨认出的是品牌和A货的不同,或是奢侈向通俗的过渡;另外一种,类似于白沟大集,却不在乎“千市(城)一面”了,因为荒地上根本没有规划,甚至没有固定用地和入口。对于它们的消费者来说,逛集的乐趣,并不只是最原始的物物交换,而是无目的无预设的闲游。后者的规模和时间保证了空间的强度和效益。
从貌似不太高大上的集市中学习具体的空间营造,库哈斯并非第一个。比如,很久以前,欧洲的建筑理论家就意识到,市场中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营造模式:一种尚存最基本的特殊性,拱廊街边缘的商业依然附着在城市街区的大体上,就像“买卖街”的演出取决于两侧深藏的宫室,空间结构存在着正中/侧面、基座/楼上等差别,在这里,人们辨认出的是品牌和A货的不同,或是奢侈向通俗的过渡;另外一种,类似于白沟大集,却不在乎“千市(城)一面”了,因为荒地上根本没有规划,甚至没有固定用地和入口。对于它们的消费者来说,逛集的乐趣,并不只是最原始的物物交换,而是无目的无预设的闲游。后者的规模和时间保证了空间的强度和效益。
如此一来,摊位的“行”(也是行业的“行”)和“列”,再不需要有什么讲究了,它们并不存在显著的前和后、边角和中央的计较,顶多有个只有摊主自己记住的号码。对照后来兴起的人造购物空间比如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它们俘获顾客的效率不算高,因为百十个类似的叫卖者,不会有明确的吸引你的方位,你不容易直奔主题,而是迷路其中。对当代的某些“聪明”商场,例如宜家,这种貌似有缺陷的路线设计却是它们生意经的起点。在人类最初的市场分类中,你会看到一样货品后面“运输者—生产者—原产地”的社会关系链条,知道它们是生活日用、基本生产资料,还是超乎实用的高级制品。在现代,在很难不循环的回头路中,取代这一链条的是货品源源不绝且有无尽选择的幻觉——消费者走得越久,买得越多。
在这种延宕之中,在摊位前把腿走断的人反而收获了一天的快乐。这种快乐应该是限量版的,难怪古今中外的市场管理者,都需要严格控制市场开放的时间:“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非正式建筑史
受到极致非正式空间启发的当代城市,在空间类型上自有它的发明。比如,逛街的人最需要的还不是“街”,而是帮助“逛”的神器,于是,我们有了可以垂直往上,也可以水平移动的电动扶梯,方便了脚不点地的顾客左顾右盼,它们既可以是购物商场的标配,也可以用于图书馆、电视台、博物馆等处。在库哈斯的很多作品,比如巴黎国家图书馆提案和柏林荷兰大使馆中,都可以看到这类非传统的建筑要素的踪影,他的观点,空间的意义来源于内容,不是容器。
更深层次的发明受益于市场的结构。除了买者和卖者,中央(管理)元素,比如高高在上的市楼是另一个至要的存在(四川博物院藏东汉画像砖上就出现了它的身影),市场的结构基本上是扁平化的,但是身处十字路口市楼上,处在优势观察角度的市场管理员,早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眼中的绝不是平面构图而是秩序、纠纷、事变。按照《哈佛购物指南》的观点,当注意力集中在物(人)的关系而不是空间自身时,市场整个儿就成了一本三维的产品图册,对产品的货号、条形码、扫描器、取款机、广告灯箱(在古时这一切市场“基础设施”只是简陋不同而已)的关注,代替了入口、楼梯、厅廊、飘窗和外立面。
这样的市场中,风格(区分名牌还是便宜货)并不重要,功能(是否只能用于售卖)也变得可疑了。非正式建筑学内发生的种种变化,也可以轻易地适用于高大上的对象。比如,西方世界的市政厅同时也起源于它的市场,巴黎圣母院门前原本是群氓簇集的地方。因为本性卑下,我们很难记得“某一个”市场,更不要说它不起眼的容貌,那么瞧瞧建筑史中那些最有名的城市——看过库布里克版《斯巴达克斯》的人或许还记得,参与政事后,同情角斗士的格拉古议员出来顺手买了只鸡,仿佛衬托着他平民化的政治立场。事实上,在罗马共和国,元老院(Curia)旁最尊贵的权力空间确实是从一个集市发展而来的,尽管出身寒微,它却是今日罗马市“古罗马论坛”(Roman Forum)那些著名的神庙和宫殿的前世。
神圣和无聊确实可以彼此反转,这恐怕是“非正式空间”最重大的启发之一,就像今日不拘一格的网红视频,红极则黑。除了传出“鹿入市门”“家豕生子”(《旧唐书》)这样的市井新闻,“哭于东市”便是很大的政治事件了,可以吸引到中央一级的关注,小道消息在这里不胫而走,豪酋犯官也总是在长安东市狗脊岭、西市的独柳树被当众斩首。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不喜欢市场和市政广场混为一谈,这或许就是答案。可直到19世纪的伦敦,这样双面功能的市场还是层出不穷,城市想把市场和广场同为一种功能,这样不正经的市场却可能威胁到城市的庄严。
正是“非正式”的规模才兼容两种看上去不甚相容的品性,规模和与此相匹配的多样性,是“非正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指标。“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对于巨大利益的追逐,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而且,因为有可观利润贴补微薄基础设施,它们通常可以比其他空间得到更好的维护——比起那些要求高度精神自觉的文化空间(比如博物馆),市场中的文化成活率更高。有着清教徒式洁癖的城市规划,往往会驱逐野生情侣;但临时市场就像露水姻缘,“快闪”实则是一种都市情感的狂欢,它缓解了梦想其实难以成真的焦虑,使得被“正式”所压抑的人性得以释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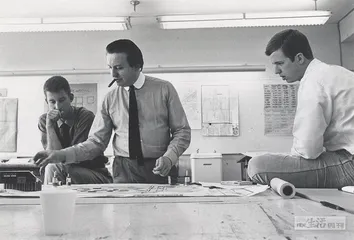 过去的城市难免会有各种“临时”,时间的灵活贴补了空间的不足,“偶然”成为非正式的护身符,今天可不一定了,“临时”会被“正式化”的强大诱惑力撕扯,营造手段也逐渐升级。早在罗马向帝国转换时期,不大周正的小市场空间已被庞大规整的皇家新集市(比如图拉真市场)逐渐取代,格拉古从农夫手里买鸡的场景不合时宜了;现代人因为有了强大高效的结构工程能力,他们的此类空间保持了自发市场规模的同时,已经不需要再简陋和“临时”。巴尔塔(Victor Baltard)设计的巴黎大市场是现代以前的集市奇观;双曲薄壳结构,也称为蔡司-迪威达格型体系(Zeiss-Dywidag system),造就了法兰克福、莱比锡和布达佩斯都不罕见的穹顶市场,商贩们在此的聚会依然是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空间内,室内没有额外分割依旧熙熙攘攘,你可以暂时觉得自己还是置身于现代城市之前的乡村。米兰和仙台都还看得到半通室外的室内商廊,但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商业了。CBD或是购物街现在绕来绕去都出不来,但是“非正式建筑学”一旦真的介入城市,总会让一切最终变得“正式”。
过去的城市难免会有各种“临时”,时间的灵活贴补了空间的不足,“偶然”成为非正式的护身符,今天可不一定了,“临时”会被“正式化”的强大诱惑力撕扯,营造手段也逐渐升级。早在罗马向帝国转换时期,不大周正的小市场空间已被庞大规整的皇家新集市(比如图拉真市场)逐渐取代,格拉古从农夫手里买鸡的场景不合时宜了;现代人因为有了强大高效的结构工程能力,他们的此类空间保持了自发市场规模的同时,已经不需要再简陋和“临时”。巴尔塔(Victor Baltard)设计的巴黎大市场是现代以前的集市奇观;双曲薄壳结构,也称为蔡司-迪威达格型体系(Zeiss-Dywidag system),造就了法兰克福、莱比锡和布达佩斯都不罕见的穹顶市场,商贩们在此的聚会依然是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空间内,室内没有额外分割依旧熙熙攘攘,你可以暂时觉得自己还是置身于现代城市之前的乡村。米兰和仙台都还看得到半通室外的室内商廊,但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商业了。CBD或是购物街现在绕来绕去都出不来,但是“非正式建筑学”一旦真的介入城市,总会让一切最终变得“正式”。
1993年,港英政府终于拆毁了6英亩大、约2.7公顷的九龙城寨。因《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遗留的这一“界中之界”,一段时间内是传奇的“三不管”空间:5万多名居民,蜂群一般,密密麻麻住在一堆城中村建筑的聚合体中,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笔下的黑暗世界,这里违建四出,帮会云集,黄赌毒俱全,成为东亚各种地下文化的“异托邦”空间想象的对象。九龙城寨本酷似一标准的现代“社会住宅”(social housing),是自我发育城市的神奇样板,够“非正式”了。它显示了现代主义“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望一旦落空,低标准的空间可以多么“堕落”;对于切身利益与此无关的人而言,这种“非正式”是一种恶趣味;换了出奇招的文旅产业,它没准还是值得效仿的商业样板。
只是,和乡村大集相比,城寨毕竟依托实实在在的门槛更高的建设手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一旦消失也很难再生。我们看到,“非正式”并不只是无规划的“弱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而是依托于特定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即使强有力的建设手段,在管理员消失的时候,一样可以变得无法无天;话说回来,这种生活方式哪怕是像类型片一样火爆,图新鲜的人们,总会渴望着回到某种确定的空间秩序中,复又感到新一轮的厌倦。 研究集市最多的不是建筑学家,而是经济史学家。集市的数量和分布密度,甚至具体地点都和特定的经济规律相关。许檀证明,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市,平均每集市的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此类集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并不像现代规划那样,重视物理空间确定的范围,如果我们考虑参与集市的人的因素,“交易半径”是一个更灵活的界定此类空间的指标。
研究集市最多的不是建筑学家,而是经济史学家。集市的数量和分布密度,甚至具体地点都和特定的经济规律相关。许檀证明,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市,平均每集市的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此类集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并不像现代规划那样,重视物理空间确定的范围,如果我们考虑参与集市的人的因素,“交易半径”是一个更灵活的界定此类空间的指标。
学者发现,平原的“交易半径”大概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这些数字透出的信息是“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对于不同的赶集人,生活世界的范围实则是由步力所及决定的。在没有高铁和高速公路的时代,它一样显示了灵活性(mobility)对城市形态的重大影响,我们习惯了城市里有边界和门禁的“销品茂”(shopping mall),而这类因为交换——交通和置换——而形成的聚落,不像正统思想要筑“城”才有市,而实实在在是因为“市”才有城(镇)。前者意味着先设的秩序,后者却是“变化”的结果。
再妖娆的形式也难以一笔画出这样的“非正式空间”。经济学家更擅长的数字,呼应着一个时期和地区市场和货源的律动、货品和花样更换的频率、营销计划和折扣方案的效能……自古如此,现代人的赶集,不过产生了更多地点和意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就是经济学家也是无法解释的——取决于你从哪里来。对城市人,“非正式”充满了野趣,对另一些人,“正式”让人心跳加速。路遥的《人生》之中,那个渴望着脱离农村命运的主人公,正是走到大马河与县河交汇的地方,意识到了自己要干的事和人生理想的冲突:“……他又来了。再不是当年的翩翩少年,衣服整洁而笔挺,满身的香皂味,胸前骄傲地别着本县最高学府的校徽。他现在提着蒸馍篮子,是一个普通的赶集的庄稼人了……”
“市之城”正是法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口中的“非场所”(non-lieu),典型的“非场所”比如高速公路既不是都会也非荒野,现代交通工具和建筑学手段极大地推动了“非场所”的升级换代。只是,它并不一定要体现为奥热难懂的“超现代性”,比如有着水路交通之便的南方市镇更容易孕育独特的无边无际的城市形态,人和人更自由方便地链接,而不必定会产生有圈城墙的北方土堡。除了技术手段,“非场所”和古老的人性论关系更密切,一个人在任何时代总会给自己拘束和轻松的不同选择,也许是刻意逃避足够的、确定的意义,“非场所”一定同时也是我们所说的“非常(informal)所”。
有意思的是,城市如今的商业中心已经不容易区分“正式”“非正式”了。它们很少向街道开放,多数有着一个共享的内向的中庭,里面通俗端庄应有尽有,在这儿待上一天,无始无终的空间自然也就成了“非场所”。“非场所”在为生活创造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抹杀这种生活的物理特征。购物空间往往是内向的、迷宫般的,且没有一扇窗。商家有无数种手段将它们打扮成你想要的样子。
商店难免倒闭,但商业并不会消亡,尤其那不起眼的空间的魅力,来自无意义的物质生活和枯燥的生活意义之间的消磨。一般来说,这过程并不能将你的精神送上超越之旅,但是它也不容忽视。过去,对一个在寂寞中度日的人,赶集仿佛是过节,会慢慢从陌生、恐惧,变成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只是如今你好像每天都在过节。
舒勒(Montgomery Schuyler)曾经评论说,上述空间的形成过程未必就是一种(可以察觉和设计的)建筑景观,“但是它(一旦起作用)……就像城市商业本身”;对于汉语造词法而言,“市”也就是“城”,在真实生活里两者很难区别。喜欢正式不正式的空间都是同一个我们。 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