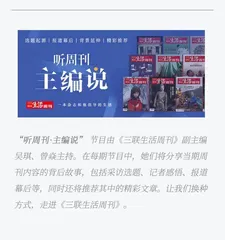主编说 | 时隔一年,我们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作者:曾焱2023年4月,因为ChatGPT的问世和爆发性表现,我们曾以《ChatGPT改变世界——重新认识工作》为题,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一次封面报道。在2024年第五期,我们再一次以人工智能为主题采写了封面报道,题目是《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对齐》,而原因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再次超越界点:一方面,ChatGPT飞速升级为4.0,与用户交流的方式从单纯的文字增加到了图片,它不但可以描述图片,并且可以根据文字描述来生成图像。另一方面,是全球各大科技公司这一领域研究的竞争白热化,随着谷歌Gemini的出现,研究者预测,通用人工智能将在未来5到10年内诞生。
何为通用人工智能?我们大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能够完成多种工作的深度学习系统——这种系统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表现得不逊色于人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工智能崛起的真正起点。
虽然最终未能如计划地接近Gemini 等最新进展的研究者,但科学主笔苗千仍通过对相关研究人员和观察人士的采访,对人工智能这一年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讲述。比如他采访了在美国硅谷专攻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的学者,也采访了斯坦福大学芬恩教授研究团队:去年年底,有一段在网络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机器人工作视频,而芬恩团队正是这款机器人的制造者,他们的课题是让机器人通过“模仿学习”来完成复杂任务,这也是去年在Gemini之外另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进展。
记者陈璐对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AI安全与治理中心执行主任杨耀东的采访,则想要回应另一个迫切的重大问题:目前主流学术界已经认可将人工智能列为与核武器、流行疾病并列的人类所面临的危险,那么人工智能对齐就成为迫切的技术问题,即,如何让大语言模型、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向人类看齐,理解人类的思想、行为,并遵循人类基本的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而超级对齐则是,在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时,如何实现对齐。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研究领域,相关信息尚未公开。
除了专业领域的研究者,AI和普通使用者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在这个封面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们和大家分享三个个体故事,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而他们和AI的工作关系,对AI伦理的认知,都各有方法和观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这一年多来,人类尝试和AI共生的真实又现实的方式。
科幻作家慕明《与生成式AI共同工作的一天》。她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学习,2010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系,主修机器学习,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微软、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工作,2016年开始写科幻小说,现在是一个一岁孩子的妈妈,不久前从谷歌辞职。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爆发式发展,改变了许多人的工作方式。而慕明兼具技术工作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对AI如何影响内容创作的流程和未来非常感兴趣,在离开“大厂”员工的道路后,她开始尝试用生成式AI来进行写作,主要是合作剧本创作。但作为写作者,她更感兴趣的是想象力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化。而她目前的感受是:无论是预制的定制化应用还是自己训练的GPT,都无法代替她本人。
另一位作者高品天,是一位刚刚在德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他的博士课题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化学问答系统:在化学领域内,以用户问题为输入,自动查询数据库,输出回答。该课题涉及到大量的自然语言处理,也是人工智能之大语言模型中非常核心的技术环节。他的文章详细记述了在导师指导下建立这个问答系统的过程,而他在完成这一课题后,却感慨:很多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导师,都一度认为一个万能的、普适于各个领域的解决方案已经出现。但是,在我们用更审慎的眼光评估了ChatGPT之后,包括我们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都意识到,ChatGPT本身并不具备完全击败所有现有行业内专用问答系统的能力,更不用说作为一种通用工具取代所有专业化工具。
记者陈璐写了一位艺术家和AI技术之间的故事。艺术家郑曦然(Ian Cheng)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认知学,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艺术创作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还曾在乔治·卢卡斯的特效工作室“工业光魔”里工作。当他开始创作,就常在作品里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游戏引擎技术,探讨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与人工智能共存的可能性。如何看待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他认为对人工智能进行过度道德化还为时过早,现在应该做的是,做更大的梦。
———编辑/高一丁音频制作/张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