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形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尤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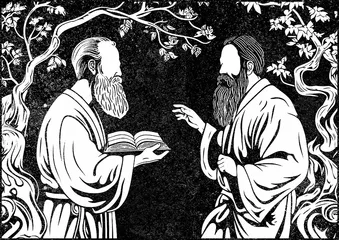 对于写得好的文章,我们也会赞一个“漂亮”,仿佛它模样周正、赏心悦目。反之,写得不好的文章就是丑、不匀称。不会写文章的人写作时往往像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越是着急往外倒,越是弄得一塌糊涂,一会儿让人来不及接,一会儿让人干着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风格感觉》中这样解释写作的困难:“作者的目标是用短语树将思维网编码为词语串。短语的树形结构能赋予语言以力量,表达观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一股脑儿地把观点都推给读者。接收者就会反向操作,把词语放进树形图中,还原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成功的写作就是词语没有形成树形结构,而是成了一根根光溜溜的树干或者枝条相互缠绕的大树。
对于写得好的文章,我们也会赞一个“漂亮”,仿佛它模样周正、赏心悦目。反之,写得不好的文章就是丑、不匀称。不会写文章的人写作时往往像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越是着急往外倒,越是弄得一塌糊涂,一会儿让人来不及接,一会儿让人干着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风格感觉》中这样解释写作的困难:“作者的目标是用短语树将思维网编码为词语串。短语的树形结构能赋予语言以力量,表达观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一股脑儿地把观点都推给读者。接收者就会反向操作,把词语放进树形图中,还原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成功的写作就是词语没有形成树形结构,而是成了一根根光溜溜的树干或者枝条相互缠绕的大树。
文章是思维的外在表现,人的思维本身就有不同的模式。《文本语言学》一书中说,世界各民族的思维模式大致有四类:东方型、闪族型、斯拉夫型和英美型。东方思维是螺旋型,语篇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反复性,作者谈完后面的问题后,可能又会回过头来谈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英美型是一条直线,语篇的推进是一往无前。闪族型是多头并进的往复式,斯拉夫型是曲折向前。
西方人觉得如果把文章写成螺旋型的,会让人觉得作者不自信、不谨慎,生怕自己前面没讲清楚。朱光潜先生在《谈对话体》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描摹:“中国人作文章真正要‘布局’,西方人作文章实在是‘理线索’。拿用兵打比,中国文章是横扫,要占的是面;西方文章是直冲,要占的是线。中国文章有宾有主,有正有反有侧,较近于画;西方文章像亚理斯多德所主张的,有头有腰有尾,较近于乐。这种异点反映着两种思想类型,中国思想偏向平排横展,西方思想偏向沿线直展。先秦诸子与柏拉图的对话的方式不同也就在此:一个是抱定主旨,反复盘旋;一个是剥茧抽丝,层层深入。”
我们可以引申一下:中国横扫型的文章是外向的,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和盘托出,一目了然,然后四面出击;西方直线型文章是内向的,作者自己孤军深入,以身示范。一位网友说:“中国的文章讲究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轻重缓急,也暗含乐理。”
思维的模式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写作的套路比较有限。美国作家冯内古特说:“我的梦想是用文字来做毕加索用绘画所做的一切,或是崇拜爵士乐者用音乐所做的一切。如果我打破了标点符号的规则,用文字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把它们杂乱无章地组合在一起,别人就不会懂得我写的是什么。因此,最好避免毕加索式或爵士乐式的写作。”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打破标点符号规则的作品,《尤利西斯》结尾的24048字只用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的第一句,有122个单词,只用了一个逗号,“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9月下午……”好比国画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墨点。 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