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阅读
作者:肖楚舟 这个夏天,电影《封神》第一部上映,掀起一阵神魔故事的热潮。翻翻评论区,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跟那些呼风唤雨的圣贤和神仙相比,两个妖怪引起的好奇和讨论似乎要更热闹一些,一个是从红颜祸水变成“哈基米”的狐妖妲己,另一个是从青面战神变成“丑萌怪婴”的雷震子。
这个夏天,电影《封神》第一部上映,掀起一阵神魔故事的热潮。翻翻评论区,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跟那些呼风唤雨的圣贤和神仙相比,两个妖怪引起的好奇和讨论似乎要更热闹一些,一个是从红颜祸水变成“哈基米”的狐妖妲己,另一个是从青面战神变成“丑萌怪婴”的雷震子。在那些长久流传的故事里,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更戏剧性的情节安在异类身上。妲己从普通人类变成九尾妖狐,又在这一版电影的诠释里变成知恩图报的动物精灵。《封神演义》里的雷震子本来是个正常长相的弃婴,误食师父仙杏才变得“面如青靛,发似朱砂”,在影片里却直接以浑身青黑、眼瞳金赤的妖孩儿面貌登场,大概是为了突出姬昌那句育儿经,“即便是妖孽,也要看所受教诲如何”。
给不可知的力量安上奇特的外貌,编造妖魔鬼怪之事,是人类天生热爱的游戏。有人因为雷震子鸟嘴人身、青面巨翅的外貌,把他和日本的天狗、印度的迦楼罗联系在一起。如果把“鸟人”的范畴扩大一点,还可以把斯拉夫神话里能让人失忆的美女鸟妖阿尔科诺斯特、罗马神话里的风神奥斯忒耳(一个大胡子男性鸟人)、美索不达米亚传说里的鸟人战神安祖算进来。
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古怪家伙,可美可丑,或善或恶,亦敌亦友,有时被叫作精怪,有时又近似神魔,可能与某种远古的神祇有点儿亲戚关系,也可能只是平常生活里随处可见的飞禽走兽、锅碗瓢盆。在妖魔鬼怪的故事里徜徉,我们难免惊叹,人类的先祖究竟是如何创造出这些奇特形象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为何依然沉迷于妖魔鬼怪的故事?讲故事的人,究竟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异界来客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异界来客
民俗学者和神话学者眼中,人类创造妖怪的初衷不是出于娱乐,而是源于恐惧、忧虑和敬畏。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专门梳理过《山海经》里的妖和怪,他把妖怪观念的起源归于对一切破坏秩序感的事物的恐惧,无论什么样的妖怪,它的存在本身就宣示着叛逆:“妖怪是打破了名与实、外形与属性同一性的叛逆者,平凡美丽的外表下藏匿着怪异或丑陋的真相,妖怪是世界平滑表面上突然出现的裂痕,是分类体系中无法归类的异类,是正常秩序中无法安顿的反常。”
刘宗迪让我想象一个古代中国人的“夜生活”,家宅和荒野不过一篱之隔,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野充满各式细碎奇怪的声响,那里面充满了可感可闻却不可见的恐惧。人本能希望将这些抽象的异常捕捉,划定为某种具体之物,才能够捕捉和降伏。因此中国最有名的妖怪,不是虎狼之类的猛兽,而是狐狸、蛇或者老鼠,“它们的特点就是离日常生活很近,打破了人跟自然的界限,也就打破了野性和人性的界限,它是自然界与崇高世界之间的枢纽”。
最原初的妖怪形象,刻画的是人类活动的边界。生活在山林中的民族,喜欢想象四条腿的怪物,因此印尼、印度、缅甸以及中亚、阿拉伯半岛都有独角兽的传说。海边的民族善于创造海怪,其中挪威人对海怪的问题最权威,18世纪的卑尔根主教埃里克·彭托比丹写到会喷火的海蛇的时候,甚至煞有介事地介绍它的产卵季节,还炫耀似的提到这东西在挪威司空见惯,“对他们而言,谈论海蛇就好像我们谈论针鱼或者鳕鱼一样”。
但我们真正熟悉的妖怪,比如在中国,并不是《山海经》里那种拉清单式的妖怪图谱,而是《封神演义》《西游记》或者《聊斋志异》里那些近似人类的精怪。本来是异类的妖怪,越来越有“人味儿”,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峰长年从事妖怪学研究,在他眼中,“先有妖怪,才有妖精”,妖怪的人格化是后世各类宗教、哲学思想不断注入的结果。东汉王充在《论衡》里将“精”“气”和妖怪现象联系起来,道家认为老去的事物便能成精,儒家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日本人信奉万物有灵、天命思想,都为妖怪注入了能和人比肩的灵气。这股“气”从狐狸精的鼻孔里跑出来,再收进道士的葫芦里去,也可以转移到草木山川上去。于是不该有灵智的东西,拥有了不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有了参与人间故事的资格。 这些“陌生之物”的命名方式,大致可分为妖、魔、精、怪这几种,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刘宗迪认为,“怪”强调的是外形古怪,只是因为不大常见而让人产生臆想;“妖”重在善变化、能害人,哪怕是平素常见的事物也可以化作妖,且常常是灾变的异兆。台湾学者范玉庭总结明清妖怪观时,在“异兽型”“妖征型”之外又加了一个“精怪型”,“精”的说法更强调万物有灵的理念,扩充了“妖”的范围,比如《太平御览》的“妖异部”专门有“精”这一节,山水草木之外,故道、故宅、故井都有精灵。“魔”则带有宗教色彩,佛教里的魔是阻碍修行的障碍,基督教里的恶魔是诱人犯罪的反派,妖可以行善,魔却不可能不作恶。当然,妖怪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可以灵活糅合。到了《西游记》里,“妖魔精怪”已经不分彼此,孙悟空到濯垢泉查问蜘蛛精来历时,土地公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灵有大能。”
这些“陌生之物”的命名方式,大致可分为妖、魔、精、怪这几种,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刘宗迪认为,“怪”强调的是外形古怪,只是因为不大常见而让人产生臆想;“妖”重在善变化、能害人,哪怕是平素常见的事物也可以化作妖,且常常是灾变的异兆。台湾学者范玉庭总结明清妖怪观时,在“异兽型”“妖征型”之外又加了一个“精怪型”,“精”的说法更强调万物有灵的理念,扩充了“妖”的范围,比如《太平御览》的“妖异部”专门有“精”这一节,山水草木之外,故道、故宅、故井都有精灵。“魔”则带有宗教色彩,佛教里的魔是阻碍修行的障碍,基督教里的恶魔是诱人犯罪的反派,妖可以行善,魔却不可能不作恶。当然,妖怪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可以灵活糅合。到了《西游记》里,“妖魔精怪”已经不分彼此,孙悟空到濯垢泉查问蜘蛛精来历时,土地公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灵有大能。”
因为本体不过是一团“精气”,所以在妖怪横行的世界里,时空拥有了超出现实的弹性,想象的迷人尺度也由此得来。南朝吴均写的《阳羡书生》,今天看来算是一个“盗梦空间”式的故事。阳羡人许彦肩背鹅笼行走,路遇一书生,要求坐到鹅笼中,途中休息时,书生口吐肴馔与许彦共享,并吐出一女子陪伴他。而女子又趁书生醉卧,嘴里吐出一个小帅哥来和自己约会。这小帅哥也不安生,又口吐一妇人相对戏谈。眼看书生要醒了,这几个套娃似的小人又一个个缩了回去。后人考证《阳羡书生》的故事应当来自印度《譬喻经》,但妖怪的故事却不囿于宗教的范围。到《桃花源记》里面,鹅笼成了层层洞开的异域空间,到《聊斋志异》里,又变成了道士巩仙的袖子,能装下一套豪宅,供书生与爱人结婚生子。
比起东方妖怪的灵巧变化,西方人的妖魔精怪要简单直观一些。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提出东西方妖怪的不同:“据说自古日本的妖怪是无足的,西方的妖怪有足,同时全身透明。由这类小事便可知道,我们的想象中通常都有一个漆黑的世界,而他们却连幽灵都想象成玻璃般通透。”顺着谷崎润一郎的思路往下说,东方人的妖怪遮遮掩掩,因为安于幽暗之美,“对阴暗并不会觉得不平,而是认为那是不得不尔之事势,于是坦然接受,还沉潜于阴暗中,发现自然形成之美”。富于进取心的西方人,总是“苦心孤诣消灭哪怕些微的阴暗”,因此面对陌生之物,他们更喜欢用一目了然的“杂交”来表达造物的神奇。
自古埃及和古波斯的时代就守卫宫殿大门的狮鹫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是陆地和天空的王者——狮子和老鹰的结合体,曾经遍布于中世纪贵族的家族徽章。到了16世纪,一个扫兴的博物学家论证它是一种“无聊的虚构”之后,狮鹫就失宠了。让它重振雄风的是另一次“杂交”想象,因为它被认为和马有点亲缘关系,以至于维吉尔在《农事诗》中编造了一个狮鹫和母马的爱情故事,用来比喻怪诞和荒谬。一直到现在,狮鹫和母马的孩子还是魔幻小说的宠儿,《哈利·波特》里的鹰头狮身有翼兽,就是它们的后代。
胡应麟写的《少室山房笔丛》里有一句话,说到唐代志怪小说蓬勃发展的原因,“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未曾发生的事情,因为可以随意发挥想象,而生出了无穷的乐趣。始于恐惧的妖怪想象,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并未消亡,反而愈发丰富,那是因为我们总是要学习如何与幽暗的影子相处——它可能是月色下的树影、山林间的洞穴,也可能是我们内心不为人知的角落。 如果写一本“寻妖指南”,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遇见妖怪的时机”。刘宗迪和我碰面时,指着被西晒烧得滚烫的窗子说了句玩笑话,“夏天是妖怪出没的季节”。仔细一想,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搜山捉妖的二郎神的生日在六月,许仙和白蛇是在夏日相遇的,白蛇显形是在端午,而海市蜃楼也是炎热天气里出现的幻象。如果非要有个科学的解释,“那只能说夏天植物繁茂,各种生灵活跃,山泽荒郊显得越发荒芜,人烟罕见,野物出没,同时夏天人又闲得慌,没事找事,想入非非,因此容易跟各种妖怪邂逅”。刘宗迪说。
如果写一本“寻妖指南”,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遇见妖怪的时机”。刘宗迪和我碰面时,指着被西晒烧得滚烫的窗子说了句玩笑话,“夏天是妖怪出没的季节”。仔细一想,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搜山捉妖的二郎神的生日在六月,许仙和白蛇是在夏日相遇的,白蛇显形是在端午,而海市蜃楼也是炎热天气里出现的幻象。如果非要有个科学的解释,“那只能说夏天植物繁茂,各种生灵活跃,山泽荒郊显得越发荒芜,人烟罕见,野物出没,同时夏天人又闲得慌,没事找事,想入非非,因此容易跟各种妖怪邂逅”。刘宗迪说。
日语里面还有个词语,叫“逢魔时刻”,指的是黄昏降临、昼夜交错之时,传说这时候最容易遭遇灾祸,或是容易遇到魔物。原理也很简单,天光黯淡,白日里轮廓清晰的山林草木,渐渐生出奇形怪状的影子,人间与妖界的界限模糊,在你眯起双眼辨认前路之时,或许已有一个心怀不轨的妖物尾随在后,算计着要如何把你拉入它的世界。
日本妖怪学家小松和彦在《妖怪的魅力在哪里》中说,妖怪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就是远离中心,边界模糊且阴暗的空间,又或是自身所属领域与异域交界的空间,也就是被叫作“边界”的地方。刘晓峰对这个“边界”有更清楚的阐释:空间论上的边界是与家相离的村界,时间论上的边界是昼夜之交、生死之界。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妖怪,是如何进入人间故事的?跨过界限的那一刻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对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和演变过程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要能生存下来,千变万化中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对于妖怪故事而言,“那个稳定的点就是人的生活。妖和人相遇,故事就开始了”。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妖怪,是如何进入人间故事的?跨过界限的那一刻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对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和演变过程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要能生存下来,千变万化中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对于妖怪故事而言,“那个稳定的点就是人的生活。妖和人相遇,故事就开始了”。
日本作家泉镜花出过一本集子就叫《逢魔时刻》,里面有篇《妖怪年代记》,讲热爱寻访妖怪的主人公特地跑到小城市的古宅去探秘,因为里面有个“打不开的房间”。传说初代女主人不愿让出宅子,就把自己永远地关在了里面。那个房间里看不见的鬼怪,很有参与人间事务的自觉。宅子里如果发生好事,她就嘤嘤嘤地哭个不停,如果发生灾祸,她就哈哈大笑。有一个晚上,这个“妖怪弹幕”突然默不作声了,宅子里的人反而感觉不习惯,跑进去看个究竟,故事就从屋主的妻子误闯房间的那一刻开始。
主动打破边界的从来都是人,怪不到妖怪头上。《太平广记》里讲了一个道士徐仲山的故事,他在山中偶遇暴雨,电闪雷鸣中看见一座宅院便前去投宿。宅内住着一大家子人,有主有仆,老爷子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徐仲山。好日子过了没多久,徐仲山非要去打开宅子里唯一一间密室,只见满屋鸟羽。结果妻子告诉他,自己一家子都是飞鸟成精,这下被他看破,已经有人放火烧山赶来捉拿,徐仲山就这样落了个妻离子散。
和“打不开的房间”类似的地点,还有无人的山林,人迹罕至的桥梁、渡口、隧道、密室。随着妖怪身上的崇高和恐怖意味逐渐消散,落入日常生活,变成不可思议的伙伴,那些标示着人类经验和常识的边缘地点,也可能是串联连绵情思的通道。
宫崎骏创作的动画片里,穿越边界的表达总是充满哀伤之美。千寻一家驾车穿过了一处荒僻的隧道误入妖魔之境。故事最后,琥珀川河神送千寻离开,还是要穿过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隧道才能回到人间。河神嘱咐她“千万不能回头”,千寻的背影微微颤抖,每一步都像踩在我们的心尖上。看过这些故事的我们,谁会不渴望一个来自异界的爱人呢?毕竟妖怪不用吃饭穿衣,它能用全部的生命来表达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爱意。
另一种,是精神或心理上的区隔,这让妖怪的故事多了一层隐喻,成了“人类世界的倒影”。刘晓峰分析过唐朝《广异记》中的狐精赵门福。唐参军碰到一个叫赵门福的和一个叫康三的来拜见,唐参军觉得来者是妖怪,避而不见,后来出门杀死了康三。狐妖赵门福却觉得自己本无恶意,遭到这样的不公对待,决意复仇,他慷慨激昂地说出复仇的原因:“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刘晓峰研究这个故事的时候,将赵门福的愤怒归为身份边界问题:赵张是中原大姓,白康指代归化中国的胡人,在兼容并包的唐朝,族类界限是开放的,已经认同了人类社会文化的狐狸自认为人也不足为奇,古板的唐参军却不肯接纳他们。赵门福和唐参军的冲突,反映的是界限感的冲突。故事最后的报复也很有意思,唐参军请来和尚驱邪,赵门福却化作祥云中的佛像迷惑和尚,劝唐参军买肉给和尚吃。正当和尚和唐参军克服了心理障碍喝酒吃肉的时候,狐狸现出原形,对他们嘲笑一番,从此消失无踪。到头来,他就是要唐家人承认一件事:界限在于内心,并无一成不变之理。人和妖是这样,人和人亦如是。 因为本质上不属于一个时空维度,妖怪反而显得比俗不可耐的人类要率直可爱。施爱东讲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一人一鬼相约种地,约好人收地面以下的,鬼得地面以上的部分,人提议种花生,鬼没头脑地答应了,结果这一年鬼颗粒无收。第二年,鬼以为自己学聪明了,要求反过来,人却提议种稻谷,结果鬼又什么也没收到。施爱东感慨:“人类是复杂的,怎么会像鬼这样傻傻信守承诺,吃了亏也不翻脸。正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才只能把这样的想象加在妖鬼身上。”
因为本质上不属于一个时空维度,妖怪反而显得比俗不可耐的人类要率直可爱。施爱东讲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一人一鬼相约种地,约好人收地面以下的,鬼得地面以上的部分,人提议种花生,鬼没头脑地答应了,结果这一年鬼颗粒无收。第二年,鬼以为自己学聪明了,要求反过来,人却提议种稻谷,结果鬼又什么也没收到。施爱东感慨:“人类是复杂的,怎么会像鬼这样傻傻信守承诺,吃了亏也不翻脸。正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才只能把这样的想象加在妖鬼身上。”
随着妖魔和人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要找妖怪倒也不必特地跑得太远。它可能就在卧榻之侧,餐厨之间,甚至与你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只是你还不知道而已。施爱东总结妖怪和人的故事的“套路”,无非分为妖怪害人和妖怪帮人两种。人与妖如何相处,决定了故事的走向。
说起来有些辛酸,人最常在妖怪身上寄托的,实际上是无处排遣的欲望。看妖怪故事,看的就是“缺啥补啥”的美梦。志怪小说里的妖怪常常变成美女或俊男,不求回报地给予主人公温情和陪伴,也是因为作者本人难以寻见理想的配偶。蒲松龄写的绿衣女,纤纤细腰,歌喉婉转,临走的时候变回了蜜蜂本形,还知道在纸上“走作谢字”。小泉八云写的《雪女》本是吃人的恶鬼,因为爱上了俊美的男人便以身相许,男人说漏了嘴,雪女如冰雪般消散,最后并没杀死丈夫。这样的大度,在人化成的怨鬼身上却是很难看见的——同样是小泉八云的《怪谈》里面,武士的妻子因为丈夫不信守誓约,死后化作怨鬼,摇着心爱的手铃,生生拧下了新妻子的脑袋。
很多时候,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妖怪,反而能说出人的真心话。《阳羡书生》里从鹅笼里钻出来的小人儿一个比一个心直口快。书生吐出来的女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家主的厌烦,“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世间男女,虽然明知口是心非不对,谁又能做到从来以真心示人呢?也只有借妖异之物的嘴巴,才能大放厥词了。 妖怪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面,高中生夏目贵志得到外祖母留下的一本妖怪名录,所以总是碰见前来讨回名字或者抢夺名录的妖怪。他的招牌动作,就是双手合十,口含外祖母与妖怪订立的契约,凝神吐气,念出妖怪的名字。
妖怪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面,高中生夏目贵志得到外祖母留下的一本妖怪名录,所以总是碰见前来讨回名字或者抢夺名录的妖怪。他的招牌动作,就是双手合十,口含外祖母与妖怪订立的契约,凝神吐气,念出妖怪的名字。
日本的许多妖怪形象来自中国,“归还汝名”的桥段也来自中国道家降伏妖怪的法门。道士写的书里面,最有名的是葛洪的《抱朴子》,此外《白泽图》《百鬼录》《九鼎记》都是妖怪词典一样的读物,目的是明了天下鬼怪姓名,万一遇到可以对照缉拿。名字或真身为何如此重要?仍然因为妖怪是破坏“同一性”原则的事物。刘宗迪打了个比方,“治妖如同治病,道破他的名字,就可以对症下药。道士知道了妖怪的名字,就等于揭破伪装,把它打回原形”。
关于称名的故事也发生在犹太人的创世传说中。夏娃诞生之前,上帝先创造了莉莉丝(Lilith),她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亚当热衷于给事物命名,莉莉丝却热衷于变幻成这些事物的形态,一会儿是蛇,一会儿是牛,一会儿是海鱼,向亚当展示它们真正的样子。亚当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字母(或者语言)才能揭示被命名之物的真正本质。
莉莉丝的含义是“夜晚”,她就像太阳下的阴影,认知外的幽冥。在变化万千的莉莉丝身上,妖异的存在好像一道利器,在事物的本体和标签之间划出一道缝隙。后来莉莉丝被上帝驱逐,因为她不愿遵守造物主确立的秩序,现代人却在她身上看见最早的女性独立思想:谁有权为我命名?我又岂止是一个名字?
“变化”是妖的独门法宝。孙悟空和二郎神的斗法,一个变麻雀,那个就变老鹰,一个变鱼,那个就变鱼鹰,无穷变化是征服对方的武器。胡适认为孙悟空的神通是从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神猴那里借鉴的,哈奴曼同样懂得变化取胜,他曾被一个老母怪(Surasa)一口吞下。哈奴曼在老母怪的肚子里把身子变得无比高大,对方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哈奴曼趁她身子变得极大时,突然把自己的身体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老母怪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裂隙,给了妖怪故事生长的空间。我们对妖怪故事的期待往往系于那些“面具滑落”的瞬间,等白娘子喝下雄黄酒露出蛇尾,等徐仲山发现房间里的鸟羽,等孙悟空一棒子下去叫美女变成画皮。当能人高道呼出妖怪的原型,万物归位,妖异不再,故事便结束了。生而为人的我们,也只能从想象回到无趣的现实中,徒留一些惊魂之余的惆怅。
妖怪的可爱,也在于出人意料的变化,能让平常的事物展现出有趣的性格。日本的妖怪文化里面,物品成精的故事特别多,从雨伞、木棍到草鞋,只要熬到100年,日常杂物都有成精的机会。其中最厉害的是“付丧神”,《金阁寺》里面说过他们的故事:一群即将成精的老物件被人扫地出门,因此怨气满满,商量着要报仇。但这帮家伙还是摆脱不了做物件时的性格:作为念珠的一连入道,总与佛经相伴,自然宽厚些,试图阻止众妖作怪。愤怒的大棒荒太郎将一连入道打得落荒而逃,而博闻多识的古文先生做了军师,组织大家在节分时去找造化大神许愿成精。
妖怪的好坏,其实是人心的映射。日本妖怪学家柳田国男谈到狐狸信仰时总结说,妖怪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它们带给人类幸运还是伤害,取决于人类的态度。过去被崇敬为神的狐狸,后来成为阴险狡诈的样子,又或者成为为祸人间的妖,乃至出现了“驱狐”的仪式,不是因为狐狸变了,而是人的生活方式变了,以至于“那些陈旧过时的信仰,只能蜷缩于一隅死撑苦熬,常常不得不妥协于时代的潮流”。
信仰的变迁,为妖怪的形象赋予了更多可能。中国的神魔小说里,人、神、妖、魔的界限趋于模糊,难分彼此,故事的意蕴又与神话和志怪里不同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可以被神佛收去当坐骑,《封神演义》里的凡人和妖魔都可以上“封神榜”混个编制。妖怪变得和人一样苦恼,要站队,要上进,也要困在阵营和等级里打转。于是人和妖物的斗争,也就等于和另一个自己缠斗。这个问题,唐僧在出发上西天前就看明白了,“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不能跨越的界限、不可挣脱的身份、说不出口的秘密,妖怪的面孔其实并不陌生。即使生而为人,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在某个时刻身不由己地成为“妖”呢?蒲松龄写的《罗刹海市》,最近被写进流行歌曲大受欢迎,大概就是说破了这层道理。罗刹海市的人以丑为美,误闯罗刹国的马骥先是被这里的审美吓得魂飞魄散,后来却乐于融入其中,抹黑了脸做起龙王的驸马。所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人和妖哪有什么界限,不过是语言的把戏罢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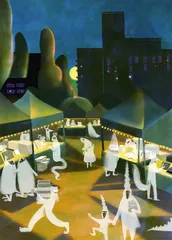 有位研究《山海经》的博士后朋友告诉我,她平时不大关注网络,前两天发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妖怪“相柳”居然上了热搜,大吃一惊,仔细一看才明白是因为近期热播的一部仙侠剧。《山海经》里面那个相柳,“九首人面,蛇身面青”,被大禹斩杀后腥血流经之地寸草不生。剧中的相柳却是白衣白发、俊美妖异的痴情将军。这么一来,相柳被斩杀的结局虽然不变,却显得凄美了许多。
有位研究《山海经》的博士后朋友告诉我,她平时不大关注网络,前两天发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妖怪“相柳”居然上了热搜,大吃一惊,仔细一看才明白是因为近期热播的一部仙侠剧。《山海经》里面那个相柳,“九首人面,蛇身面青”,被大禹斩杀后腥血流经之地寸草不生。剧中的相柳却是白衣白发、俊美妖异的痴情将军。这么一来,相柳被斩杀的结局虽然不变,却显得凄美了许多。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妖魔鬼怪的事情沉迷,大概就是源于他们身上无限可供虚构的可能性。志怪小说、神魔故事、神话传说,都不足以概括我们将要给大家讲述的故事。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对“精怪故事”的解释似乎可以借来一用:
尽管这本书叫精怪故事集,你却不大容易在书中间找到真正的“精怪”。会说话的野兽是有的,你多少会读到些超越自然的生物,还有许多不大符合物理定律的事件,但人们通常说的“精怪”却很少,因为“精怪故事”是一种修辞手法,我们用它来泛指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以前甚至现在的某些时候,这些故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在世间延续、传播,它们作者不详,却可以经由每个叙述者之口被反复地创作,成为穷人们常新的娱乐。
妖怪的故事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却比神仙的传说更加深入人心。明代学人胡应麟也对这种困惑做了分析:“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心里明知不好,嘴上忍不住要讲,精怪故事的魅力,来自于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
刘晓峰有个观点,“妖怪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重要补充”。他提到前南斯拉夫学者写的一本书《蜃气楼文明》,大意是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这样的文明发源地,从地理上看都是会出现海市蜃楼的地方。每当半空中出现不存在的楼阁,就仿佛径直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插入了另一个维度,“一旦出现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一下子就被打开了。高等文明都需要超越现实生活,建立起一种更高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超越契机就是不可思议的想象。”
帮助并不存在的妖魔鬼怪生存下来的,是我们对于虚构与奇想的热爱。法国人帕纳菲厄在撰写《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时断言,没有谁会真的喜欢描写自然本来的样子,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别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与老普林尼(古罗马学者,著有《博物志》)写尽了”。但这些神秘事物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它们让人逃离日常生活,令人好奇或沉醉”。和现实比起来,臆想之物的生命力要坚韧得多,科学家为了论证海怪想象的合理性,努力证明确实存在大约2吨重的章鱼,“但奇怪的是,自从这种动物变成真实的样子后,它就再也没有袭击过海船了”。
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理性认知远不能覆盖所有的未知,尤其是自己内心深处那些不可知的疑惑。强行摒弃虚构的魅力,反而会造成精神世界的狭隘。英国作家埃德蒙·戈斯出生在一个严谨的加尔文派家庭,他在自传《父与子》里面抱怨父母“错误地将虚构排除在我对事实的看法之外”。作为一个只听过传教士事迹,从不知道精灵、巨人、侏儒怪或者小红帽的孩子,他却没有变得坦率真诚,而是武断多疑,“对不加质询的循规蹈矩感到不满”。他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归为父母的教育,因为他们不让他沉浸在奇想幻象之中。
当我们不再相信床底有怪物、衣橱有鬼,或者天花板上的倒影是某种鬼怪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自己长大了,而那同时意味着我们告别了童年,告别了一个相信万物必有解释、存在即是合理的精彩世界。妖怪的存在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不可思议都有对应的姓名,也有解除的法门,如果你不害怕,也可以与它交个朋友。
这期的封面故事“夏日阅读”里,我们将讲述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神仙”与“妖物”,有的来自远古,有的和我们一样身处现代社会。从“塞壬”“鲛人”到“小美人鱼”,寻找关于人鱼的想象。从王小波的《绿毛水怪》,谈谈岸上的人类和海里的水鬼能不能深情。从《酉阳杂俎》和《阅微草堂笔记》,看看中国古人怎么借妖魔精怪讲人情世故。从安房直子的故事里,看日本人的魑魅魍魉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看看欧洲,为何浮士德能驯服妖怪,却拿精灵无可奈何。又或者在身边找找神灵的存在,看《美国众神》如何演绎现代人的迷信……
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借《小红帽》的故事,把人们对这类故事的迷恋讲得很透彻:“因为小红帽偏离了正确的路径,所以她来到了森林,遇见了狼、伐木工,与奶奶一起历险。如果不是因为小红帽偏离了正道,故事便不会发生。”妖怪的故事,就像突然从我们枕边岔开的一条小路。它不是通向地铁、写字楼或者学校,而是通往百无禁忌的不思议世界。在那些错误的路径上,两点之间不必是直线,我们听从自己的意志,选择想要停留的中点。在某个时刻,我们都甘愿当一个小红帽,被引诱,被捕获,在故事的密林里面,世俗又天真,“在林中漫步,自由自在,不惧虚伪的狼”。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及李天飞、赵爽、刘亚惟的帮助。参考书目:刘宗迪,《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刘晓峰,《唐代的狐狸与人间的秩序——古代世界的怪异与边界》;杨利慧,《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王鑫,《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日〕柳田国男,《孤猿随笔》;〔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迷人怪物:德古拉、爱丽丝、超人等文学友人》;〔法〕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博物学家的神秘动物图鉴》) 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