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诺奖在这里发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任晓远(发自斯德哥尔摩)
 10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开车去工作,以便可以提前下班,避开斯德哥尔摩的早晚高峰。中文互联网流传着一则故事,大意是说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会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多走一些路,目的是给晚到的同事留出离办公楼更近的车位,缓解他们迟到的焦虑。在我工作的大学,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便利的车位就像学术交流会的限量午餐和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先到先得。
10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开车去工作,以便可以提前下班,避开斯德哥尔摩的早晚高峰。中文互联网流传着一则故事,大意是说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会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多走一些路,目的是给晚到的同事留出离办公楼更近的车位,缓解他们迟到的焦虑。在我工作的大学,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便利的车位就像学术交流会的限量午餐和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先到先得。
这是个难得的秋日晴天,向阳墙面上的爬山虎已经通红,在晨光下显得格外耀眼。除此之外,这天和以往任何一个带着星期一综合征的周一并无太大区别。陆陆续续到来的同事们也都没有急于展开今天的实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秘而不宣的默契。直到有人问了一句:“大家都在等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吧?”气氛像被火柴引燃的木屑,迅速弥散开来。
从办公室的窗户望下去,公布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诺贝尔厅(Nobel Forum)仅百米之遥。我索性赶在公布之前,下楼去到门口。新冠疫情以前,除了预留出的媒体席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奖公布坚持对公众开放,任何感兴趣的人均可排队进入,发布会后的提问环节也并非专属媒体。疫情显而易见地改变了这一传统,2020年和2021年的发布会只对少量媒体开放。今年虽然增加了媒体席位,但仍未向公众开放,因此门口显得有些冷清。
我本着来都来了的心情推门走进诺贝尔厅,走廊上几家媒体已经开始采录素材。前台有两位女士拦住了我,语气柔和地问我是不是记者,有没有预约。我解释道,我有位中国的记者朋友来不了,我想拍几张现场的照片。她问我是否在卡罗林斯卡工作,我点点头。她面带笑容把我带进发布会大厅,耐心地等我拍完照片,又领我出来。对于本校的学生和雇员,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不吝给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机构的“特权”,来加强组织认同感。
赶在颁奖直播开始前回到办公室,同事们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坐在电脑前等待诺奖的宣布,还不忘开开玩笑,提醒彼此手机不要禁音,以免错过那通重要的电话。大家似乎并不热衷于预测诺奖将颁给哪个领域,大多时候甚至对此话题避而不谈。我也思考过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不确定性,长久以来的科学训练,让我们不倾向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妄下结论,而诺奖也确实常常爆冷;另一方面又来自于确定性,近些年大数据的加入,让这个竞猜游戏变得多少有些无趣。学术信息巨头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每年11月份都会公布一份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囊括了过去10年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6000多名科学家。自2002年起,他们还会公布一份经过甄选的“引文桂冠奖”得主名单。在接近20年时间里,只有396位科学家进入过这个名单,而其中的64位已经斩获诺奖。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由50名来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组成,他们有责任保守秘密直到奖项发布。过去几年中,我也偶尔在发布会前就从某几位诺奖评委的科研组里听到过一些笃定且精准的预测。或许只是巧合,却也难逃瓜田李下之嫌。这一特殊性,也让诺奖预测在卡罗林斯卡不那么主流。
11点30分,托马斯·帕尔曼(Thomas Perlmann)教授开始宣布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先用瑞典语,然后是英语。如果你懂瑞典语,你会比其他人早十几秒知道结果。因此瑞典同事第一时间转译给我们:“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一个瑞典人!”随后,我们马上意识到,同组的一位同事今年刚刚和帕博教授共同发表过一篇论文,阐述了印度次大陆上一小部分智人,因携带一个基因的尼安德特人变种,而变得更容易罹患炎症的生化学机制。我们纷纷转头对她表示祝贺,她也难掩惊喜之情,脸上洋溢着谦逊又骄傲的笑容。
之后我聚精会神地观看获奖简介。将一个科学家乃至一个领域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浓缩进10分钟的简介,本身就极具挑战。它就像一部《史记》般的科学纪传体史书,里面不仅有重要年份和重要事件,还隐藏着许多具有寓言意味的细节。
 我们该如何定义科学?尽管弗朗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创造了“ 科学”一词,英国科学理事会直到2009年才首次给出一个官方定义:科学,即运用系统性方法,基于证据,追求知识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
我们该如何定义科学?尽管弗朗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创造了“ 科学”一词,英国科学理事会直到2009年才首次给出一个官方定义:科学,即运用系统性方法,基于证据,追求知识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
经过漫长的积累,科学的体量已经大到惊人。现代科学家往往需要经年累月地深入一个领域的腹地,才有可能收获一些新的发现。一个博士生3到5年的工作量,对科学体系的增量可能只相当于一滴水。但正是这一滴又一滴的水,汇集成了科学知识的海洋。作为一个科学从业者,我时常觉得自己像《格列佛游记》小人国里的国民,在用放大镜观察一个庞然大物的毫毛。科学对求新、求深的不断要求,常常让科学家丧失整体的视角,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茫。
维生素C或许是我们最熟知的一种维生素,它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中留下过许多耐人深思的细节。我们现在知道坏血病是因缺乏维生素C导致,人类是为数不多的无法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哺乳动物,因此只能靠食物摄取。贯穿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坏血病是笼罩在水手头顶上的一朵恐怖阴云。罹患坏血病的水手,在死亡前往往表现出可怖的症状:牙龈和关节出血、满身瘀青、牙齿掉落、旧伤不愈等。我们在后世的文学,如《白鲸记》《1984》等作品中还常常能发现它的踪影。
当时的政府和船长都有预期,每次远航将有一半的船员死于坏血病。据估计,地理大发现时期死于坏血病的水手多于200万人,比死于风暴、沉船、海战和其他疾病引起死亡的总和还要多。英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鲍恩(Stephen Bown)甚至认为,能否找到治疗坏血病的良方,是当时足以决定国运的重要因素。
 1747年5月20日,在英国海军战舰做船医的苏格兰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为了找到治疗坏血病的方法,进行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对照试验。他将12名患有坏血病的病人放在一个船舱里,两人一组,分别给予6种不同的疗法:
1747年5月20日,在英国海军战舰做船医的苏格兰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为了找到治疗坏血病的方法,进行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对照试验。他将12名患有坏血病的病人放在一个船舱里,两人一组,分别给予6种不同的疗法:
第一组,一夸脱(约1.1升)苹果酒;
第二组,25滴硫酸(当时的英国人迷信硫酸可治百病);
第三组,两勺醋;
第四组,半品脱(约0.3升)海水;
第五组,两个橙子和一个柠檬;
第六组,一勺由大蒜、芥菜籽、树胶等草药制成的药膏。
只有服用了橙子和柠檬汁的病人从坏血病中康复了过来。
得益于林德的研究,英国皇家海军从18世纪末开始给水手们发放柠檬汁,用来防治坏血病。林德的研究不经意间改写了英国历史的走向。没有了坏血病的困扰,英国海军才可以依靠长时间封锁英吉利海峡来抵御拿破仑的入侵,并于1805年取得关键性的特拉法加海战的胜利。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坚信枸橼类水果(如橙子、柠檬)中含有一种抗坏血病的物质。1928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匈牙利化学家阿尔伯特·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偶然分离出了一种神秘的抗氧化物质。通过测算,他只知道这个化合物的分子式是C6H8O6,和很多单糖,如葡萄糖(glucose)、果糖(fructose)等分子(C6H12O6)类似,但对它的结构一无所知。于是他把它命名为古德诺斯(godnose),谐音God knows!(天晓得!)并尝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可学术期刊对他的谐音梗并不买账,他不得不改为“己醣醛酸”(hexuronic acid)才得以发表。后续的动物实验证明了己糖醛酸就是几百年来人类苦苦寻找的对抗坏血病的神奇物质。因此圣捷尔吉把己糖醛酸重新命名为抗坏血酸,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生素C。
回到匈牙利后,圣捷尔吉尝试从不同的植物中提取维生素C。但由于维生素C和糖类的结构近似,使得从橙子、柠檬等含糖量高的水果中纯化维生素C变得异常困难。一天晚餐,圣捷尔吉的妻子用匈牙利特产的红椒做了一盘沙拉。圣捷尔吉既不喜欢吃生的红椒,又不想让妻子失望。于是他说他需要把这些红椒带到实验室去做一些检测。结果出人意料,红椒是他发现的维生素C含量最高的蔬果之一,而且避免了纯化过程中糖类的干扰。
1937年,仅仅在维生素C的秘密被破解4年之后,圣捷尔吉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其在维生素C和生物能量代谢方面的重大发现。当时的圣捷尔吉完全没预料到,自己的重要发现,将和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产生深刻的联结。
美国科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因其对化学键本质和及其在复杂结构物质中应用方面的贡献,独享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是当之无愧的量子化学的奠基人,并深刻地影响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领域。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就是基于鲍林的理论。
 鲍林还是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活动家。有感于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二战”之后鲍林渐渐成为科学家群体中反对核武器的旗手,并因此受到美国麦肯锡主义的迫害。1954年后,他更是利用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联合全球近万余名科学家向联合国呼吁禁止核试验,还出书让公众了解核污染的危害。他的努力对促成1963年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授予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鲍林因此和居里夫人一起,成为唯二的在两个不同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鲍林还是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活动家。有感于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二战”之后鲍林渐渐成为科学家群体中反对核武器的旗手,并因此受到美国麦肯锡主义的迫害。1954年后,他更是利用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联合全球近万余名科学家向联合国呼吁禁止核试验,还出书让公众了解核污染的危害。他的努力对促成1963年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授予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鲍林因此和居里夫人一起,成为唯二的在两个不同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就是这样一位可以比肩历史上那些最杰出人类的科学家,却让自己在晚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科学争议。1966年,时年65岁的鲍林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表达了自己对长寿的渴望和延长寿命的野心。不久后,鲍林就收到一封来自艾尔文·斯通(Irwin Stone)的听众来信,信中他建议鲍林像他一样,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来维持机体健康并延年益寿,相当于当时学界推荐剂量的百倍。
我们很难得知,那时的鲍林何以如此轻信。在和妻子进行了短暂的尝试后,鲍林成了维生素C最虔诚的信徒和最尽职的传道士。他逐步加大服用剂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每天要吃下高达18克的维生素C。1971年,鲍林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一些不太严谨的动物实验集结成一本名为《维生素C和普通感冒》的书,开始向大众传播维生素C的“福音”。他凭借一己之力让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践行维生素C养生,并让美国各大药企的维生素C销量瞬间翻了几番。之后,鲍林还把维生素C的治疗领域拓展到精神分裂、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鲍林渐渐放弃了自己在化学方面的研究,醉心于证明维生素C是人类健康神药的研究中。
鲍林的行为得到学界几乎一边倒的不解和冷落,致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举步维艰。1981年,80岁高龄的鲍林在连续申请了8年之后,终于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获得了一笔2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用来支持他研究维生素C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的治疗作用。知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还不忘发了一篇名为《莱纳斯·鲍林终于获得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的文章,言语中多少透着些揶揄。一代科学巨匠,就此跌落神坛。
科学难以弥合的鸿沟
如今,我们似乎处在一个科学前所未有地昌明的时代,但世界好像也在前所未有地割裂。在社交媒体上,信息分布不对等,让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疫苗可以说是人类医学最好的礼物,最近几年却遭到愈演愈烈的“反疫苗运动”的抵制,导致一些本该濒临灭绝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卫生机构苦口婆心,世界卫生组织(WHO)甚至将“疫苗犹豫”和埃博拉病毒等一同列为“2019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但仍收效甚微。
很多医学问题还集中体现在物质分配的不平等上。来自美国的研究显示,新冠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与社会经济地位呈负相关。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往往从事基础体力劳动,无法远程办公且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其感染新冠的概率必然更高。与之相反的数据是,在非洲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新冠被视作一种“富贵病”,因为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高昂的检测费用。如果你觉得坏血病已经可以如此轻易地解决的时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数据显示,2010~2020年间,全英国坏血病的病例增加了一倍,多数是因贫困引起的营养不良。贫困是坏血病滋生的土壤,根除坏血病就像根除贫困一样困难。而这些鸿沟,单靠科学是难以跨越和弥合的。
我时常会想,如鲍林般的巨人殒落,科学本身是否也有责任。在构建愈发复杂和庞大的科学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对于大众显得越来越疏离。科学始终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实现和大众的沟通和互动,而不能单单依靠几个科学明星和大众连线。有时公众的盲从,使这连线变为操纵如木偶般追随者的悬丝。
科学内部的沟通也并非畅通无阻。回看林德治疗坏血病的实验,结论是那么的显而易见。接受橙子和柠檬治疗的病人恢复得如此快速和彻底,以至于他们很快就开始帮助林德照顾其他病人。但英国海军直到1795年——整整48年之后——才开始配给柠檬汁,许多水手在此期间并没有逃脱坏血病的魔爪。
究竟何以至此?1748年,林德从海军退役,开始着手编写一本学术巨著《坏血病论:对该疾病性质、原因和疗法的调查,和以批判性和时序性视角对该领域发表专著的回顾》(A Treatise of the Scurvy:Containing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Causes,and Cure,of That Disease Together with a Critical and Chronological View of What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e Subject)。和冗长的标题一样,林德的这本书共有400多页,他用了200多页的篇幅分了5个段落来描述他至关重要的实验。最后,他把最关键的实验结论浓缩进一句轻描淡写的句子:橙子和柠檬是治疗这种海上恶疾的良方。林德无意掩盖重要的结论,但他糟糕的学术写作和交流技巧使得最关键的信息被淹没。等这本书出到第三版的时候,连林德自己都忘记了哪些曾是他最重要的观察。加之出于“学术严谨”的考量,林德又加入许多含糊其辞的免责声明,导致他的论点看上去说服力不够,在学界并未引起反响。
1769年,一位年轻的英国医生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ark)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来破解坏血病之谜。在头一个月里,史塔克只吃面包和水,然后慢慢引入更多食物种类,一次只添加一种,并详细记录自己身体的变化。他的食物添加清单有牛奶、鹅肉、橄榄油、牛肉等。两个月后,史塔克的牙龈开始流血,他成功在自己身上诱发了坏血病。随后,更多种类的食物被引入,但史塔克还是在7个月后死于坏血病,终年29岁。新鲜蔬菜和水果在他的食物添加清单上,但处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他没有等添加蔬果就死于坏血病。如果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更发达,或许史塔克能读到林德的论著,从而避免在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医学烈士”的悲剧。
如果圣捷尔吉对维生素C以“天知道”(godnose)命名的主意被学界同行采纳呢?或许我们今天就能在药店买到“天知道泡腾片”和“果味天知道片”等维生素C类产品了。实际上,圣捷尔吉受妻子启发从红椒中提取维生素C的故事,出自其自传,真实性难以考据,但无疑给维生素C的发现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圣捷尔吉也和鲍林一样,在晚年践行维生素C养生,但他远没有鲍林那么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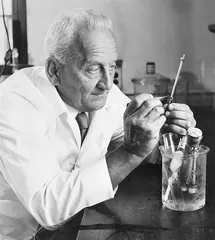 1954年12月3日,在鲍林即将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前,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有300多人参加的盛大饯行派对。鲍林的学生们编排了一系列搞笑的表演和合唱,串成一出名为《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的喜剧,现场充斥着欢快的笑声。其中有一首合唱,部分歌词如下:
1954年12月3日,在鲍林即将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前,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有300多人参加的盛大饯行派对。鲍林的学生们编排了一系列搞笑的表演和合唱,串成一出名为《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的喜剧,现场充斥着欢快的笑声。其中有一首合唱,部分歌词如下:
“鲍林的课无与伦比/鲍林的课沁人心脾/你能从中学到所有东西……
鲍林博士永远正确/他的双手强过一切/……”
鲍林形容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感受时说:“这是当代世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之一!”晚宴过后,诺奖得主们一致推举鲍林代表他们,向数百名手举火把前来庆祝的瑞典大学生发表演讲。他这样说道:
“或许,作为老一辈的我们,应该给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但我不建议这么做。我将给你们一些建议,告诉你们应该如何对待你的前辈们。当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辈跟你交谈时,请认真恭敬地听他们讲话,但不要相信他们。永远不要相信除了你自己的智慧以外的任何东西。你的长辈们,不论他是白发还是脱发,也不论他是否是诺奖得主,都可能是错的。随着年轻一代发现他们长辈所言之中的错误,世界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向前进步。因此,你们必须始终保持怀疑态度,始终为自己思考。”
显然,晚年的鲍林,只记住了年轻一代的对他的颂扬,全然忘记了自己对年轻一代的忠告。
 就在斯万特·帕博获奖的消息公布了几分钟之后,办公室关于帕博身世的八卦就流传开来,让你很难不去关注它。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于1991年设立,旨在奖励那些“乍一看好笑,后又引人深思”的科学研究。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研究八卦传播在社交中价值属性的一群科学家。他们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八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就在斯万特·帕博获奖的消息公布了几分钟之后,办公室关于帕博身世的八卦就流传开来,让你很难不去关注它。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于1991年设立,旨在奖励那些“乍一看好笑,后又引人深思”的科学研究。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研究八卦传播在社交中价值属性的一群科学家。他们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八卦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帕博的父亲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苏内·贝里斯特伦(Sune Bergström)。40年前,因其对前列腺素研究的贡献,和同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本格特·萨米尔松(Bengt Samuelsson),以及英国药理学家约翰·范恩(John Vane)共同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萨米尔松教授的办公室,与我们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最近几年我们越来越少看到萨米尔松教授出现在这里。帕博的母亲当时在贝里斯特伦的实验室工作,已婚的贝里斯特伦和她产生了一段秘密婚外情,并诞下了帕博。父亲只能每周周末出现在帕博的生活中,贝里斯特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把帕博这个私生子的秘密告诉他的“正式”家庭。
我和同事们也讨论了这则关于帕博身世的八卦,我们都不认同这和所谓的诺贝尔奖基因有关系,它也不应该和《冰与火之歌》里的琼恩·雪诺(Jon Snow)的身世进行浪漫化的对照。帕博父亲和母亲这样权力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在如今的瑞典社会是很难被接受的。贝里斯特伦如果在今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工作,很可能就此葬送职业生涯。我去年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妻子独自在瑞典,一边全职工作,一边带女儿,我只能在周末从巴黎飞回斯德哥尔摩陪她们两天。我深知面对这样的“幽灵父亲”,作为母亲需要付出怎样努力,承受怎样的艰辛。帕博出生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瑞典女权主义新浪潮的萌芽,通过女权主义者自上而下的游说,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育儿福利的覆盖范围。单亲妈妈的道德压力和经济压力得到全面的减轻,也间接保证了帕博相对安稳的童年。相比于帕博的“幽灵父亲”,他的母亲和瑞典社会或许才是他获得诺贝尔奖最可靠的支持。
第二天在办公室,那位和帕博一起发了文章的同事告诉我们,她陆续收到远在意大利七大姑八大姨的电话祝贺,着实让她有些措手不及。“我就不该告诉我妈妈!”她带着快乐的懊恼说。
瑞典同事也告诉我们,昨晚她对10岁的女儿说:“你知道吗?我的同事和今年的诺奖得主帕博一起发过文章。”她女儿表现得很激动:“真的吗?太棒了!那你同事会一下变成名人吗?”“科学不是这么运作的,”她想向女儿解释道,“恐怕不会那么快。但依旧很酷,不是吗?”她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在想象,这样的对话,会不会成为孩子偶然捡到的魔法豌豆?不同于杰克的豌豆,这颗豌豆不会一夜之间冲上云霄,它需要灌溉,需要时间成长。或许有一天,有人可以顺着爬上去找到宝藏,我们都要耐心一些。
我每年都会关注诺贝尔奖,对我这样的科学从业者来说,这是一种带着科学乐观主义的激励和启发。很多历史和细节慢慢演变成了科学寓言,甚至已经无关科学研究内容本身。就像没有人真的去深究,那颗苹果到底有没有砸到牛顿的脑袋。
(作者任晓远,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 瑞典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