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科生的思维读文史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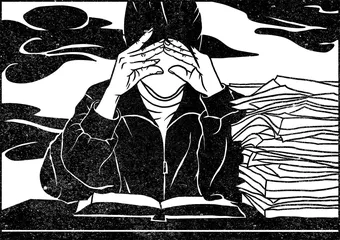 黄仁宇先生说我国古代缺少数目字管理,那我们就动手算一算。他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明朝皇帝要参加献俘仪式,仪式上,皇帝坐在午门城楼上,两旁站立着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刑部尚书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无可逃避),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
黄仁宇先生说我国古代缺少数目字管理,那我们就动手算一算。他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明朝皇帝要参加献俘仪式,仪式上,皇帝坐在午门城楼上,两旁站立着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刑部尚书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无可逃避),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
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觉得皇帝喊“拿去”很有意思,他用的是不是南京口音?要是唐朝皇帝,是用闽南语还是粤语喊?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想这2传4,而后8、16,后面到2的8次方是256,9次方就是512了,不会出现320或者360。难道现场没有配齐512人?而且这么喊的话,最前面的2人一共喊了几声?
《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凯特琳·莫兰给年轻人提了一个建议:“读自传,看传记片,在派对和火车上跟人聊天。任何像样的书都会包含作者当时知道的一切,所以如果你读完了,你就会像是过了你自己的以及他们的人生。再读第二本书,你就有了三种人生可以选择。”也许作者的人生选择也是从书中看来的,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有些省份要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但到上大学时还是要选专业,人有不同的性情因而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意大利作家娜塔丽亚·金兹伯格的父亲是一位生物学家,她的叔叔是戏剧评论家,一个理科生,一个文科生。她在《家庭絮语》一书中说,她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喜欢高山峻岭,喜欢巉岩,喜欢水晶和昆虫;有人讨厌大山,喜欢卡索拉蒂的画、皮兰德娄的戏剧、维尔兰的诗、普鲁斯特。“这是两个无法相互沟通的世界。在前面一个世界,一切都是清楚的,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神秘或秘密,后者总是有一些神秘的、莫测高深的东西。”她的妈妈既没有选前一个也没有选择后一个,她“时常是在这个世界里待一会儿,又在那个世界里待一会儿,在两个世界她都待得很愉快。因为她的好奇心从不拒绝任何东西,总是汲取一切养分”。这相当于接受了通识教育。她父亲就比较排斥文艺。
《世说新语》中说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小朋友确实很较真、很机灵,你说杨梅是杨家的,难道孔雀是你们孔家的?他使用了归谬法,按照孔君姓氏与同名物种有关的逻辑,会推出一个不靠谱的结论。问题是你杨家确实端出了杨梅,孔的推理还有些经验依据。再者,杨姓跟杨梅有关系的可能性要大于孔姓和孔雀有关的可能性:孔雀的孔是“大”的意思,如成语“孔武有力”,“孔雀”就是大鸟,这里的孔不是名词。如果是生物学家,知道杨梅的种属、有哪些近亲、孔雀的分布,就不会像孔君那样开玩笑了,也会给聪惠的杨氏子再上一堂自然课。 理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