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没有能力质疑现有的权力关系”
作者: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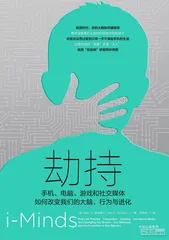 《劫持》
《劫持》
作者:〔美〕玛丽·K. 斯温格尔
译者:邓思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8年
这本书从一个治疗师的角度,描述数字媒介是如何影响儿童、夫妇、家庭和学习的。数字媒介则让社交霸凌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这种严重的大型霸凌行为在极端情况下会逼迫一个脆弱的青少年自杀。施暴者会通过行动和言辞对受害者造成生理或者心理伤害,比如攻击受害者的人格、自尊、自我价值、安全感,贬低或者摧毁受害者所珍视的东西。
施暴者的动机是享受受害者的恐惧和痛苦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等级。网上霸凌效果更严重,因为以前被霸凌的受害者通常可以找到一个避难所,比方说回家,或者去一个不同的社交圈。但现在他们不能。数字媒介可以到达一切空间,而且不会放过你。
网络霸凌泛滥的原因之一是行为的去抑制化,这个术语是由库珀、德蒙尼克和博格提出的,指个体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匿名提供了保护,线上公开或者半公开行为的代价相比于线下公开行为来说是非常小的。如果一群未成年人组织起来一起对一个过路的小孩说脏话或类似的内容,他们就会被惩戒,或者被送往校长办公室,甚至被开除。但是如果你在社交网络上这么说(你可以随后删除言论),则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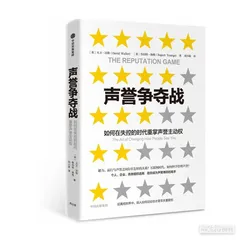 《声誉争夺战》
《声誉争夺战》
作者:〔英〕大卫·沃勒〔英〕鲁伯特·扬格
译者:刘小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8年
2015年3月,莫妮卡·莱温斯基在一场演讲中说,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骚扰滋生出种种危害——如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可以免于追责。人们在网络上对待彼此的态度可要比活生生面对面打交道时下流得多,尤其是网络匿名的庇护下。
2012~2013年间,涉嫌网络霸凌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数量增长了87%。心理学家约翰·苏勒尔将这种现象称为“网言无忌效应”,并将这种思想状态归因于网络权力机构的缺失和“匿名性”的强大威力(也就是说你对受害者可以没有同情心)等因素。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教授朱迪·奥尔森发现,人们在网上互动的过程中喜欢下论断,毫不顾忌自己所做出的结论是否建立在可靠的信息基础上。即便可供参考的信息不过寥寥,人们还是会从极其有限的信息中建立起一整套人格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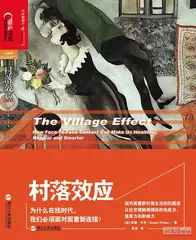 《村落效应》
《村落效应》
作者:〔加〕苏珊·平克
译者:青涂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面对面的交流好很多,但现在“社交网络”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它指的不再是你认识的人和你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现在指的是我们的电子设备之间的联系。在几十年前,大部分的社交互动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放眼现在,社交互动都“被脸书吸走了”。
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中,美国互联网专家阿曼达·兰哈特发现,32%的青少年都曾经亲身体会过网络羞辱的滋味。“卸掉了智能手机的伪装,网络上的恶霸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懦夫。但在网络上,他们会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他们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当侮辱的利箭击中了目标,他们也不必亲眼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受害者的网络社区往往会助长此类恶行,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群流行病学家发现,网络霸凌受害者的临床抑郁率,比“标准”霸凌受害者还要高。网络霸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虽然青少年受到公开羞辱,但是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遭遇深埋心底。在受到网络霸凌的青少年中,只有不足10%会告诉父母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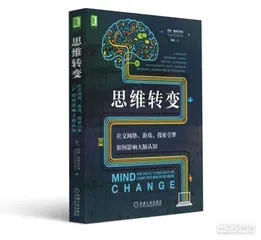 《思维转变》
《思维转变》
作者:〔英〕苏珊·格林菲尔德
译者:张璐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在2012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网络霸凌而自杀,其中有56%的案例都发生在过去的7年之中,44%都发生在过去的15个月当中。“或许是出于人类的本性,人们会在任何能容忍苦难的人身上再施加苦难,不论这种逆来顺受是出于真正的谦让,或漠不关心,还是纯粹的无能为力。”这种论调来源于1835年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
有专家争论道,互联网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会在自己与不道德的行为之间增加一些空间,从而实现道德分离。这种道德分离的过程描述了一个人是如何解除内心的道德控制的,这种道德控制原本会抑制他的行为。这种道德分离或许是网络霸凌的先决条件:霸凌者看不到受害者悲痛的视觉线索,由屏幕创造的距离压抑了其罪恶感和羞耻感。此外,由于年轻人把科技与线上游戏、朋友聊天、交换照片结合起来,网络霸凌往往和各种形式的娱乐手段相结合。研究表明,网络霸凌者往往很少悔改,这可能是因为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缺乏直接接触的缘故。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索尼娅·佩兰和伊芙琳发现,道德分离与网络霸凌没有关系。这说明网络会剥离受害者的人性,让他们显得不像活生生的人。霸凌者甚至不需要压抑自己的良知,他们在网上伤害他人之前不需要进行道德分离。
 《在群中》
《在群中》
作者:〔德〕韩炳哲
译者:程巍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9年
韩炳哲认为:“在数字媒体的交流中,恶意评论是一种固有的现象。网络的数字交流让人可以马上发泄冲动。这种即时性所传递的冲动要多于传统的模拟交流。数字媒体即是一种散播冲动的媒介。”
保持距离有利于公共空间的建构。然而,如今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种彻底的无距离感。数字媒体中的交流普遍消减了距离,空间距离的削弱带来的是精神距离的消融,数字的媒介性不利于尊重:“网络暴力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一种毫无敬意的、言行草率的文化中成为可能。”
数字居民汇集而不聚集,“没有灵魂,亦无思想。他们主要是那些独自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与世隔绝的、分散的隐蔽青年”。数字的个体偶尔会汇集在一起,组成例如快闪一类的群体行动。但是他们的集体行动模式却与动物群相类似,极其仓促和不稳定。反复无常是它的特征。此外,它还显得如狂欢节一样,轻率而又不负责任。网络暴力没有能力质疑现有的权力关系。它的目标只是个人,即诋毁他们并暴露他们的弱点。 网络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