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革命”一词时应该非常小心
作者:苗千 丹麦科学史专家赫尔奇·克拉夫(Helge Kragh)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曾担任欧洲科学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istory of Science)的主席。在2019年,克拉夫因为“对物理学史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对天文学理论和争论的分析,对量子力学中基本粒子和固态物理学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保罗·狄拉克和尼尔斯·波尔的人物研究”,获得亚伯拉罕·派斯物理学史奖(Abraham Pais Prize for History of Physics)。关于发生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及其影响,克拉夫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丹麦科学史专家赫尔奇·克拉夫(Helge Kragh)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曾担任欧洲科学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istory of Science)的主席。在2019年,克拉夫因为“对物理学史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对天文学理论和争论的分析,对量子力学中基本粒子和固态物理学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保罗·狄拉克和尼尔斯·波尔的人物研究”,获得亚伯拉罕·派斯物理学史奖(Abraham Pais Prize for History of Physics)。关于发生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及其影响,克拉夫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量子时代:20世纪物理学历史》(Quantum Generations:A History of Phys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书中写道:“在1945年后,物理学开始全速向着‘大科学’前进。尽管人们需要知道,这种高能物理学实验从来也不是典型的物理学研究方式。”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物理学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是战争、世界政治形势,还是物理学本身?
克拉夫:所谓的“大科学”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那时开始出现了回旋加速器和其他仪器,以高能的方式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可以说这是科学自身的需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例如“曼哈顿计划”同样也改变了科学——首先是在美国,随后影响了全世界——在战争过后,这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科学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终发展出广义相对论之前,爱因斯坦曾经热衷于阅读马赫、休谟、康德等人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之后,物理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哲学自身又有了哪些改变?
克拉夫:我认为哲学对于物理学革命的作用常常是被夸大了。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都不是依靠哲学家才产生的。哲学家们只是在这些理论形成之后才开始对它们感兴趣。对于现代物理学真正的哲学研究起源于80年代,而且在哲学界也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整体来说,物理学家并不了解哲学家们的工作,但是当然,哲学家们非常依赖物理学研究。因此,物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是非常不对称的。现在这种不对称比19世纪甚至是更早期更加的突出,因此我并不认为在未来哲学会对物理学发展有太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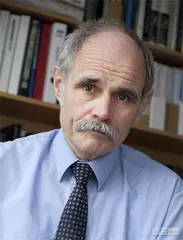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通过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机械式的牛顿世界观。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描述现代的世界观——究竟是量子式的,还是相对论式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通过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机械式的牛顿世界观。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描述现代的世界观——究竟是量子式的,还是相对论式的?
克拉夫:这取决于是谁的世界观。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他们的世界观依然是牛顿式的,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在科学界,世界观则同时是量子式的以及相对论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两种理论理所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中它们又各自都有着自己的角色。
(注:所谓“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主要是指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以及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地球运转,世界由“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构成。西方世界曾经长期接受这种世界观,直到17世纪牛顿世界观取代了这种传统观点。而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分别描述极小和极大领域的运动规律,两者的数学形式和结论并没有完全融合,因此也有可能导致人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
三联生活周刊:是从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科学开始不仅统治治理世界,并且开始统治社会、经济以及军事”?
克拉夫: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直到1920年,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才显得尤其重要。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科研,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来说都有重大影响。随后其他国家也开始跟进。目前在富裕国家里,尤其是美国,研发经费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3%。
三联生活周刊:在20世纪初,物理学以一种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进步,在这场科学革命中,之前19世纪的物理学研究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克拉夫:(19世纪的科研)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在使用“革命”一词时应该非常小心。因为无论是量子力学还是相对论,都是建立在19世纪的研究,以及更早时期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些基础(电磁学研究、热力学研究)就不会出现这些新理论。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科学革命产生出的成果中,广义相对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看上去它完全是一个天才的产物。如果没有爱因斯坦,人类有没有可能仍然无法发现广义相对论?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科学革命产生出的成果中,广义相对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看上去它完全是一个天才的产物。如果没有爱因斯坦,人类有没有可能仍然无法发现广义相对论?
克拉夫:这样说并不准确。广义相对论确实是爱因斯坦天才的产物。但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这样的成果,还有其他科学家(比如希尔伯特)也接近得到广义相对论了。假想如果世界上没有爱因斯坦,那么人类会不会发现广义相对论?我想会的,但时间会更晚。即使是一些极为抽象的理论也是科学界共同的成果,而非属于某一个天才。爱因斯坦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他没有发现广义相对论,其他人也会取得这个成就。
三联生活周刊:牛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天才。而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中,更多的天才涌现了出来。那么你认为科学进步与“天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克拉夫: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错误的。在1590~1690年之间的科学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科学天才”要比20世纪的“天才”更多,因为现代的科学进步更多依靠集体合作,而非单独的某个科学家。所谓“天才”一词本身就有问题,而且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无论如何,“天才”都要依靠一个共同体来认定其为“天才”。所以我并不认为在科学进步和“天才”之间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在现代,更难以发现像爱因斯坦或海森堡这样的科学天才了。但是科学仍然在稳步前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量子时代:20世纪物理学历史》一书中,将1918年和1945年作为三个部分之间的分隔点。那么你认为该如何描述战争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20世纪?
克拉夫:可以说科学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紧密了(主要是化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尤其紧密(主要是物理学)。在冷战期间科学与战争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今天看来,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似乎又没有之前那么紧密了——据我所知,相对来说只有较少的科学家在军方实验室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物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数学结构——比如弦论——希望统一在极小尺度和极大尺度的物理学。但是这样的数学结构远远超出了人类进行试验验证的范畴。这是否也是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呢?
克拉夫:确实是这样。弦论就源自人们想要统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想法。在另一方面,很多数学结构,包括无法通过试验验证的理论也可能在更早期就被发现,因为人类很早就有获得一个大统一理论的梦想。当然弦论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仍然有争议。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它是(大统一理论的候选者)。
 三联生活周刊:当爱因斯坦最初发表相对论时,这个理论被批评“过于数学化”,不够“日耳曼化”。现在,在21世纪,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科学研究中的“民族性”和“个人风格”呢?
三联生活周刊:当爱因斯坦最初发表相对论时,这个理论被批评“过于数学化”,不够“日耳曼化”。现在,在21世纪,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科学研究中的“民族性”和“个人风格”呢?
克拉夫: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民族科学”(ethnic science)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不当用词。科学是客观的和国际化的,与民族文化无关。当然存在有所谓的“民族风”(ethnic style),但这也只是关于风格而无关实质。早期的一些科学家在写作时通常会有“个人风格”(比如说玻尔和狄拉克),但是现在这种个人风格几乎完全消失了。非常不幸的是,现在的科学论文看上去都是没有个性、统一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能否想象下一次科学革命发生的场景?物理学大厦会不会再一次被摧毁?
克拉夫:我可以想象下一次科学革命——当然这仅仅是幻想。我不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会被摧毁,但是它会被逐渐精细化。(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中)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理论也没有被真正摧毁。人们只是意识到了经典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也在试图寻找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局限性——比如说在宇宙大爆炸的开端进行寻找。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是在神学、哲学还是科学领域,人们都热衷于寻找一个“大统一理论”。你认为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如果它真正存在的话,现代科学家是否正在逐渐接近发现它呢?
克拉夫:我们应该把“大统一理论”(Grand Unified Theory)和“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区别开来。研究大统一理论是一个实际的科学项目,但万物理论并不算——在我看来这更接近于神学。人们发现一个能够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是可能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理论并不存在。关于这个话题,我在《更高的猜想:大统一理论与失败的物理学和天文学革命》(Higher Speculations:Grand Theories and Failed Revolutions in Physics and Cosmology)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大统一理论物理科学革命世界观广义相对论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