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中国融入“科学全球化”的努力
作者:刘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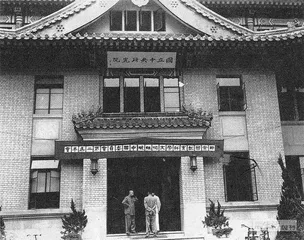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次年又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为什么20世纪初清政府就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科研能力才开始显现?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次年又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为什么20世纪初清政府就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科研能力才开始显现?
刘晓:可以从学术、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在学术上,1905年废除科举前后,中国有大批留学生留日,由于学制和基础等原因,他们中很少有人接触高校中最前沿的科学,大多回来做老师或参与政治、军事活动。1908年美国返还部分庚子赔款,中国学生开始成规模地留美。从1909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末有三届约180人的甄别生前往美国,此后设立清华学校,到1929年共选派1279名。早期留学生大多获得本科学位,回国创办高等教育。因为他们带回来的新思想,成为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些人培养的学生,在20世纪10年代后期出国留学,是中国第一批成规模的博士生,他们在20年代后期回来,才开创中国的科研事业。
从经济上看,中国只有到20年代末才有余力建设科研体系。“一战”结束后,列强无暇东顾,中国轻工业有了喘息的机会。国共合作北伐,初步实现政治和经济独立。那时中央研究院一个月的经费是10万大洋,北平研究院是3万大洋,相当于当时养一个师的军队。同时,继美国之后,法国、英国也相继退还庚款,庚款的指定用途除了培养留学生之外,也会资助研究机构,不少研究所就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设备或聘用人员。
从政治上看,在我国这样一个没有现代科学传统的国家,科研体制的开创需要强力政治人物的推动。从辛亥革命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十余年间,学界曾有数次设立国立科研机构的动议,皆因政局不稳和科技界乏人而失败。随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系列收回教育主权的举措也随之推行,目的是令教育规范化,一个是中央批准办学,一个是学校办学要规范,只有三个学院以上才能称为大学。
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除了宣示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也是蔡元培、李石曾贯彻“教育独立”理念的产物。起初在他们的设想中,教育体系应像法国一样,自上而下是一个“金字塔”。一个省里面有一所大学,大学设研究院,研究院管理大学,大学管理省内的中小学,撤销教育厅。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蔡元培、李石曾等辛亥元老开始有能力实现他们在国外看到的样板。
只不过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大学区制度的实验结果不符预期。起初谋划教育版图时,希望随着北伐,次第成立中央大学区(江苏)、浙江大学区,以及北平大学区,学区内所在的大学皆合并为一所大学,大学之上设立研究院。蔡元培就曾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因此举受到基础教育方面的抵制,撤销教育厅也导致行政事务不畅,最终改制失败。中央大学区的试验首先结束,蔡元培也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北伐推进到北平后,李石曾坚持在北平继续改革,而且主要引用留法人士。京津高校合并而成北平大学,迅速设立了北平研究院。然而,不仅中小学方面反对,而且学界的英美派也不合作,如北京大学的师生经常就此闹事,北平大学风雨飘摇,李石曾只好退出教育界,专任独立出的北平研究院院长。
李石曾效仿法国大革命的做法,将过去皇家的一些资源转为科研用途。如将清宫廷的动物园改组为天然博物院,北平研究院在那里开展生物研究。溥仪出宫后,他将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考古和国学研究,如今神武门郭沫若题写“故宫博物院”的几块石头,背面就是李石曾楷书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中南海怀仁堂等地,也被北平研究院占用。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国立研究院如此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国立研究院如此重要?
刘晓:作为国家机构的研究院代表着一定的官方身份,对内决定国家发展科学的战略、分配学术资源、评判学术水平;对外则代表国家开展学术交流,宣示学术主权。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后,各种专门学会的国际组织纷纷建立,包括国际研究理事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等,我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构,就无法参与其中。
有些资源调查、考古发现,是与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的。所以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科学机构和组织,都有官方背景。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在17世纪成立的巴黎科学院,院士领取薪金,当然也要完成政府的任务。比如巴黎科学院的拉瓦锡既是一名化学家,也是兵工厂的厂长。研究所也由此将科学与应用结合在一起。
但像英法这些科学原发性国家,他们是先有科学家,不少都出身贵族,再从这些科学家中选聘院士和会员,成立科学院和学会。而中国没有现代科学的积累,是先设立研究院,然后从科学知识的生产开始,有一定积累再评价,选举院士。因此我们研究院的模式不是效仿巴黎科学院,而是一种新型的科研体制,即1911年德国威廉皇帝学会开创的研究所体制。
在德国,学术界人才济济,形成了梯队,他们将最精英的科学家集中到研究所,免除教学任务;二流的科学家在大学任教,三流的科学家到企业从事研发。威廉皇帝学会的两个副会长,一个来自银行,一个来自克虏伯公司,代表着资本和工业的支持。而且,威廉皇帝学会设立的研究所,除了按学科而设的基础型研究所外,还有面向工业和军事的研究所。德国社会由此实现了科研、教育和工业的相互促进。德国也得以在物理、化学等领域迅速产生巨大的科学成果。
威廉皇帝学会成立的时候,蔡元培正好在德国留学,这种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很自然成为中央研究院效仿的榜样,如设立研究所、成立评议会,设置院长、总干事等,都是复制而来。不过,二者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社会资本和工业支持有限,研究院也只有基础型的研究所,社会层面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当时是无法企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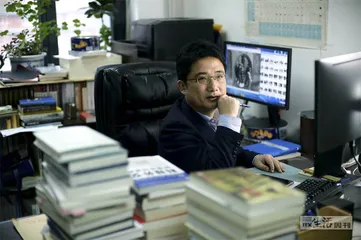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如何分工?
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如何分工?
刘晓:表面上看,虽然两个研究院没有隶属关系,但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央,北平研究院更偏向地方,研究方向上也是前者要紧跟国际,后者更重视应用。但从研究所的设置来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大多类似,比如都有物理、化学、动植物、考古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所。如开展考古调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前往殷墟挖掘,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所就去西安挖掘唐代遗址。实际上二者的区别,仍是不同势力范围以及规模大小的差异。因开创者留学背景不同,中央研究院属于“英美派”的势力范围,北平研究院属于“留法派”的势力范围,他们有各自联络国际学术组织的渠道,而留学法国的人少,所以北平研究院规模较小。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留学回来的学者在研究院与大学之间,会如何做选择?
刘晓:首先这是两方的问题。研究所的所长都是聘任制,研究院、研究所的领导本身就能发挥伯乐的作用。比如中国光学研究奠基人严济慈是中国首位法国国家博士,1931年回国时被李石曾看中,聘为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主任,李经常带他往来于社会名流的宴会,并亲自为他的婚礼证婚。
对于学者而言,进入国立研究院本身就是荣誉。就像威廉皇帝学会邀请爱因斯坦成立研究所,同时给予他普鲁士研究院院士待遇,爱因斯坦欣然接受,因为那就是德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耀,中国学者也如是。更何况那时进入研究院意味着接近学术权力的中心,有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条件,也有评价全国这一学术领域水平的权力。而且研究院的待遇,远非一般高校可比,当时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员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大洋,也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这是当时许多高校都不敢保证的。所以研究院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两院建院后都没有大规模扩张,所以更多的人还是只能到高校。
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也并非与大学隔绝。虽然最初大学区的科教融合理念没有贯彻到底,但实际上研究院仍然与大学联系紧密,比如接受高校的学生来做论文等。而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更类似于一个微型的大学区。中法大学的校长李麟玉,就曾兼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法大学即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那时北平研究院的许多研究员,除非不愿教课,不然也会在中法大学任教。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很多都到大学兼职。
20世纪30年代的这批科学精英,无论是在研究院还是在大学,放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极其特殊的一批人。他们的学术生命一般特别长,学术地位崇高,学科分布较为合理,所以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来说,研究这一百多人是重中之重。那时授予博士学位大多是世界公认的机构,现代科技革命在西方刚刚兴起,科学在高校中得到推崇,国家间高精尖知识的壁垒尚不森严,这些人在西方最前沿的领域获得学位,拥有与最尖端的科学家对话的能力,他们从上世纪30年代回国,在20多岁的时候就任所长、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院也由他们担任所长、研究员,甚至“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还是由他们挑起重振科学的大梁。
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有哪些成果?
刘晓:有了“国字号”的研究院,并在研究院中成立委员会、学会之后,中国能与国外的科研组织进行对等的合作、研究,一定程度上收复了学术主权。这是进入“科学全球化”的重要一步。那时虽然没有院士,但成立了学术评议会,履行对外交往的职能。从此以后,国外学者来中国考察,只能以合作考察团的形式,比如考古挖掘再不会出现像斯坦因那样,把得来的中国文物全部带走的情况。
同时,因为分配留学教育资源的权力在专门委员会手中,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而这些委员与其他国家有密切学术往来,能够获得最新的学术信息,于是可以“定点投放”人才。在这种机制下更能紧跟科学潮流。1932年严济慈在北平研究院创立镭学研究所时,那是中国最早从事原子物理研究的专门机构,当时中子的发现正是国际热点,因与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熟识,居里夫人向他寄来了含镭盐的样品和放射性氯化铅。而严济慈不断派遣练习生到法国或英国学习,培养了钱三强、杨承宗、钱临照等著名科学家。
在研究成果方面,那时国外的理科博士论文都要求是开创性的,一般既要自己设计仪器,又要利用这个仪器做出科学发现。但他们回国后因为经费有限,难以购买高精尖的实验设备,往往最多只能延续一点博士期间的研究。毕竟像居里夫人的成就背后,当时全世界80%的放射源材料都堆在她的实验室里。因而中国在物理、化学等基础性的科学进展有限,独有的地方性科学成果较突出,比如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除此之外,像药物研究所那时已经开始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寻找治疗疟疾、肺结核的药物。
当然,短期成果毕竟有限。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北方局势一直不稳,1934年日本军队抵近在北平郊区,人心惶惶。一方面学生多次举行反日游行,无心学术;另一方面,那时北平只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些与美国相关的学校,仗着美国的势力,敢于扩张、发展,招收硕士,其他学校和研究机构想的大多只是维持现状,不再有更多经费投入。随着局势恶化,高校和研究院或关闭或搬迁。实际上,北平研究院的镭研究所在1934年就已经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1937年,北平研究院整体迁入昆明,中央研究院迁往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地。“遗产”
三联生活周刊:抗日战争后,研究院的研究员做过哪些贡献?
刘晓:发展科学有两条路径,穷则谈理论,达则谈应用。在战乱年代,谈应用已不可能,谈理论也非常艰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研究院西迁,工资朝不保夕,研究员纷纷到高校做老师。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的研究员境遇同病相怜。1938年发现核裂变,世界许多科学家都转向核物理,但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王淦昌,却只能躲到贵州的穷乡僻壤,做一点理论研究,保住火种;更多的人转向生产或教育领域。
比如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后,要承担军需项目: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军用饼干所需的鲜酵母的制造方法,并寻找替代品;物理学研究所承担显微镜和军用水晶片制造工作等。与此同时,许多研究员和教授致力教育,甚至深入地方中学,从而像邓稼先等一批40年代在高校或中学读书的学子,因为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仍能成才。
三联生活周刊:新中国在研究院的建设上,继承了民国时期研究院的哪些传统?
刘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模式,重视研究所和研究院,新中国成立伊始即成立中国科学院,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都接收进来,集中了有限的力量和资源。由于科研条件的优势,科学院对科研工作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许多著名科学家被从高校抽调到科学院,而且吸收了很多归国科学家,以致当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闹矛盾,因为许多院校的专业是“一人系”,一名教授调走,整个系都办不成。
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一样,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郭沫若也是政治地位和学术水平兼备,几位副院长均是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研究院和科学院的设立,奠定了科学在我国社会中的地位。而这种官方背景的研究院和科学院,为中国开展国际科学合作创造条件。比如中苏合作考察黑龙江、中法考察喜马拉雅、中英考察青藏高原,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的。通过合作,也促进了我们制度的完善,如成立学部,遴选学部委员,以便于对外交流。
同时,研究院内部的研究所体系延续下来,这些研究所的设置形成了一个学科完备的系统,所以科学院建院之初就有一个较为齐全的学科体系,一个研究所就意味着一个科研领域,根据科学发展的需求,可以在体系的主干上不断设置新的研究所,淘汰旧所。
学生的培养逻辑也一脉相承。近十年来,中科院和社科院先后成立大学,招收本科学生,研究生在研究所培养,学位则由大学授予,人才培养机制日益规范,促进科教融合。
(感谢张卜天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实习记者明芳菲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学科学革命全球化中央研究院刘晓中法大学中国大学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