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于奇峰险洞之间
作者:辛德勇 明朝末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明朝末年,更是一个奇葩的末世。
明朝末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明朝末年,更是一个奇葩的末世。
在明末这个奇特的年代里,朱家那一代代奇葩的天子,到这时,先后登场的,是跟朝廷大臣耍脾气,以至于长期罢工不上班的神宗万历皇帝;穷淫极欲,以至于上位不到一个月就耗尽元阳撒手人寰的光宗泰昌皇帝;不爱江山爱斧凿,一心想与鲁班比肩争锋做天下第一木工高手的熹宗天启皇帝;最后,是那位刚愎自用以致倾覆大明社稷的亡国昏君思宗崇祯皇帝。
这位崇祯皇帝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自绝于天下之前半个月,讲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万世名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其君刚愎至此,昏聩至此,这国想不亡也真难。
国君昏聩至此,庙堂里那些大臣如何也可想见。党争派斗,由外廷勾连到内宫,从内阁首辅延展到候选备位的草野书生,打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特别是从天启时期开始,东林党与所谓阉党演变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党派的界限俨然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通观整个中国历史,晚明党争之剧烈及影响之深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管你高尚也好,龌龊也罢,正义也好,奸邪也罢,党派的利益,系乎权力,而权力既是媚药,也是毒药。当权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以后,“清流”里也会激起团团浊浪,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很卑污的小人了。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号霞客),就生长在这个昏暗污浊的王朝末世。他读过书,受过很好的教育,当然像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想要获取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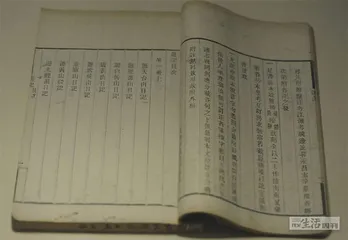 伴随着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选拔官员近乎唯一的途径,在宋仁宗至神宗时期,通过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积极努力,各地州县,始普遍设立官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走向全面普及的重要时期,从此以后,教育的普及程度日甚一日,有条件接受系统教育的青少年也一天比一天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具备相应资格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
伴随着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选拔官员近乎唯一的途径,在宋仁宗至神宗时期,通过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积极努力,各地州县,始普遍设立官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走向全面普及的重要时期,从此以后,教育的普及程度日甚一日,有条件接受系统教育的青少年也一天比一天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具备相应资格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
“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的入口越开越大,可它的出口,也就是官场里设定的位置,却所增无多。这样,朝廷也就没必要择取那么多人做进士,很多年轻的士子便怎么考也考不上。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民间信仰中所谓“梓潼神”,由一尊战神,陡然转身变脸,成了“文昌帝君”这样的文运之神。其间缘由,就是因为考场如战场,考中与否犹如战役的胜负,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应考者既需要才华与学养,也还要有很多运气的成分。
这就是徐弘祖走入场屋时面临的严峻局面。遗憾的是,他运气不佳,没有能够挤进入仕的行列。现在颇有一些对徐弘祖的评议,说他不屑于科举功名而甘愿到大自然中去探索科学的真理,这实在是不了解古代社会想当然的拔高话,虽然在市面上很通行,却当不得真。利害关系在那儿明摆着,圣人才能绕得过去。
被摒绝于仕途之外的徐弘祖,为自己安排的人生之路,便是寻山问水,游历各地名山大川,特别是那些奇峰险洞,而明末以来直至民国时期以前,前人对徐弘祖其人其事的评价,大略不过奇人奇行、奇事奇记而已——别人没跑这么多地方并把自己的行迹一一记录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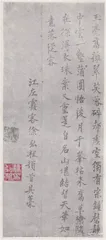 这部《徐霞客游记》,便是徐弘祖的旅行记录。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说古人品题山川名胜而能“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当首推此书;或谓之曰“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这部书的独特之处,仅在于篇幅宏大,前所未有,而不是在内容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这部《徐霞客游记》,便是徐弘祖的旅行记录。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说古人品题山川名胜而能“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当首推此书;或谓之曰“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这部书的独特之处,仅在于篇幅宏大,前所未有,而不是在内容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至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丁文江等人,相较于西方近代科学,高度赞誉《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特别是游记中对西南喀斯特地貌的观察和记录,说这些内容甚至完全可以同西方近代地理学家的著述相媲美,称颂徐氏乃“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并且总结说,徐弘祖有包括发现长江源在内的五大地理发现。
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特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但由于事关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一些基本问题,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就需要再斟酌。
丁文江等人所说徐弘祖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发现长江源在内的五大地理发现;二是对喀斯特地貌的科学观察与记录。
关于前一方面,谭其骧先生早已举述切实的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特别是明人对长江源的正确认识,即以今金沙江为长江之源而不是《禹贡》记载的岷江,不仅早在徐弘祖出生之前就有名章潢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章潢还明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河源判别原则——一级原则是“以远为源”,二级原则是在两条上源长短相近的情况下“以大为源”(即以水流量较大者为正源)。
关于后一方面,一者西方近代地理学同西方所有学科一样,它们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因而不宜用中国古代文献中某些孤立、零散的记载简单地同西方近代科学的内容相比,把个别现象上的相似性视作系统的学科等同性。对徐弘祖的旅行记录也是这样。
二者就其实质性特征而言,类似的山水游记,至迟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已开其端。稍后,复有韦宗卿在唐敬宗宝历元年撰著《隐山六峒记》,描摹桂林附近的6个石灰岩溶洞(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九、清官修《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而且其文字描摹之细腻详明,绝不在800年后的徐弘祖之下。再后来,像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更对岭南石灰岩地貌有较大篇幅的集中记述。更具体的例证,如明嘉靖时人郎瑛所撰《七修类稿》,其中述及云南临安府的石灰岩溶洞“颜洞”,就比后来徐弘祖的游记要更为详明(《七修类稿》卷一《天地类》下“生平奇见”条)。
这样看来,徐弘祖在这一方面也并无开辟之功,有的只是四库馆臣所说“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而已,也就是成规模、上批量。可谁都明白,这只是简单重复,算不上创见性学术贡献。
若是转换一个角度,通观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后期的地理学确实出现了一个重大发展,但这发展并不是以徐弘祖著述为代表的山川游历,而是区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复有《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承续其后,而在唐代初年以后,斯学沉寂日久,大有归于泯灭之势。孰知延至明代后期,风气竟又丕变,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区域地理学著述,诸如王士性的《广志绎》、张瀚的《松窗梦语》、陈全之的《蓬窗日录》等,都是其代表性佳作。《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是远不足以与这些区域地理学著述相并比的。
此外,品题山川名胜,至迟从南宋时期起,就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南宋时人祝穆撰著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作为各地“胜览”的重要项目,其中就包含“形胜”和“题咏”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是同品题山川名胜具有深重内在联系的。
至明朝嘉靖末年,有何镗编印《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显示出对名山的游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时尚。从此以后,延至明末,又出现了一大批汇纂名山游记的出版物,如慎蒙在何镗《古今游名山记》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十六卷和不著撰者的《名山记》四十八卷等。在这些名山游记当中,就包含很多明朝时人的著作,如《名山记》“所录古人游记十之三,明人游记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八《地理类存目》)。作为个人著述,名山游记更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十二卷、王世懋的《名山游记》一卷等。
 明末大批量刊印的这些名山游记,活灵活现地向我们展现了人们空前喜好游览名山胜迹的情况。徐弘祖的游历和游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明末大批量刊印的这些名山游记,活灵活现地向我们展现了人们空前喜好游览名山胜迹的情况。徐弘祖的游历和游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徐弘祖其人本来是一条热血汉子。他关心国事,胸怀正义。1640年(崇祯十三年),清流领袖人物黄道周遭阉党罗织罪名,被逮下诏狱。病中的徐弘祖闻讯,当即遣长子前往北京探视。其子“三月而返,具述石斋(黄道周号)颂(讼)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一《徐霞客传》)。此举此情,诚可谓侠肝义胆。
然而明末的社会,就是那么黑暗,黑暗得令人窒息,而徐弘祖又身无功名,仅仅是一介布衣。要想让自己的灵魂不被窒息而死,恐怕只有逃离。我们若是不带任何预设成见地通篇审视一下《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应该很容易看出,徐弘祖奔走各地的游踪,是可以用“纵情于奇峰险洞之间”这样的话来概括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之情和尘世之欲都倾注到这些奇峰险洞之中了。
(关联阅读:谭其骧《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学上之重要发现》,见作者著《长水集》;辛德勇《徐霞客史事二题》,见作者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辛德勇《章潢之地理学贡献》,见作者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 历史中国古代史地理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明朝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