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法国”
作者:维舟 前些年,一项民调显示,法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本国历史人物是戴高乐,因为正是他在危难中拯救了法国,并且还是两次:一次是1940年夏天,在面临战败沦陷的困境之下,在所有人陷入迷茫之际,是他发出了“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的顽强声音;第二次则是在1958年,又是他解决了战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和派系纷争陷入僵局的死结,彻底改造了法国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当代法国国父,并不为过。
前些年,一项民调显示,法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本国历史人物是戴高乐,因为正是他在危难中拯救了法国,并且还是两次:一次是1940年夏天,在面临战败沦陷的困境之下,在所有人陷入迷茫之际,是他发出了“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的顽强声音;第二次则是在1958年,又是他解决了战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和派系纷争陷入僵局的死结,彻底改造了法国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当代法国国父,并不为过。
在一个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公众能对某个人物取得最大共识,这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形象超越了各派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戴高乐本人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强调超党派立场,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刻意保持某种“战略模糊”,他的追随者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甚至直到今天,左右两边仍各自打着他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这一点他本人也心知肚明,早就说过:“每个人或现在、或过去、或将来都是个‘戴高乐主义者’。”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乃是矛盾的综合体,集各种元素于一身,既能被不同人认可,又能被从各种视角加以解读利用。也因此,他曾被称作一个“当代斯芬克斯”,一个谜一般的政治人物。正如本书所言,戴高乐一生都是“一个残酷而分裂的人”,“他既是法国现代史当中最受尊敬的人物,同时也是最被憎恨的人物。他受到的辱骂与赞美、憎恶与崇拜,几乎是同等的。20世纪的其他法国政治人物也被憎恨过,但从未达到戴高乐那样的程度”。
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世多么富有争议,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整个国家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彼此针锋相对时,没有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因为戴高乐竭力超越其上,试图尽可能地弥合这种分歧,他才在受到不同派系拥戴的同时,也更遭到他们的攻击、憎恨——原因很简单,他看起来既像是代表着所有群体,又好像没有代表任何特定群体,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自己人”。
戴高乐曾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何才能统治好拥有258种奶酪的国家?”这句俏皮话隐含着深意: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就是一个深陷在多元分歧中的国家。这在好的时候带来极大的丰富性,但在坏的时候则让全国陷入撕裂、对立和剧烈的来回摆荡中,以至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一次复辟的王朝政权,像“德雷福斯事件”引发的社会争议,余波在数十年里都未能平息。可以说,1940年法国的战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架构本身的缺陷所致:它已经陷在“多元停滞”的困局中太久,无法有效行动起来应对一触即发的危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戴高乐的答案是“法国”——所有人都应该为了法国,放下分歧,共同应对一个动荡世界的外部挑战。也正因此,他一贯不在意追随者的政治观点,只要他们愿意服务于国家利益,都能为我所用;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也一样:面对世仇德国,他眼里看到的也不是其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德国,这使他在战后能迅速化解仇恨,打造了日后成为欧盟基石的“法德轴心”,也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在西方阵营中独持异议,既和苏联保持接触,还率先和新中国建交。其他人是透过意识形态的眼镜看待世界,而他却是透过地理的镜片,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是法国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
问题在于,这种强调国家认同的视角,在左翼看来,本身就是偏右翼色彩的。这一点也确实不可否认。戴高乐本人出身于一个保皇主义氛围浓厚的家族,在军中又接受了“荣誉和祖国”这一格言,从年轻时起,他就痛心于法国社会的对立和撕裂,认为要重现法兰西的辉煌,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来解决当下的分歧。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夏尔·贝玑就追求所有法国传统的综合,强调“整个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换言之,这一思路推崇的不是分化的特殊利益诉求,而是积累、复合和整体性。对戴高乐来说,从这无所不包的大海中升腾起来的名字就是“法国”。
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1940年的战败和1958年的困局虽然是国家的不幸,但对戴高乐本人而言却是极好的机会。这使党派纷争的政治精英们声誉扫地,进而召唤一个像他这样能凝聚共识的人物。他也确实一再倡导某种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出现的“神圣联合”,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拯救法国这个更崇高的事业面前,同意搁置当下的政治分歧,从分裂走向团结。与此同时,他自己则扮演了一个凌驾于派系斗争之上的角色,如果说路易十四的格言是“朕即国家”,那戴高乐未明言的座右铭其实是“我就是法国”。也难怪他在晚年坦率地承认:“我一生的憾事是未能建立君主制,因为没有君主制所需要的王室成员。事实上,我当了10年的君主。”
的确,不管怎样,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调和了君主制传统和大革命成果之间的矛盾,并以坚定的意志推动国家向前,使戴高乐主义成功地成为法国政治传统的综合体,用他自己的话说,让左派考虑国家,让右派考虑国民。这有点像是法国式的“通三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法国”的定义,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民别无选择的身份来源,而成了一个各派力量在其中进行复杂博弈的多元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愿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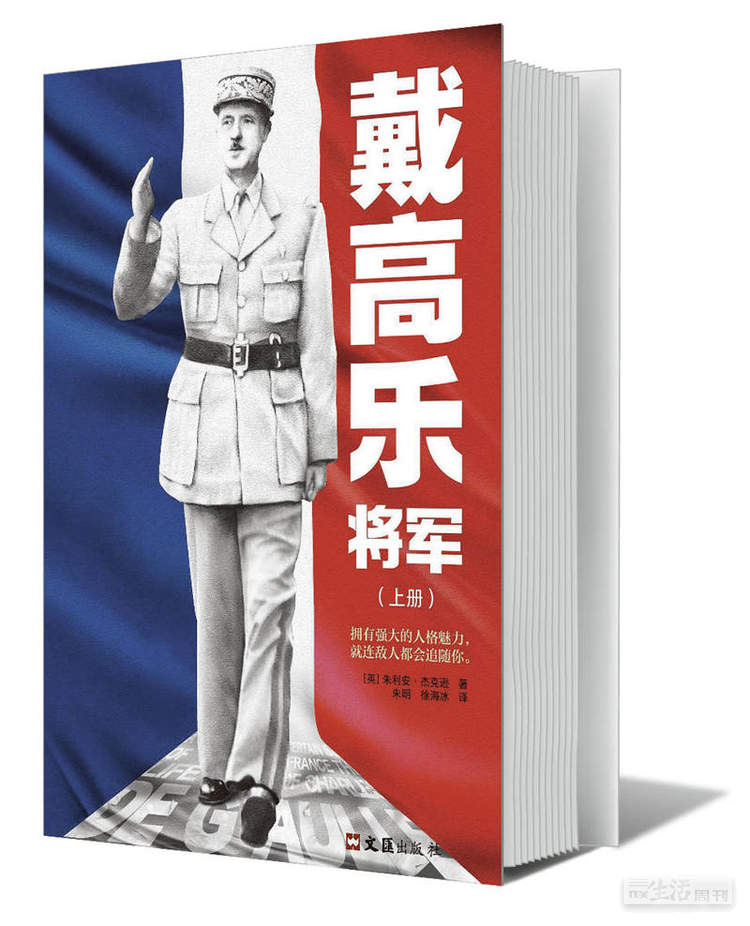 朱利安·杰克逊的书
《戴高乐将军》
朱利安·杰克逊的书
《戴高乐将军》
对戴高乐来说,真正的挑战正如本书所言,“一旦危机结束,这位天佑的救世主就会变得多余”,而他的办法则是不断警告危机从未远去。如果对比另一位政治家的命运就可以看出差异:拯救了英国的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就被选下台了,因为英国人认为,战争即将结束,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他这样的人物了。丘吉尔当时苦笑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就此而言,虽然戴高乐困扰于法国当时的政治纷争和危机,以至于他两度临危受命,但也正是这造就了他。
在他身后,再没有人能具备像他这样的威望凌驾于各派系之上,也没有那么深重的危机能召唤出这样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法国的幸运,当然也是戴高乐的幸运——无人能再成为戴高乐,他也因此成了不朽的传奇,他是现代法兰西最后的“道成肉身”。 戴高乐政治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