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所心血管病医院的八个半小时紧急转移
作者:杨璐 “整个下午我都在手术室里,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不知道。手术做到晚上6点多,我回到办公室喝口水,顺便看了一下手机才知道外面雨下得很大。”年近60岁的范太兵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先天性心脏病专家、卫生部先心病专家组成员,时常有全国各地的患儿被父母带到位于郑州的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救治。7月20日,他像往常一样忙碌,上午在门诊看了40多个病人,中午把病人都安排好,他赶去手术室,下午安排了两台大手术。
“整个下午我都在手术室里,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不知道。手术做到晚上6点多,我回到办公室喝口水,顺便看了一下手机才知道外面雨下得很大。”年近60岁的范太兵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先天性心脏病专家、卫生部先心病专家组成员,时常有全国各地的患儿被父母带到位于郑州的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救治。7月20日,他像往常一样忙碌,上午在门诊看了40多个病人,中午把病人都安排好,他赶去手术室,下午安排了两台大手术。
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国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它是河南省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医研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性医院。国家卫健委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和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也落户在这家医院里。它在2017年底正式开诊,院址在郑东新区白沙园区里,就像很多城市的新开发园区一样,远离市中心。
雨在傍晚6点多开始越下越大,天已经黑了下来,它不但阻滞了来探病的家属离开,也阻滞了医生和护士们下班。放射科主任葛英辉告诉本刊:“我们医生和护士很多来自于郑州市区里的省人民医院,家也都在市区里,当时天气特别恶劣,医院的领导同事们都说,大家晚上都住在医院里吧。所以,我们科室20多个职工都没有走。”
范太兵也没有按时下班,像他这样全国知名的专家,日复一日工作繁重,他从办公室又去病房,在病房里他看到工作群说地下二层的车库进水了,大家都去抢险。“我就赶紧加入了。”范太兵说。
范太兵很清楚地下车库进水对医院的严重性,他告诉本刊:“我们医院里的两个餐厅、供电设备、很多大型医疗器材都在地下车库、地下一层和一层楼,那是很重要的区域。地下车库有4个出口,院领导就带领大家分组,守在不同的口上。最开始我们是堆沙袋,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附近贾鲁河上可能水量比较大的情况,车库里水涨得很快,沙袋用完了。我们又去找大塑料袋,想往里面装满土来堵水,医院里塑料垃圾袋很多,可是医院里平时都是干干净净的,土不多。后来我们又抱被子来堵,还有同事把自己的车开过来堵,希望沙袋不要被水冲开。”
 20日晚上10点多,医院里抗洪抢险的压力越来越大。跟外面院子相比,医院的地势其实很高的,但很快水就漫到了一楼大厅,然后进到了放射科工作区,葛英辉和科室同事就成了医院里抗洪的前线。“我们科室都是拿着枕头、被子、毛巾、地毯,反正能用的都用上了。后来,我们还想了一个招儿,把废胶片贴在门缝上,然后用桌子抵住。科室内,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垫高,能放到桌子上的设备,我们就放到桌子上。一直忙到凌晨1点多,能堵的都堵上了,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时候,一楼大厅的水已经没到脚脖子了。”葛英辉说。
20日晚上10点多,医院里抗洪抢险的压力越来越大。跟外面院子相比,医院的地势其实很高的,但很快水就漫到了一楼大厅,然后进到了放射科工作区,葛英辉和科室同事就成了医院里抗洪的前线。“我们科室都是拿着枕头、被子、毛巾、地毯,反正能用的都用上了。后来,我们还想了一个招儿,把废胶片贴在门缝上,然后用桌子抵住。科室内,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垫高,能放到桌子上的设备,我们就放到桌子上。一直忙到凌晨1点多,能堵的都堵上了,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时候,一楼大厅的水已经没到脚脖子了。”葛英辉说。
在地下车库里堵水的范太兵,意识到水可能堵不住了,要保证病人们的安全。“我不知道水会涨成什么样,涨多长时间,所以赶快回到办公室做预案。”范太兵惦记着自己科室病房里的22个孩子,“平时值班是一个医生带一个进修医生和护士们一起,那天晚上,我要求医生护士要配够,在单位的4个医生、2个进修医生都要回到岗位上,病房里一个护士看一个孩子。”范太兵是儿童心脏病专家,深知病房里的孩子很脆弱,他说:“有一些孩子是戴着呼吸机的,我非常担心会断电,就让护士长带人把所有设备都充上电,一旦断电了,还可以坚持4到6个小时。”范太兵1998年博士毕业,逐渐带团队把心脏外科做了起来,经验丰富。他觉得充电器也不够保险,又跟医院要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医院里有国家的供电系统,电网停电了,我们地下室还有发电机。这两重保障都不行了的话,还有4台小型的发电机备用。”范太兵说。
但是随着水位上涨,医院的高压电泡了水,为了安全医院拉下了电闸,所有人陷入了黑暗。
7月21日凌晨3点钟左右,水灌满了医院的地下二层、地下一层,一楼也淹了一半,全部医护人员都撤到了二楼以上。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门诊楼、住院楼,几千名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陷入黑暗之中。葛英辉说:“我只能听到雨声、水声,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也看不见,手机信号也没有。从那时候开始,医院就处于一个对外隔绝的状态。”
紧张和压力才刚刚开始。凌晨4点钟,葛英辉回到一楼看情况,“水已经灌到楼梯的第六层台阶,马上要漫到第七层了。地下一层、二层灌水的声音非常大,很沉闷就像打雷一样,听着非常恐怖。可能是因为地下两层的水灌满了,一楼地板像有泉眼一样往上冒泡,踩下去明显感到地板往上冲的水流。我当时觉得地板要塌了。”葛英辉说。她顾不上恐惧,组织科室同事去抢救设备,因为水还在涨。“我们把非常贵重的设备往楼上运。7点钟,水已经到了大腿。10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女孩就不敢下水了,男孩跳下去水也到了胸部。”
范太兵也要面对复杂的局面,一要保障电力,二要照顾好患者饮食起居。“我们科室里有一些矿泉水,我给每个家庭分了一瓶。孩子们要冲奶粉需要热水,当时整栋楼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烧热水,我们去弄一些热水来。大人不吃没问题,先把孩子安排好。”范太兵说。
此时,医生和护士们都意识到了医院已经成了孤岛,他们彻底被洪水围困了。有医生到楼顶上去看到,平时狭窄的贾鲁河已经变成了一个圆形,水早已漫过五六米高的河堤,形成一条地上悬河。
 虽然救命的医疗设备都有备用电池,医院里还有小型发电机备用,依旧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护理部是全医院护士们的“司令部”,电闸一拉下,进入到了“战时状态”。副主任于漫告诉本刊说:“呼吸机、ECMO等设备和仪器的功率特别大,小发电机带动起来很困难,柴油消耗得也快。非常时期,就考验我们医院的专业能力。”
虽然救命的医疗设备都有备用电池,医院里还有小型发电机备用,依旧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护理部是全医院护士们的“司令部”,电闸一拉下,进入到了“战时状态”。副主任于漫告诉本刊说:“呼吸机、ECMO等设备和仪器的功率特别大,小发电机带动起来很困难,柴油消耗得也快。非常时期,就考验我们医院的专业能力。”
医院的自救,迅速把资源给了危重病人。于漫说,医生们认真评估病情,判断出哪些病人是最紧急、最需要这些仪器的,最终确定当时医院一共是有69名危重病人。“我们把全院所有的仪器,电力都集中来保证这些病人的安全。”
从断电开始,护士们忙碌起来。“当时有备电的科室只有手术室,所以我们要把机器推来推去,楼上楼下抱着充电。哪里暂时有空余的充电位,把需要充电的机器推过去,哪个机器刚刚充好电,赶紧推去最需要的病人身边。楼里没有信号,内线电话也打不通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工作衔接全靠楼上楼下互相跑着说话,或者喊。每个人都特别紧急,消耗特别大,只能给自己‘打鸡血’、硬撑着,同事们跑来跑去遇到,经常第一句话就是互相问:‘什么时候有电?’”于漫说。
除了保证电力让医疗设备正常运转,危重病人意味着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治疗和监护也是不能停的。没有电,只能依靠应急灯、手电筒和护士们的手机照明继续工作。“性命攸关的时候,我们得加倍精心。昏黄的灯光下,药瓶上的字又特别小,我反复叮嘱护士们核对一定要比平时更严格、更认真。我们一直在进行治疗。病人血压低了,我们要用升压药。血压高了,我们要用降压药。病人如果出血了,我们还要给他输血。监护室里的病人经常会出现一些躁动,我们要给他用镇静药。上呼吸机的病人,我们要给他吸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要保证病人的安全,还要保证病人的治疗,真是竭尽所能了。”于漫说。
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意识到电力和其他设施的损毁严重,短期里不适宜开诊,病人们必须转移回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但医生们同时需要确定,不同的危重病人,适合以什么样的方式迅速转移出去。
范太兵说:“撤离是从陆路和飞机两种渠道转出。我们做了方案,迅速对所有病人进行判断,轻症和一般病情,他们坐冲锋舟离开,然后再坐车到省人民医院。轻症跟家属联系上之后,就可以出院了,其他病人在省人民医院继续治疗。重症的病人戴着呼吸机等设备,乘坐冲锋舟再转车太危险,就用直升机撤离。”
全院最后评估出36位需要通过直升机转运的病人。
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康洪超院长负责空中救援的总指挥,护理部杨巧芳主任和于漫负责重症患者的转运。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专业化、精细和体力的工作。于漫说:“这些病人有的是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有的是刚做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孩子,还有肺心病、多发性骨折、心源性休克等病人。我们的原则是先转移佩戴的生命支持仪器多的病人,因为耗电量太大。他们多待在这里一分钟,就会多一分钟危险,我们心急如焚地想给他们早争得一分钟安全救治的机会。”
于漫和同事们把工作做得很细致,确立了这个原则,他们分头去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把转移的顺序跟家属们解释清楚。于漫说:“危重病人谁家都想先走,如果不事先做好工作,转一个出来其他家属会问为什么不是我家,可能造成不可控的场面。我们去做工作,一开始大家也是非常紧张的,有人情绪激动,但令人感动的是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达成一致。”
 7月21日下午2点多,转运正式开始,因为5点多还要下雨,转运就要中止,时间很紧迫。于漫说:“危重病人在三楼和四楼,停机坪在五楼的楼顶。停电了电梯不能用,我们又要抬病人,又要抬仪器,仪器都是相当沉的,还要有人看着心电监护,还需要输氧,还有病人是带着输液泵的。这一套下来,我们需要十几个人事先安排好站位,转移一个病人。楼道里没有灯,我们拿着应急灯、手机里仅存的电照着路,抬不动的时候也不能换手,因为要保持病人和设备的稳定,我们要迅速把病人给抬上去。我们一点儿也不敢松劲儿,一路上互相鼓劲加油,马上要上去了,大家再坚持一层,就这样鼓着劲儿一层层送人上去。”
7月21日下午2点多,转运正式开始,因为5点多还要下雨,转运就要中止,时间很紧迫。于漫说:“危重病人在三楼和四楼,停机坪在五楼的楼顶。停电了电梯不能用,我们又要抬病人,又要抬仪器,仪器都是相当沉的,还要有人看着心电监护,还需要输氧,还有病人是带着输液泵的。这一套下来,我们需要十几个人事先安排好站位,转移一个病人。楼道里没有灯,我们拿着应急灯、手机里仅存的电照着路,抬不动的时候也不能换手,因为要保持病人和设备的稳定,我们要迅速把病人给抬上去。我们一点儿也不敢松劲儿,一路上互相鼓劲加油,马上要上去了,大家再坚持一层,就这样鼓着劲儿一层层送人上去。”
这个工作听起来简单,其实非常需要专业性和规范动作,因为病人身上连接的仪器和管子太多,人还得足够少又配合默契,否则会手忙脚乱,外人都插不上手。于漫说:“我们部门有的腰扭住了,有的骨折了,我是大拇指脚趾头已经不能打弯了。但是当时精神高度集中,只想把事情干好,我们没吃东西不觉得饿,也一点儿都没顾得上疼,那个骨折的同事也是过了几天,感觉疼痛,去看才发现是骨折。”那一天转出了5个病人。“我们其实已经非常高兴了,因为那天天气不好,飞机还出现了故障。有了第一天的经验,我们回来继续磨合和规划,让第二天的效率更高。”
7月22日,上午11点开始,转运继续进行,护士们一方面保证要高效率,一方面要保证危重病人的安全,流程衔接就特别重要,没有电梯和通信系统,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组成一个呼叫链。于漫说:“每个部位都站了人等候,比如说,一个人站在停机坪上喊,飞机来了可以转上病人了,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喊下去,一直喊到监护室门口。监护室里等待的同事们就把病人抬出来,因为如果抬出来早了,外面环境不稳定容易出危险,我们尽量让病人在转运途中的时间少一些,在我们监护下的时间多一些。飞机上的路程其实只有5分钟,但有我们医生和护士的陪同,到了省人民医院,那边也有专人来接待和照护。”
7月22日晚上7点半,最后一个危重病人通过空运转出,当天一共转移了31位病人。于漫说:“最后负责转运病人的同事们都腿软趴在地上了,我负责协调病人、规划流程和顺序,嗓子喊哑了。”
而历时8个半小时,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终于把36位危重病人,通过空中通道全部顺利转走了。
 7月21日凌晨,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一断电,基本上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在楼顶上或者窗户边,偶尔才能有手机信号。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求救信息比较晚才在媒体上受到关注。30岁的袁海见是最早跟这家医院联系并展开救援的人之一。他是郑州妙炒居士快餐店的老板,给郑州几大医院都送过餐,对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周围环境和医院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袁海见的救援送餐经过,就是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被水围困得多么严重的映照。
7月21日凌晨,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一断电,基本上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在楼顶上或者窗户边,偶尔才能有手机信号。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求救信息比较晚才在媒体上受到关注。30岁的袁海见是最早跟这家医院联系并展开救援的人之一。他是郑州妙炒居士快餐店的老板,给郑州几大医院都送过餐,对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周围环境和医院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袁海见的救援送餐经过,就是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被水围困得多么严重的映照。
实际上7月20日中午,袁海见还给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送过一次餐,当时一切都很正常。雨是下午3点钟开始越来越大的,他距离另外一所损失惨重的医院郑大一附院很近的一家店铺开始进水,到晚上8点多的时候,店铺里的冰柜、吧台都漂了起来。
21日早上10点半,袁海见从朋友圈看到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消息,他告诉本刊说:“那边刚建成大概3年时间,地方特别偏,周围没有商场、没有超市,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说这家医院被水围困了,立刻知道灾情会很严重。”医院里面的人求救说,已经15个小时没有吃上东西了。袁海见决定免费为困在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病患送去爱心餐和饮用水。他第一批做了360份爱心餐,本来店铺距离医院只有20分钟车程,没想到最终却走了4个多小时,因为隧道、下凹式桥都灌满了水,变成一个个几米深的水沟,阻断了交通。
沿路都是被冲得七零八落的车,袁海见尝试了几条熟悉的道路,都因为水太深被堵死。“走到金水东路的时候,我一想到那么多人等着这口饭呢,终于一咬牙开车冲进了水里。我感觉油门踩了好久,水就迎着面包车的前脸冲击过来,后来终于成功了。车开到明理路时,我看见马路上竟然有船,还有蓝天救援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救援队和冲锋舟。这条路再往前走,连救援队都过不去了,因为东四环金水东路的积水已经跟桥没平了,大概有3米深,根本无法通过。”袁海见说。
袁海见和同事们分别开着车在马路上兜兜转转,试图找能到达医院的路。他们搭乘过消防车,水深的地方消防车也过不去。他们跟医院里负责划着皮划艇接发电机柴油的主任联系上,可他们被困在路上,手机没信号联系不到接应的人。最近的一次,他们抵达过距离医院不到3公里的位置,“我都能看到医院那栋楼就在眼前了,就是过不去,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救命的饭呀,医院里的东西被冲毁了,病人是特别容易暴躁的,他们很多还是心脏不好的病人,医护人员很难安抚住。如果吃得上热饭,还能控制一下情绪。”

 7月21日晚上7点15分,袁海见和同事们遇到了去医院救援的火箭军。“我们跟火箭军是同时到的,他们有冲锋舟,所以,我就把快餐、饮用水、卫生纸和水杯等物资交付出去。”袁海见说。然后,他返回店铺去做下一批快餐。“需要快餐的量太大了,我们备菜的品种不太够,所以这一批我们只能做盖浇饭。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考虑餐的丰富性了,只要能吃到热饭就行。”袁海见说。这一次,他没从市内穿过,而是上高速路绕了一个大圈,同行的还有带着船的曙光救援队。“路上的水依然很深,我们慢慢前行,越过很多积水区,终于在晚上11点多到达了距离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最近的科技馆附近。”
7月21日晚上7点15分,袁海见和同事们遇到了去医院救援的火箭军。“我们跟火箭军是同时到的,他们有冲锋舟,所以,我就把快餐、饮用水、卫生纸和水杯等物资交付出去。”袁海见说。然后,他返回店铺去做下一批快餐。“需要快餐的量太大了,我们备菜的品种不太够,所以这一批我们只能做盖浇饭。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考虑餐的丰富性了,只要能吃到热饭就行。”袁海见说。这一次,他没从市内穿过,而是上高速路绕了一个大圈,同行的还有带着船的曙光救援队。“路上的水依然很深,我们慢慢前行,越过很多积水区,终于在晚上11点多到达了距离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最近的科技馆附近。”
袁海见和救援队由车换船继续往前走,“我们开了大概有20分钟,不敢开太快。路面我是熟悉的,但不熟悉现在水底的情况。第二天我重走了那条路,想想就流冷汗。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表面看是一片汪洋,啥都没有,第二天好多车顶都露了出来,如果我们稍微走偏一点,船的动力螺旋桨打到车顶,船就翻了。幸亏我熟悉路况,一直喊他们靠中间走,不要靠两边。”袁海见说。
7月22日凌晨零点13分,船驶近了门诊楼的大门。“我差一点哭出来,被困前我还来医院送餐,一切正常。短短两天,医院外面一片黑暗,非常寂静,用手机照亮一看,有一种大灾过后,杂乱无章的感觉。”袁海见说。
袁海见路上遇到的火箭军,是第一批赶来救援的解放军救援力量。7月21日晚上9点开始,中部战区防汛抢险前进指挥所调集第83集团军多支部队、火箭军某部、武警河南总队、民兵预备役官兵,携带救援装备解救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里被困的患者、医护人员和家属。这是一场涉及5000多人的大转移,除了于漫和同事们的空中转运通道,其他人要通过冲锋舟运到路面,再通过大巴车或者救护车分别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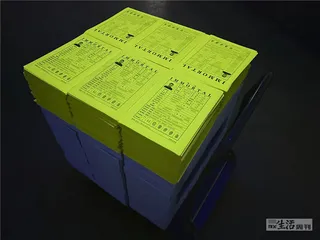 7月22日下午1点左右,第一批转移的患者到达了河南省人民医院,可同时,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里还有大量等待的病患需要供电。支援的发电机是随着医院求救信息的发出同步准备的。陈炳成是山东潍坊一家发电机企业的负责人,7月21日,1688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说郑州水灾的医院需要大功率的发电机。大功率发电机不算容易找,因为它的货值比较高,一般工厂不备货,都是下订单再生产。陈炳成厂里有3台400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现货。
7月22日下午1点左右,第一批转移的患者到达了河南省人民医院,可同时,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里还有大量等待的病患需要供电。支援的发电机是随着医院求救信息的发出同步准备的。陈炳成是山东潍坊一家发电机企业的负责人,7月21日,1688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说郑州水灾的医院需要大功率的发电机。大功率发电机不算容易找,因为它的货值比较高,一般工厂不备货,都是下订单再生产。陈炳成厂里有3台400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现货。
医院、1688平台和陈炳成拉了一个工作群,根据医院设备处和强电部门的测算,如果能运来一台400千瓦的发电机能够满足一栋大楼的基础照明和部分普通设备的运行,如果能运来600千瓦的发电机,还能满足到生物样本库的供电。医院的生物样本库有很多超低温冰箱,对发电机功率要求很高。陈炳成说:“400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是庞然大物,一辆5.2米长的大卡车只能拉一台机器。我把车都找好了,只要医院确认,立刻就能发车,大概需要8个小时运到郑州。”
7月21日晚上10点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医院周边5公里都是一片汪洋,进出只能用冲锋舟,冲锋舟最大的承载量不能超过三四百公斤,大型发电机运不进去。陈炳成又给医院准备了几台10千瓦的小型发电机,小发电机大约200公斤左右,刚好能用冲锋舟运输,它们用来给核心制氧设备、ICU紧急救护设备供电。在微信群里,有人希望能连夜出发,“这是救人啊,一个晚上的时间耽误不起啊!”
发电机的交接却要复杂一些,陈炳成说:“发电机的配件都要配好,每一台机器加上润滑油,调试好。医院那边要准备好安装场地、作业条件以及线缆、柴油,可能的安全审批等等。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和医院连夜分头行动。22日早上出发,下午运到医院。路上的这些时间,还需要医院里再坚持一下。”
最初方案里那些大功率发电机,水抽干之后医院还用得上。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是双回路供电系统,日常依靠国家供电系统供电,如果发生停电,医院里配有大功率发电机。陈炳成解释说:“这种发电机大概率是安装在地下室里。因为它牵扯到一个噪音运行问题,医院里配备的发电设备可能要有十多吨重,如果放在楼顶上,它运转起来可能整栋楼要跟着晃。发动机安装在地下室里,现在一灌水基本上就报废了。”除了发电机的损失,更严峻的是医院的高低压配电系统也在水泡之后瘫痪了。陈炳成说:“它是集成了几十个、上百个配电柜,每一个配电柜可能管着一层楼几十个房间。这种系统一般都是根据工程定制的,因为每个地方的构造不一样,国内好像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项目,所以,市面上买不到现成的匹配这个医院的高低压配电系统,定做配电柜可能都需要两三个月时间。这绝对不是一件电力公司合上闸,一个小时就能来电的事情,这是一场巨大的天灾。”
受损失的还有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它们很多都是被安置在一楼。放射科主任葛英辉非常伤心,20日进水那天,她和同事们忙了整晚,拼尽全力跟上涨的雨水抢救设备。最开始是放在桌子上,一步步往高处搁放,可人力和时间有限,能搬运出来的器材并不多,大型医疗设备的损失非常大。最先进水的地下二层车库里,还有医护人员、家属的1000多辆车,全都泡在了水底。 袁海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