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物理学家的杨振宁
作者:苗千 在辉煌的17年之后,当他最终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已经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物理学家,成长为一位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大师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很多年轻人像他当年崇拜爱因斯坦、费米和狄拉克一样,对杨振宁投以崇拜的目光,希望跟随他学习,理解他在物理学上成功的秘密。从普林斯顿到纽约
在辉煌的17年之后,当他最终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已经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物理学家,成长为一位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大师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很多年轻人像他当年崇拜爱因斯坦、费米和狄拉克一样,对杨振宁投以崇拜的目光,希望跟随他学习,理解他在物理学上成功的秘密。从普林斯顿到纽约
或许杨振宁最初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普林斯顿逗留如此之久。在194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一年左右,作为费米(Enrico Fermi)的助手进行研究工作。到了1949年春天,杨振宁申请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博士后职位,很快就被录取。或许他认为自己在不久之后还会回到芝加哥——毕竟自己的博士导师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费米已经为他在一年之后的归来做好了安排,但最终,杨振宁还是在普林斯顿度过了17年时间。
促使杨振宁最终离开普林斯顿的原因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生活在这个以纯理论研究闻名的象牙塔里确实已经太久,如果继续生活下去,他或许只能选择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1965年春天,曾经将杨振宁和李政道坐在普林斯顿草地上讨论问题的样子描述为一道靓丽风景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告诉杨振宁,他准备从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并且准备推荐杨振宁成为下任院长,他希望杨振宁能够对此认真考虑。杨振宁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随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一封信里写道,自己不确定是否能成为一个好院长,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自己一定不会喜欢院长的工作。
拒绝了院长的职位,或许让杨振宁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另一个原因则来自外界。1964到1965年,纽约州决定在纽约州立大学设立5个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职位(Einstein Professorship)。当时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约翰·托尔(John Toll)和物理系主任庞德(T.Alexander Pond)都真诚地邀请杨振宁前往刚刚建校不久,风景优美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担任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并且承担起在大学里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职责。经过考虑之后,杨振宁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在1966年启程前往纽约。25年之后,托尔在一封信中写道,他认为杨振宁做出这个决定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时刻。
对于这个重大的决定,后来杨振宁回忆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个有名的、非常成功的象牙之塔,所以我离开时,很多人问过我:你离开环境那么好的象牙之塔,而你又在那里做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研究工作,你离开以后是不是后悔?我也问过自己,回答是:不后悔。因为象牙之塔虽然是重要的,可是象牙之塔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创建一所大学是对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一个人能在这样的事业里做一些工作,他自己也可以觉得满足。我有17年的工夫在最好的象牙之塔中工作,又有17年的时间离开象牙之塔,投入社会,投入大学,我觉得其中几乎每一件事,我都是最幸运的。”
来到纽约州立大学创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杨振宁,要负责更多的行政和教学任务。在美国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作为教授的杨振宁与学生相处时,不仅展现了大物理学家的风度,也有着鲜明的东方智慧,总能找到积极的方法来帮助大学发展,维持良好的研究与教学环境,并且温和而有效地解决困难。
校长托尔回忆起60年代的杨振宁时,充满了敬佩之情:“作为这个年轻大学的校长,我预计到必须处理很多问题。尤其是我认识到,在学生们关注越南战争及其他热点问题时,我得花大量的时间来应付学生们的捣乱,甚至他们要烧掉一个跟国防部签约做研究的计算中心。那个时候,学生们也要求学校的行政和教职主管都必须到校园入口的警卫岗亭里待一夜。当我得知学生们开始纠缠杨教授时,我可真是怒不可遏。他们可以浪费我的时间,但我觉得他们竟然意识不到纠缠杨教授是多么大的错误,实在太不应该了。在我看来,他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掉。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学生们就已经从杨教授那里得到了承诺:他将在保安室值一个夜班!事后发现,这实际上是杨教授做出的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承诺,因为他利用夜班的机会组织了一个通宵讨论会,他在讨论中谈到了科学与社会,还谈到了国际关系及其他一些热点问题。 这一事件受到了校园小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的正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段对峙时期的紧张状态。杨振宁总是一如既往地产生积极与正面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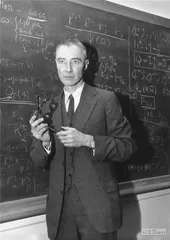 让杨振宁在30多岁的年纪,从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契机,当属他在1956年与合作者李政道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这个发现堪称惊世骇俗,打破了当时几乎所有物理学家的惯性认知,让人类对自然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以至于时至今日,即便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大多也听说过“宇称不守恒”这几个字。
让杨振宁在30多岁的年纪,从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契机,当属他在1956年与合作者李政道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这个发现堪称惊世骇俗,打破了当时几乎所有物理学家的惯性认知,让人类对自然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以至于时至今日,即便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大多也听说过“宇称不守恒”这几个字。
客观来说,杨李二人发现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并且迅速被世界物理学界所接受,不仅源于这两位年轻物理学家的无畏勇气、大胆猜想和小心求证,也得益于当时另一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对此做出的快速反应,立即通过实验对其进行了验证。另外,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也做出了罕见的迅速反应——在发现被证实仅仅一年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就被授予了物理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如果我们忽略掉诺贝尔物理学奖所带来的巨大荣誉,那么物理学界公认杨振宁的另一项成就——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才是他对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这项成就与发现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不同,在诞生之初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发展前景困难重重。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杨-米尔斯理论开始在理论物理学,尤其是粒子物理学领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甚至开始占据中心位置——这种影响就连杨振宁本人在最开始也没有预料到。
杨-米尔斯理论不仅在物理学的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杨振宁的代表作,它也充分体现出杨振宁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特性——自幼受到数学家父亲的影响,对于数学,尤其是群论领域有着极深的理解;而其受到的作为物理学家的训练,又让他得以把对数学的洞察和物理学家的直觉深刻地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对于一个全新的、最初并不被太多人看好的理论,杨振宁又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可以说,杨-米尔斯理论正是杨振宁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种种特点的集中体现。
杨-米尔斯理论源于杨振宁长久以来的思索,最终诞生于一次看似偶然的合作。1953年,杨振宁接受了当时担任“Cosmotron”质子同步加速器部门主席乔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的邀请,暂时离开了普林斯顿,前往位于纽约州长岛萨福尔克县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与杨振宁在同一间办公室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其中一位是当时只有23岁的实验物理学家伯顿·里克特(Burton Richter)——22年后,里克特与丁肇中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位则是当时27岁的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
当时米尔斯还只算是理论物理学界的新人,他刚刚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距离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理论物理学家诺曼·克罗尔(Norman Kroll)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年时间,就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开始了研究工作。米尔斯问杨振宁,两人能否开展一些合作,于是杨振宁向米尔斯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想法。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讨论与合作,两人于1954年在《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杨振宁在当年美国物理学会四月会议上所做报告的摘要《同位旋守恒与推广的规范不变性》(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and a generalized gauge invariance),另一篇则是更加详细的论文《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这两篇论文的诞生标志着杨-米尔斯理论的诞生。
杨-米尔斯理论以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命名,但当米尔斯回忆它的诞生过程时,则诚恳地认为杨振宁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写道:“在1953~1954学年,杨振宁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我当时也在布鲁克海文……并且被分配和杨振宁同一间办公室。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中,杨振宁都向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物理学家展现了他的慷慨,他也对我讲述了他想把规范不变性(gauge invariance)进行一般化的想法。我们对此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关于量子化过程的处理和得出最终形式的过程,但是其中关键的想法都来自于杨振宁。”
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杨-米尔斯理论在物理学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为什么被认为其中充满了美感?这要从人类通过数学形式来描述世界和发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说起。1960年,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曾经看似充满迷惑地写道:“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有着不合理的有效性。”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可以通过数学语言以极高的精度描述自然界的规律,数学的这种“有效性”实在是令人迷惑。实际上,除了数学的有效性,人类还认识到自然界中具有某种独特的美感。例如爱因斯坦正是出于对“惯性系”和“非惯性系”的平等性的信念,发展出广义相对论,用几何语言解释了引力现象。
数学自身也具有某种独特的美感。例如群论的发现,就让人们认识到在数学世界中还有着一种独特的秩序。那么,能否把这种数学中的秩序和美感应用到物理学中?自幼跟随父亲学习群论的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研究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群论领域,分为“阿贝尔群”(Abelian group)与“非阿贝尔群”(non-Abelian group),这两种群在进行运算时有着不同的规律。例如两个整数进行加法运算,彼此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因此整数集合和加法运算就构成了一个阿贝尔群;而两个高维矩阵在进行乘法运算时,两者的顺序就会对结果造成影响,这样的群就属于非阿贝尔群。
此前,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已经将阿贝尔群的理念应用到电磁学领域,并且在电磁学中拓展出一种此前没有人注意到的对称结构。这样的数学虽然形式优美,但是对物理学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帮助?当时大多数物理学家对此并不在意。杨振宁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群论被应用到物理学中的美感,还通过物理学家独特的直觉,认为可以将这种独特的对称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将阿贝尔群的对称性拓展到非阿贝尔群中。他相信,群论这种独特的对称结构必定会支配物理学的基本规律。
这个想法从芝加哥大学时期开始萌芽,最终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与米尔斯的合作中完成。时至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于原子核内部基本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在自然界中除了常见的引力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之外,还存在着弱相互作用(weak interaction)和强相互作用(strong interaction)。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些相互作用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又该如何通过数学语言描述不同的相互作用?物理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杨-米尔斯理论所体现的对称性在其中起到了最基本的作用。
目前,对于自然界中的基本粒子,以及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可以被归纳在“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之中,它描述了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并不包含引力作用)。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发现了人类寻找多年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这标志着标准模型的最终完成。而在标准模型的数学形式中,杨-米尔斯理论所蕴含的规范不变性可谓无处不在。
可以说,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把理论物理学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研究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在20世纪之前,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方式大多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开始,逐渐寻找其中的规律,最后尝试建立一套有效的数学理论。牛顿正是通过这样的科学方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典力学体系。时至20世纪初,爱因斯坦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物理学研究方法。他从一些基本的理念出发,试图通过数学形式寻找其中所蕴含的物理学规律。经过多年的探索,爱因斯坦最终通过黎曼几何,发现了描述引力作用的数学形式——广义相对论。
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前所未有,也出人意料地展现了强大的力量。杨振宁从中受到了启发,他从群论中所蕴含的对称性出发,相信这样的数学美感必然会在自然界中有所体现。正是这样结合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直觉和信念,指引着杨振宁探索出不朽的杨-米尔斯理论。可以说,从爱因斯坦开始,杨振宁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推向了极致。
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杨-米尔斯理论在物理学整体框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们对其评价也随之越来越高。1994年,美国富兰克林研究所授予杨振宁富兰克林研究所奖项(Franklin Institute Awards),颁奖词中写道:“这项工作已经排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类似的影响。”
时至1994年,在一个纪念规范场论发展的会议上,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自己的发言《规范场论:过去、现在和未来?》(Gauge Theory:Past,Present,and Future?)中,回顾了人类从发现规范场论到将其应用在粒子物理学领域,最终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历史。这是一条从麦克斯韦到杨振宁,历时100年的历程。格罗斯最终总结道:“对称性制约着相互作用,而杨振宁主宰着对称性(Symmetry dictates interactions and Yang dictates symmetry)。” 物理米尔斯数学杨振宁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