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住:独居社会的自由与孤独
作者:张星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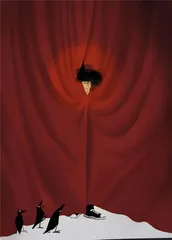 (插图 以独攻毒)
(插图 以独攻毒)
一个上了热搜的女孩
田琳从小被教育要独立,要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在上海念大学时,从大二开始,她就尽量不向父母要钱了,除了父母出学费以外,她开始想办法养活自己,最初当家教,后来又去做艺术展览策展助理。“我觉得首先应该经济独立。”
临近毕业,她在闸北区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学校在闵行区,离得远,所以她决定搬出学校,在实习公司边的弄堂里租房住。当然,居住的条件并不好。“其实那时候也会不开心,但这种不开心都是因为没钱。我当时也想过,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学校宿舍住,但既然我已经努力想出来住了,我就得承受这些。”
毕业后她来了北京,最初在通州附近合租,“被中介坑了”,三居分租,中介说另外两间的租户也是自己一个人住,但住进去之后她发现,一间里是一对夫妻,另一间里是一对情侣。“晚上可以听到隔壁的各种杂音,听到别人说话,晚上我敲键盘不能太大声,不能太晚回家,但最受不了的是他们都踩着共用的马桶上厕所。”田琳说自己那时一心只想努力赚钱,逃离那个空间。
8个月后,田琳搬出了通州,在离公司走路十分钟的地方整租了一套房,位置在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的热闹市区,离朝阳公园也不远。老塔楼里,一个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加上中介服务费,每月房租6500元。她25岁,养了只猫,开始了在北京的独居生活。
按照防疫要求,2021年的春节,田琳没回老家四川,而是留在北京就地过年。除夕那天,下班后和朋友匆忙吃了顿火锅,就回家了。凌晨,她走进卫生间洗澡,洗完澡,当她想出来时,却发现卫生间门锁坏掉,怎么也打不开。她没带手机,被困在了里面。
后来的事情上了热搜,她的经历被各路媒体报道。她在那个不到两平米的小卫生间里,踹门,大声呼救,敲击水管求援,靠自来水维生,度过了漫长的30个小时。终于在大年初二早晨,她把住在楼下、同样独居的邻居吵上来了,这位邻居帮她报了警,打了开锁公司电话。开锁师傅来后不到10分钟,帮她把卫生间的门打开了。
半个多月后,面对我,再次回忆起那30个小时的时候,田琳说自己反思了很多。
 很多年轻人选择合租来降低生活成本(IC photo供图)
很多年轻人选择合租来降低生活成本(IC photo供图)
她说自己从卫生间出来后的第一反应是去拿手机。她以为会有很多人惦记自己,但点进微信,满屏都是小红点,除了或许是群发的拜年信息就是订阅的公众号文章,她找不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消息。
更让她崩溃的瞬间是在大年初一,她被关在卫生间的头24小时里。那天她大声呼救,卫生间离入户门不远,果然有人循声围过来,她焦急地说明情况,却被门外的邻居们反问:“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你说你被困,怎么声音还这么大?”围在门口的邻居逐渐散去,却并没有人为她报警,她失去了一次获救的机会。
“后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对站在门口的那几个邻居,我不应该真实地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应该跟他们说现在着火了,把楼烧起来了,灭不了,他们可能就真的紧张起来,因为他们是我的邻居,只有跟他们真正利益相关的时候,人才会行动起来。”
事件最初被媒体报道后,田琳一边看房子,准备搬家,一边承受网络上的质疑和道德审判,以及对她生活细节的胡乱猜测:为什么不找男朋友?为什么一个人住?是不是在炒作?凭她自己的工作肯定付不起6500元的房租,等等。
甚至前来采访她的记者,也会问她:“你是不是一个有些自闭倾向的人?”“你选择长期独居,是不是因为不善言语沟通?”还有记者问她:“独居会不会承受很大压力?”
“我其实没太懂他这个问题的点在哪儿。这个压力是指什么?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如果是内在的,不管独居还是合租,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如果是外在的话,那就是钱上面的,独居确实比合租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更高,所以我只能努力赚钱,没有别的办法。”田琳告诉我,她发现,那些采访她时对独居带有污名化的人,都不是独居,而是合租。有个采访她的男记者,31岁了,对她说:“我也想独居,但我父母绝对不会同意的。”
周围的人也开始给她介绍男朋友,这让她很焦虑。“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其实是好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和有没有男朋友没关系,我选择独居或者不独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会为了结束单身,随便找一个男人谈恋爱。”
少有的让她感到欣慰的回应是,“天猫精灵”因为这件事升级了软件,推出了报警功能,以后无论在屋子的哪个角落,只要大声呼叫“报警”,“天猫精灵”就会拨通报警电话,据说下一次迭代版本,还会推出暗语报警。
另一个让她欣慰的是,帮她开锁的师傅在网络平台上也出名了,好评不断,评分上升了很多。师傅做这行不到一年,在北京见惯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女孩,被锁在厨房,自己拆了三四个小时才打电话求救。一个80来岁的老人,被锁在卫生间,6个小时后,家人下班才发现。除夕当天,一个30多岁的独居女性,出门贴春联,就被锁在了门外。还有的年轻人,出门后发现没带钥匙,提前跟他预约下班时间开锁。从他的职业来观察,独居现象,正在中国大城市里愈发普遍。
田琳的经历可能是极端个例,但却让人们关注到独居的青年人群。
实际上2020年,中国民政部也公布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高达2.6亿,超过英、法、德三国人口总数,其中8000万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上升至9200万。随着城市化发展、个人主义兴起、女性地位提高、网络社交发展、寿命的延长,独居早就作为一种新的人口结构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兴起。从1996年到2006年,全球独居人口从1.53亿增长到2.02亿。2014年,丹麦、芬兰和瑞典三国独居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40.5%、40.8%和39.9%。2015年,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独居人口占美国户籍总数的28%,意味着独居者已经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在纽约曼哈顿,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独居。
那么,中国的独居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吗?它会对人们的城市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会与欧美的独居现象有什么不同?独居,到底是当下年轻人短暂的人生阶段?还是一种将会改变社会结构的真正的新生活方式?
 猫狗陪伴着很多独居的年轻人(视觉中国供图)
猫狗陪伴着很多独居的年轻人(视觉中国供图)
猫狗陪伴与上门服务
许阿姨是河北人,和老伴在北京朝阳区东五环边的平房村住了20多年了。她之前一直是干食堂的,给人做饭,三年前,她换了工作,作为上门打扫卫生的阿姨,为一款提供上门家政服务的App工作。
在那款App上,她设置的上门服务范围是14公里。客人在App上预约上门打扫卫生,如果有客人选择了她,她需要先通过电话确定地址,然后再带着全套洁具准时来到客人家,进行2小时至4小时不等的清洁服务。这三年,她最南去过百子湾,最东去过管庄那边,最西到朝阳公园,而离平房村很近的朝阳大悦城、小悦城、天鹅湾,她去得最多。
她的客人90%都是“80后”或“90后”,自己一个人住,绝大部分是租的房,房子不大,对她都很礼貌。通常约过她两三次,就成回头客了。“阿姨来啦!来了自己干吧。”然后就不管她了。
许阿姨的客人里,80%都会养猫或养狗,这给她的清洁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每次下班回家,她浑身上下都是猫毛,第二天早上睡觉醒来,经常会发现嘴巴里还有猫毛。
许阿姨说也就是和我抱怨抱怨,她在客人面前,绝对不能展现出对猫狗的任何嫌弃。一旦不小心流露出来,客人下次肯定就不会再用她了。“他们真的把那些猫狗当小祖宗养着,你得边打扫边对着它说:‘宝贝,你可真好看。’那他们下次还会用你。”
客人中最普遍的情况是,一个女孩,自己一个人住,房租五六千,养了两只猫,给猫做美容,每半个月洗一次澡,还专门为猫买了睡觉用的小房子。“她们吃着外卖、用着阿姨、养猫养狗,人家也不剩钱,也挺好,活得潇洒着呢。”
根据亚洲宠物展联合宠物领域垂直媒体“狗民网”发布的《2019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19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达到9915万只,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其中,单身一族在宠物主中占比达32.5%,更有过半的单身青年将宠物视为亲人或者伴侣。
许阿姨的客人中,独居的女孩比男孩多,但女孩家里有时候比男孩家里还脏乱不少。
许阿姨见过的最脏乱的一家,女孩自己住一室一厅,以前玩快手,后来在望京上班,养了只松鼠。女孩每个月约一次许阿姨,“每次约三小时打扫时间,但时间根本不够,三小时光够叠她的衣服的”。女孩的背心、袜子、内衣、鞋子满地都是,进门时无从下脚,客厅有张桌子,桌子上落了厚厚一层“衣服山”,女孩吃完的东西也放在床上,牛奶倒了流到地上她也不收拾。一开门蟑螂满地跑,有次蟑螂钻进女孩耳朵里了,女孩去了医院。每次打扫,许阿姨要收拾出五大袋垃圾。
许阿姨见过最干净的家,是个男孩家。男孩给阿姨特意准备了专用拖鞋,一进屋,地面像镜子一样亮,屋子里什么都看不见,客厅就一个光杆桌子,连个水杯都没有。服务最少两小时,男孩家太干净,许阿姨后来实在没得做了,把他的猫窝都刷了。
这三年里,许阿姨见过太多独居的年轻人,也见过很多情侣住着住着分了。她也问过为什么客人要一个人住,姑娘反问:“我找个对象,他挣得还没我多,我要他?”
姜师傅干按摩十几年了,选这行主要是因为喜欢自由,干按摩不用坐班,时间灵活。以前他一直在按摩店上班,五年前开始成为上门按摩App的师傅,就像许阿姨的家政服务App一样,客人可以用App选择按摩师傅,预约时间,姜师傅就会带着泡脚用的水盆、一次性床单,以及各种按摩精油准时来到客人家里,进行一到两小时的足疗,肩颈、背部或者全身按摩。
他说这种App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按摩行业。以前在门店里,一半以上来按摩的客户是为了社交,通常是谈完生意后的娱乐消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姜师傅的客人里,80%都是年轻人,这其中60%到70%的人自己住,“都是不结婚的,单身的,都有个性”,28岁到35岁最多。姜师傅说他在北京也独居,“但他们和我不一样,三年前我前女友离开我回老家结婚去了,我是被动独居,我找不到另一半,而他们是主动独居,家里也催,又有条件,生活好、工作好,又有文化,但就是不结婚”。
 各类上门服务给独居者的生活带来便利(视觉中国供图)
各类上门服务给独居者的生活带来便利(视觉中国供图)
姜师傅住在朝阳门,他的上门按摩范围东到朝阳大悦城,北到惠新西街、望京,西到西二环,南边去得少。他客人里独居的年轻人主要住在沿海赛洛城、后现代城、双井、国贸、金台路、十里堡这一条线上。
在这个主要靠回头客的上门按摩App里,每位按摩师傅手法不同,“需要按透了,按到客人心里去了,客人才能认可你,才会再找你”。姜师傅告诉我,“按透”的第一步,是需要客人信任他。姜师傅去新客人家里也多少会有些紧张,如果有第二次、第三次,他便会边按摩边尝试着和客人聊聊天,扯扯家常,几次之后便熟络起来了。
他有位熟客,是个编剧,每次都约他早上8点来上门按摩。姜师傅来到他家的时候,他通常是刚写了一整晚的剧本,出门吃了个早饭回来。家里的窗帘全拉上,把窗外的朝阳捂得严严实实的,“你伸手都看不见指头”。他会和姜师傅简单聊几句,然后就躺在床上盖好被子露出脚,只让姜师傅做足疗,姜师傅坐在床尾的小板凳上给他按脚,不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姜师傅会按满订单规定的一个半小时,然后按照他睡前的嘱咐,安静地离开,带上门,无需叫醒他。
姜师傅说这位客人通常会这样连续约他一两周,每天早上如此,通过足疗伴他入睡,然后“消失不见”一两个月。再见面,他会和姜师傅说自己前段时间去外地出差去了。
客人通过App能预约的最早的上门按摩服务时间是早上7点半。姜师傅说这类订单通常是凌晨下单,这类客人也通常自己住,因为失眠,在床上躺到凌晨几点还是睡不着,情急之下下了个单,希望按摩师傅能够拯救他的睡眠。
但这类客人不好办,因为姜师傅7点半到他们家时,通常客人已经睡着了,把他们叫醒需要花番功夫。他有个熟客住富力城,有次早上5点多下的单,他7点20分到了他家门口,使劲敲门也没人答应,打客人手机也关机,给客服打电话,客服也没办法。砸了半小时门,把隔壁大哥都砸出来了,大哥问他:“你这是抢劫还是要债的?”最后客人终于被吵醒了,门开了。姜师傅问他:“你为什么下单?”他答说自己那会儿就是睡不着,头疼、迷糊,于是就下了一单,没想到下完单10分钟困意就来了。
更多的订单集中在晚上,从晚上8点半到11点。姜师傅说这些订单中90%都是自己住的小白领,因为入眠难,“睡前容易想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压力大,想法太多”,所以希望通过上门按摩获得缓解。
 在欧美国家,“未婚独居”往往被视为一种中产阶级新兴生活方式
在欧美国家,“未婚独居”往往被视为一种中产阶级新兴生活方式
什么算独居?
2013年,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曾在他那本著名的《单身社会》的结尾写道:“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无休的社会文化中,……独居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在他看来,与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的人选择独居生活,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这样的生活。独居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和各类“to C”的服务,让独居变得越来越容易。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将注意力更集中于自身。独居者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也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但注重家庭传统的东亚国家,会像欧美一样,出现越来越多的独居者吗?起码从数据增长上来看是如此。东京独居人口在东京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从1995年的38.12%增加到2005年的44.03%,首尔的独居比例从1980年的4.5%增长到2010年的24.39%。在上海,独居人口比例从1996年的8.73%增加到2014年的23.68%。在中国,独居青年群体数量早已超过了独居老人。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年龄在20至39岁之间的一人户有343.6万户,占了中国独居户数的三分之一,比60岁以上的独居总户数都多。
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与其他处于个体化过程中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不断享受个体自由的同时,还需要面对传统单位制和其代表的传统国家福利制度的结束以及对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上一代人还在享受事业单位稳定工作和单位分房制度的集体生活的时候,下一代人不仅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还要面对频繁更换工作带来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短暂性。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说,中国的独居现象与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有关,个人主义上升、婚姻推迟、生育率下降,还有同居率和离婚率上升,都会使得单身人口增加,而单身与独居又有着强关联性。此外独居现象更可能发生在大城市,与求学和工作机会直接相关。
但在中国,其实独居的概念并没有完全厘清:到底是一个人住一套房才算独居,还是几个人合租一套房也算独居?“西方不少对独居的研究指的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套房,‘未婚独居’是一种中产阶级新兴的生活方式,代表着更好的生活品质,与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都有关系。”但中国的研究主要针对“空巢青年”,即离开父母居住,无论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合租,或者与情侣同居,都算“空巢青年”。但这并不算是一个新概念,从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前往城市的打工者,都算是“空巢青年”。
沈洋也说,如果不与欧美社会相比较,其实也可以与文化相近的日韩比较。日韩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极高,达到70%以上,但父权制社会的痕迹依然明显,女性一旦结婚,就会面临辞掉工作的可能性,因此越来越多女性不选择婚姻,而是专注于事业发展。这使得日韩30至40岁的女性独居率很高,可以看作一种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韩国的生育率目前更是降到全世界最低,比欧美国家都要低,尽管韩国政府近10年来出台了很多支持家庭的政策,但也无济于事。
另一个存在于中国的现象是男性的选择。沈洋是上海本地人,她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性别研究博士学位时独居过好几年。她说自己回国后,身边有很多上海本地的女性朋友,工作之后都会选择离开父母家,在离公司近的地方租套房子自己住,但她好像没见过任何一个上海本地男性出来独居的,往往是工作后也住在父母家,然后结婚,然后和老婆出来同居,并没有独处的机会。
心理咨询师王嘉悦说,其实除去一线城市房租贵的问题之外,这里还涉及原生家庭分化这一心理学问题。在中国原本的乡土社会和嫁娶制度中,个人是不需要与原生家庭分化的,往往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共同在土地上耕作,但城市化的出现,让年轻人不断前往大城市工作,才有了与原生家庭分化的需要。此外原生家庭分化程度高的人,心理学上称之为自体感高,就是说对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看得更重,这种人更喜欢独居。
王嘉悦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心理咨询专业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做心理咨询师,已经六年了,客户都是“80后”“90后”。她说一个人自体感的形成,主要是在20多岁的阶段。从原生家庭或者学校集体环境分化出来进入社会后,人们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到底以怎样的生活方式存在于这个社会上?以前住在父母家或者住在学校,都是被动服从,当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就出现了心理学中常说的“四分之一人生危机”。自体感强的人,会在这个时刻主动选择独居,而更多人可能选择自己之前熟悉的生活方式,即继续大学宿舍式的合租,或者继续住在父母家。
能够在这个阶段考虑买下单身公寓的年轻人,是极少数的幸运者。
 独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房租
独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房租
独居与同居的轮回
房地产中介是小李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六年时间,他从店员做到店经理再到现在的商圈经理,如今他已经不直接做业务,主要负责管理了,朝阳区东四环边十里堡的一个店面,十几个人都归他管。
这个小区一共1400户,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大户型住宅楼,每户面积一百多到两百多平方米,总价没有下1000万元的,通常是家庭购买。此外还有一栋单独的公寓楼,与大户型住宅楼享有相同的精装修、地暖、落地窗,国企物业、负责接快递的前台、保安每层巡逻,每周一次免费的上门保洁服务,24小时的上门维修师傅可以帮着换灯泡、通马桶,24小时管家服务,即便出门时忘了锁门,给管家打个电话,管家就会上楼为你关门。只不过这栋楼里的306户,绝大部分都是“开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房间,60平方米,开放式厨房,没有燃气,只设电磁炉灶台,适合一个人住。
这种房子太特殊了,带客户们来看,不喜欢的人,只看一眼,撂下一句“这不就是酒店嘛”,然后继续去看其他小区的房子了。“所以这部分受众群体一定是小众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他们。”小李对我说。
他说,买这栋公寓楼里开间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通常在27岁到31岁之间,就是人们所说的“独立男性、独立女性”,独居,收入不低,言谈举止得体,都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各行各业的都有。小李说客户画像不会再年轻了,因为如果没有几年的工作积累,也无法支付买房的首付。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买房的年轻人,很少有连续缴纳五年社保获得购房资格的,通常是已经有了北京市集体户口或者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这也说明,他们的工作能力很高,被公司认可,已经帮他们在北京落了户。
这些人大多留过学。正因为他们在外国留学时独居过,又见过欧美的单身公寓,所以知道这种开间不仅能住,也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传统的住房观念里,这种“不就是酒店嘛”的开间连燃气都没有,会被认为“没有生活气息”。
这里的开间总价400万左右,同样的钱其实可以在周边买一套面积更大的老小区或次新房的一居室,但他们为了更好的精装修和更好的物业服务而牺牲面积和格局,去换取生活质量。小李看到,他们也是坐十几站地铁的上班族。
最后买下这栋公寓楼里开间的,通常第一次来看房时是年轻人自己一个人来。看过一两次后,才会再带着父母来。父母基本都是从外地专程过来,“带着钱来的”。小李能深深地感到,这类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不仅和睦,而且平等。“我觉得这些人的父母都是开明的。为什么说独立男性、独立女性,他们能有独立的自主权,他们的意见能被尊重,正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成长在一个平等、被尊重的环境里。”
6年来,小李见证了他的很多客户从搬进这栋公寓楼再到搬出去的全部过程。他陪着他们买这里的房,再卖这里的房,换到别处再买房。他说这种开间,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客户通常持有3到5年,大部分原因是要结婚了。
有的人离开了这栋楼的开间后,换到了2000万元的高档大房子,但更多的人做不到这么快的财富积累。他们把开间卖掉后,加上自己攒的钱和新的贷款,通常预算在600万到800万元。
再带他们看房,小李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落差感:没电梯的老小区绝对不看,但却没有足够的预算买最好的小区。小李说他的工作就是让他们“认清现实”。
对于年轻人来说,个人空间的变迁和重组正在不断上演。就像《单身社会》的作者克里南伯格在采访中跟我说的:“很少有人想永远独居,这不是人生目标,我认为它是一种人们开启和结束一段关系前后的可靠选择。”
聂师傅在北京已经干了15年搬家了。从搬家小工,到司机,再到自己干,现在他有一辆18立方米的大货车,外加几名师傅。网络平台搬家服务起步价是120元,司机不管装卸,而聂师傅提供的是这几年流行的日式搬家服务,不仅包含装卸和搬运,还包括打包,即负责在旧家为客人把所有物品打包标记,运到新家,再拆箱摆放好。
这种日式搬家比网络平台的收费稍微贵一点,但很适合没人帮忙的独居者或者没有精力收拾打包的人,再加上聂师傅干活儿踏实,价格合理,所以他的生意不怎么靠那个网络平台,而是靠朋友推荐。
两个独居的男女决定一起住了,会找他。通常不会是两个人一起搬到新家,而是一方搬到另一方家里住。搬家前,这对情侣会在准备搬过去的那一方家里一起商量:“这个衣柜你还要不要了?如果要,到时候搬过去摆在我家哪里?”
当然,也有分手的,一对同居情侣再次回到分别独居的状态。聂师傅曾经亲自为他们搬家搬到一起去,不过一段时间后,女人就又给他打了电话,说要搬家。
从独居到同居,还是从同居到独居,在这座城市不断上演,不过在聂师傅眼里,这些人无论怎么轮回着,每次都会找他。
(文中田琳为化名。实习生江紫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单身田琳自由独居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