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之谜
作者:薛巍 ( 《自由和神经生物学》 )
( 《自由和神经生物学》 )
还原论和二元论
1月16日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了心灵哲学家约翰·塞尔的新书《自由和神经生物学》。文章说,塞尔虽然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但他却是在牛津形成的哲学思想。他1952年到那里,一共待了7年,先是读本科,后是做研究员,那时牛津的语言哲学在英语世界处于主导地位。塞尔早期发表的作品就属于这个传统,集中讨论日常语言的基本问题。但50年代初回到美国后,他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开始时他仍然继续研究语言哲学,但到了80年代,他不再把语言放在哲学的中心,开始认为人类的心灵是更基本的领域,语言只是我们表达思想的媒介。
意识现象是一个令人着迷又令人苦恼的问题。对每个人来说,有意识就等于活着。但我们又很难弄明白意识是怎样从物质中涌现出来的,更解释不清为什么神经细胞的复杂排列会使我们有喜悦、失落、恐惧、无聊等感受。
对大多数当代心灵哲学家来说,对意识问题有还原论和二元论两种选择。还原论把意识归结为大脑的物理活动,认为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情感都只不过是头脑中神经元的活动。二元论则认为意识活动完全不同于大脑的活动,它也许跟大脑密切相关,但它是一种非物理的现实。
塞尔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普通人按照直觉,也接受不了科学主义的还原论,在还原论者眼里,绚丽、鲜艳的花朵只是各种色调、色素。在近代哲学史上,英国的洛克也只好给色、香、味这些比较高级的意识现象留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的质分为两类: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第一性的质是指客观事物的广延性、形状、不可入性、运动、静止、体积等等,他认为这类第一性的质是不以人的知觉为转移而客现存在的,是在事物的任何变化下都会保存着的。事物的颜色、声音、气味、口味等等是第二性的质,是主观的,即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好像是认识的主体通过感官附加到客观世界事物上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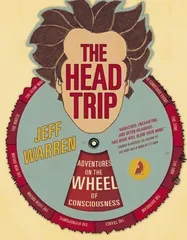
二元论的问题在于,如果意识独立于人脑,它解释不了意识何以能致使我们的身体听命于它。为此,笛卡儿设定了一个后来被证明子虚乌有的松果体。塞尔说他能提供一种在还原论和二元论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但在同行们看来,他没有成功,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意识肯定要么能还原为大脑的活动,要么不能。塞尔好像想同时持这两种立场,他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老抱着常识不放。还原论和二元论都跟常识不符,但这应该是因为常识并非正道。”
毕业于伦敦大学哲学系的尼古拉斯·费恩也指出,在意识问题上,要修正的是常识之见。为了解哲学现状,他走访了30多位思想家,写出《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一书。据他说,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理论是这样的:意识并不神秘,它是大脑的活动,至于大脑何以产生情感等复杂现象,可以由科学继续去研究。如果说大多数人接受不了这种观点,这不足为奇,常识总是跟不上科学的发展,人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做了一些类比:就好比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但常识看起来仍是太阳在绕地球转。人们不知大脑何以会产生高级的情感,就如同“不少人看到高保真电子设备或打开汽车引擎盖后也是如堕五里雾中。但只要我们攻读完机械学或音响工程专业,就应当对汽车如何行驶、对高保真怎样发生了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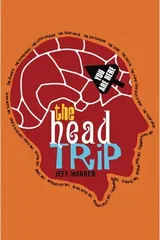
“新二元论学派的领军人物查尔默斯说,关键不在于没有肉体的灵魂是否可以想见,而在于没有了灵魂肉体能否存在。换言之,当笛卡儿搜寻魂灵时,我们应当去寻找僵尸。不是惊悚电影里浑身发绿、吃人肉的怪物,而是具备有意识的生命所有的身体特征与行为方式,唯独缺乏其精神特质。”照费恩这样说的意思,不用到别处找了,人类就是除了大脑的活动之外别无所谓灵魂的“机械人”,像《终结者:莎拉传》中的机器人那样,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像是一个扫描仪在工作。
十二种意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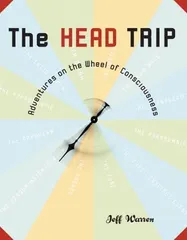
意识和大脑活动的关系被称为意识研究的“难问题”,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则被认为相对容易,不过这种区别也可以加以丰富。一方面,无意识并不等于低级、自发,它也有可能是高超的、积累出来的知识,哲学家们称之为默会知识。另外,“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要么是在睡着,要么是醒着,我们的意识黑白分明,中间没有渐变的灰色状态。但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发现,心灵有着惊人的灵活性,存在多种状态”。
2005年6月25日,伦敦一个15岁的小孩梦游,走出家门,走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后来人们发现她在一个距地面120英尺高(40米)的起重机吊臂上睡得正香。19世纪40年代,苏格兰一位医生给数百位病人催眠,让他们在做手术时不觉得痛,有一例是摘除一只有病的眼球,手术中病人健康的那一只眼睛一直在睁着。在20世纪的一个实验室里,一位佛教徒在打坐时,心理学家制造出一种“像耳朵旁边在放鞭炮”一样的噪声,这应该会让正常人惊醒,且面部肌肉抽搐,心跳加快。但这位高僧静如磐石,他后来说,那种声音在他听来又轻又远。
这几种情况,在一些人看来是奇迹,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骗局,因为它们太离奇、太不典型了,“如果说其中包含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有60多亿个灵魂,如果下工夫去找的话,你总能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
20多年前,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在《梦游病患者和神秘论贩子:科学和伪科学》一文中揭露了很多种“超感官知觉”骗局,比如灵魂出窍,他描述,“在宗教迷魂术或催眠术的条件下,或者有时在致幻药物的影响下,人们会报告说,他们的灵魂会离开肉体而外出游荡,在游荡完之后重新归附于肉体。但报告过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他还设想了一个简单方法来检验这种灵魂出窍术:当你不在时,一位朋友把一本书巧妙地放到图书馆一个高不可攀的书架上。然后,如果你能灵魂出窍,那么你就能漂浮到书那里,读出那本书的名字。当你的肉体重新醒来,并正确地说出你读到了什么时,那你就提供了灵魂出窍的证据。结论是,“就我所知,还没有灵魂出窍的演示实验能做到这一点”。
加拿大科学记者杰夫·沃伦则认为,一些意识状态看上去很离奇,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可能发生那种情况。现实在不同的心灵中有不同的反映,被催眠的病人感觉不到疼痛,雷鸣在打坐的人那里变成了低语,“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心灵,但谁也不知它会构造出什么来”。
沃伦区分了意识12种不同的状态,他在《头脑旅行》一书中像一位勇敢的游记作家一样,把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交给睡眠科学家、催眠师和神经反馈研究者,亲身体验大脑所能达到的各种特殊效果。
这些状态有些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比如白日梦和快速眼动睡眠(REM),还有一些则处于日常经验的边缘:梦游、嗜睡、睡眠瘫痪以及顶级运动员在比赛时处于的投入状态(zone)。入睡前有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这时大脑中开始发生各种思想和想象的自由连接,托马斯·爱迪生觉得这种状态能产生创见,所以他坐在椅子上打盹时,经常两手各拿一只棍子、棍子下面的地面上各摆一只金属碟子,当他开始瞌睡时,棍子从手中滑落砸到碟子上,一下子把他惊醒,他说,“很多主意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
(文 / 薛巍) 灵魂出窍意识之谜二元论还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