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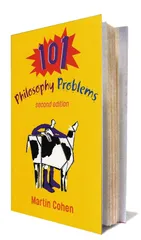
去年中国内地名气界新收两位红人,年中是易中天,年末是于丹。两位国家的在编知识分子,读读抄抄说说写写,就年入7位数的人民币,一跃成为2007年各自户籍所在地税务部门重点监管对象,实在是一件让人高兴的好事。
平心而论,易中天、于丹比起余秋雨之类第一代电视教授要进步多多,起码没有那么多知识硬伤让人诟病。而且于丹对自己的定位想得特别明白,她在回答苗炜提问时说:“我只是本着我的心提供一个起点,《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这是实话。孔子如果在世,未必听得懂于老师“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之类琼瑶式的格言。她把自己的书定名为《于丹〈论语〉心得》——用低调的书名预防大学同事前来踢馆,心得人人能说,不干学术鸟事。
比较而言,易同志的宣传就不够周密。在好几家媒体上,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媒体”没错,“对接”也没错,“文化”是顶空洞的帽子,谈不上对错,唯一的疑点就是“学术”。《品三国》能算学术书吗?如果说它是一本历史知识普及读物,我想不会有任何语病。但它不是一本学术读物,甚至不是一本学术普及读物。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101个哲学问题》,作者马丁·科恩是澳大利亚《哲学家》杂志的编辑,普通的澳大利亚学者。这本书是我以为的学术普及读物。
科恩提炼了古今哲学中的101个问题,把每个问题都编成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些故事是历代哲学大家的原创,科恩直接抄录,例如罗素理发师悖论的故事),然后根据故事提问。这些问题分成15类,分别是逻辑和悖论问题、伦理问题、数论问题、图论问题、时间问题、价值判断、个人问题、“12个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的传统哲学问题”等等。《101个哲学问题》的第二部分逐项讨论(不是解答)这些问题,这些讨论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科恩的心得,而是以往哲学家之间的辩证,科恩只是把大师晦涩的语言改写成明白晓畅的英文。讨论部分最常见的句式是: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另外有些人反对……还有人说……”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有关这些问题的哲学术语及其解释。

这本书专为中学程度的读者而写,所以作者的写作姿态非常柔软。他为搜集、编撰101个能引发哲学讨论的故事显然费了不少心思。例如有关悖论的第十个故事叫“一句话”,占了两页纸,一页一句话,前一页的那句话是“下一页的那句话是对的”,后一页的那句话是“上一页的那句话是错的”。哪句话是对的?第二部分关于这“一句话”的讨论——由此介绍哲学史上著名的“谎言悖论”,说了几百句话。
《101个哲学问题》,还有其他合格的学术普及读物,永远不会以全知的态度讲述作者的一家之言或一得之见。这些读物只是告诉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有几种讲法,它们激励读者在比较中发现最真实或者最准确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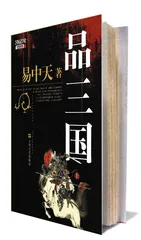
所以,易中天《品三国》如果是学术普及读物,他写“真假曹操”首先就要介绍关于曹操的文字根据和文物根据。关于曹操,历史上的记载如何,这些记载可靠吗,它们是不是得到了历代挖掘的地下文物的证明。古今中外,曹操研究有哪几家,有哪些相同的说法,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读者如果对曹操有兴趣,应该去参观哪几家博物馆,应该去读哪几本书。
当然,易中天要这样介绍曹操,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出版社未必敢和他签下百万合约,《品三国》更不会大卖。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底本——保证知识上不出大错,独断的叙述,加上一些娱乐化的口水,再加上一些中国人世故权谋的心得,这是2006年春夏之交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背后肯定有足够的聪明,但这和学术无关。成功和聪明已经很不错了,就不用和学术“对接”了吧。
质疑易同志,不是为了“学术”的定义——那样也太无聊了。主要的想法是,当下学术普及应该比知识普及更重要。普及学术不是普及学术研究,而是普及一种求真的思想方法,普及比较、反省、讲究证据、不大言惑世也不为大言所惑的思想方法。因为我的观察心得是,这些年中国人光长脾气不长见识。 品三国易中天成疑曹操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