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游泳》:格雷厄姆·斯威夫特长篇创作的前奏
作者:孙若茜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最初开始创作时,写的是短篇小说而并非长篇,这是经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当然,是否忽略了这一点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学游泳》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并且,我们已可以读到它的中文译本。作为英国当代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我们的中文阅读世界中,似乎还不具有与他文学地位相称的读者数量,这才是问题所在。
斯威夫特的作品早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在国外,尤其在法国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但在国内,他的读者确实不多。比起伊恩麦克尤恩,以及和他一样获得过布克奖的英国同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石黑一雄,斯威夫特的知名度都略逊一筹。一位作家的知名度并不总是和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相等,早期处事过于低调,或许也是他不被广泛认知的原因之一。
斯威夫特1949年5月4日出生在伦敦。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公务员,曾在“二战”中任海军领航员。在家里没有电视的50年代,斯威夫特的大部分消遣来自阅读和广播,他十二三岁就尝试动笔写作,并认为自己对文学,尤其是阅读有着很强的感受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被作家们在书中所创造的魔力搞得神魂颠倒,当时我就立誓要步他们之后。”斯威夫特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因此,他在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就读时选择的专业也是英国语言文学,并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在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最终并没有完成他关于狄更斯的论文。当时,他已开始潜心写作。
与大多数作家一样,斯威夫特经历了一次次投稿后的一次次退稿。“当我完成了学业,就面临着任何有抱负的作家都要面临的问题:怎样才能糊口填饱肚子?于是,我什么活儿都干过。”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曾做过保安,也在精神病院工作过,而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做兼职教师。直到1983年《水之乡》(Water Land)面世,获得布克奖提名并揽获了其他诸多文学奖项时,斯威夫特才冒险放弃了其他工作,开始尝试以写作谋生。
此后,他不断有长篇小说出版。1996年《杯酒留痕》(Last Orders)夺得当年的布克奖,由此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此后,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写作频率,出版了2003年的《The Light of Day》、2007年的《Tomorrow》等作品,2011年的《Wish You Were Here》因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而被译作中文《唯愿你在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不久,斯威夫特在英国推出了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England and Other Stories》,所收录的作品都是近年所作,且此前并未在其他媒体上单独发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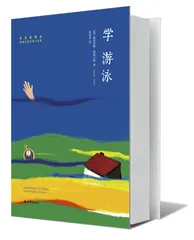 《学游泳》中文版
《学游泳》中文版
巧的是,译林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斯威夫特的中文译作,也刚好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不同的是,这本名为《学游泳》的作品集在英国发行的时间是1982年,所收录的11篇短篇都是其早期的作品。虽然出版时间看起来略晚于他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糖果店主》和《羽毛球》,但实际上,其中很多作品在集结成册前已有若干被刊载在《伦敦杂志》、《新故事》等当地的杂志上,有的还在BBC三台做了播放,也因此说斯威夫特的创作始于短篇小说。
这些早期创作所涉及的主题与后来的长篇一脉相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对真相的疑惧和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这是斯威夫特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三个主题,它们常常不带有明显界限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故事中而相映成趣。这使得他始终关注平民阶层普通家庭中的普通人,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故事中他们内心经历着多重挣扎。
他向来描写的都是所谓的凡人凡事,因为他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普通的,每个人都是不平凡的,独特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写作也正是要证明这一点。“我觉得写凡人凡事比追求轰动效应或猎奇要有意思得多。”斯威夫特曾明确表示。
在描述凡人凡事时,斯威夫特的写作之精细让很多人认为那些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说,他是个很宅的人,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写作,偶尔旅行但社交圈子狭窄,因此写作几乎必须完全依靠想象。“我并不把我个人的人生经验视为一种工作勘察之旅。生活就是生活,人们生活在生活中。因此,譬如说,因为我碰巧在旧金山,我不会为某部背景设在旧金山的小说而做有用的研究。我不会观察我认识的人而思考如何把他们转化成小说中的人物。我根本不会这样做。我笃信写作就是跃入未知的领域,但要做这种跳跃,你必须牢牢地依傍想象这根绳索。”斯威夫特曾说,“假如你非得描写自己所熟知的事物——这往往是惯常的忠告——那是非常悲哀的。你自己的阅历是有限的,因此它也许能给你提供一两件事的素材,但是你迟早得进行虚构。”
在叙述风格上,“相比巴恩斯,斯威夫特更具英国范儿,巴恩斯会把话说得很俏皮,但是英国文学中能把话说得这么俏皮的其实不是特别多的,另外,斯威夫特基本上不‘掉书袋’”。翻译了斯威夫特的《水之乡》、《杯酒留痕》两部经典之作以及《学游泳》的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郭国良说,斯威夫特的表达方式、语言节奏有着很强的辨识度,是翻译时要格外注意的。“比较诗意,能读出一点点诗歌的感觉。虽然描写的都是平淡琐事,但能饱含诗意正是斯威夫特在写作中所要追求的。他的节奏感很强,我尽量跟着他。他用一个单词的地方我就尽量用一个单词表达,他用一个短语我就尽量用一个短语,翻译其他小说时我不一定会这样,为了保证中文阅读的理解往往会自己加入一些词。”郭国良认为,虽然相对后来的长篇经典,《学游泳》在笔法上确有些尚不成熟的地方,但已经足可勾勒出斯威夫特的写作风貌,是进入其文学世界比较轻松的途径。
就斯威夫特的写作,本刊专访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郭国良。
三联生活周刊:斯威夫特的《杯酒留痕》在形式上有很多地方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相似,《水之乡》又被称作是对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戏仿,你认为他的创作和前辈作家的影响以及传统的文学理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郭国良:他认为有些故事是非常古老的,内核几乎是亘古不变的。不管是什么作家,传统的现实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同样故事内核,一代代的作家都要回归到这样的命题之中去。故事永远是那几个故事,只不过会加上一些现代人在特殊环境、特殊情境下的东西,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翻版,某种角度讲都是重复,逃脱不了。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清楚他究竟受到哪一脉作家的影响,有的时候作家自己也没有办法,因为影响是渗入到血液中的。
他在几乎所有的访谈中都强调过,他认为讲故事是写小说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是小说的职责。因此,他的创作也都是从讲好故事的基点出发的,是欧美公认的非常棒的“story teller”,讲故事的人。
他曾很多次地提到过自己并不喜欢文学理论,不想受到理论的指导或者说是干扰。但我想,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信他的话。因为我的感觉是,他对理论非常熟悉,是站在熟悉的基础上说那样的话,并不是因为不懂而排斥,并且还是深受影响的。在《水之乡》和《杯酒留痕》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叙述方式是很后现代的,碎片化的,除了传统的很强的故事性之外,他所具备的后现代性要把小说虚构的过程展示给你,是元小说的套路,告诉读者你在听别人讲故事。而传统的小说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作者自己隐没掉,告诉你一切都是真的。
与斯威夫特年纪差不多的一代作家,麦克尤恩,巴恩斯,石黑一雄,都是1950年前后出生,他们进行创作的80年代,是文学理论玩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一定会受到影响,不管愿不愿意。再以《水之乡》为例,除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外,还能清楚地看到其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学游泳》这本书里的《粉表》,也存在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此后的创作就没有这样的痕迹了,只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了。所以他现在也被认为是比较传统的小说家,总是按照时间顺序老老实实将故事推进。
三联生活周刊:从早期的创作到现在,斯威夫特在叙述上以及小说主题上是否一直保持着一些不变的选择?
郭国良:斯威夫特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只有个别情况下的次要人物会用第三人称讲述,而主角永远是第一人称,这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没有变过。主人公往往在人生的危机时刻站出来回顾:“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面对要解决的问题时,他永远在探讨,是蒙在鼓里好,还是应该知道真相?他认为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和秘密,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知道很多,否则生活的平静将被打破。当不得不将真相说破时,往往残酷。这是他常用的小说主线之一。第二,是战争对人生的影响,战争经过后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人的命运不可能脱离大的背景,这使得战争与个人的关系复杂而紧密。第三是家庭,夫妻、母女、父子之间的关系,他反复强调的是,一切都是过去的结果,人都是过去的产物,主人公之所以回望过去,起码追溯两三代人,是因为人现在的样子是上一两代人注定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过去。《水之乡》就非常典型,人必须要追溯,且不会放弃终极的追求,但又永远追踪不到根源,找不到原点,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求索的过程就像是剥洋葱,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核心。
三联生活周刊:斯威夫特的历史观才是他在作品中最核心的表达,怎么理解?
郭国良:他的历史观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历史本身都是被叙述的,叙述本身又是主观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它用到语言,语言是符号,并不稳定,不是一对一,而是全部在符号的链条里转动,永远不能指向事物本身。语言有很多是含混、暧昧、滑动的,词和词、短语和短语、句子和句子放在一起时,往往会生出一些你想不到的意义,跟你原来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甚至生出歧义。语言本身多于你要表达的东西,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是作家掌控不了的。
语言本身就具有这样空白的可供解读的个性,也是翻译的时候很苦恼的事情。当我知道一个词隐含的很多含义,又猜测作者也许是想把这几种意思都放在那里时,作为译者,面对几种都能讲通的意思却只能选择一种翻译成中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从他的短篇小说集《学游泳》里已经可以看到他长篇写作的雏形了吗?
郭国良:他的短篇小说像是长篇小说的前奏,所有的主题在短篇小说中已经初现端倪了,后面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水之乡》达到了高峰。小说里的主题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翻来覆去,有时候我觉得他很难突破了。即便把作者的名字隐掉我还能看出是他的作品,这其实是很高的评价,因为辨识度很高。但从某个角度上讲这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作家自己往往想要突破,希望自己是多面的,这很难。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斯威夫特在故意尝试所谓的突破吗?
郭国良:我觉得任何作家都在故意做这件事儿,有时候作家会有一些大动作,当发现自己无法驾驭某些领域,就又得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去,做得更精致。在《水之乡》之后,斯威夫特的东西都要努力摆脱这部小说的影响,因为他知道这部小说在其作品中的地位,别人都会以这部小说为标准来评判他,后面的东西写得好不好都会被拿来比,结果也都败下阵来。无论深度、广度都难以超越,后面的小说都只是在《水之乡》的某一点上开拓得更深。
其实,麦克尤恩、巴恩斯、石黑一雄都很注意在题材上紧跟当下,比如麦克尤恩在《星期六》里关注伊拉克战争,石黑一雄写了克隆人的事情等等,斯威夫特也是如此,2007年的小说《明天》就是关于试管婴儿的故事。但不管什么样的题材,他们的手法都已经形成,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其表达的主题内核也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放入了比较新的问题中。
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的短篇难免会有作家不成熟的创作痕迹吧?和经典的长篇之作相比,我们阅读它的意义在哪儿?
郭国良: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这本书中的人物变化不够大,不同身份的主人公讲不同的话,笔法、语调大概都应该有些变化,但这本书里所见,每个人说的话都还仿佛出自同一个人。文字上,也不如他后来的长篇那么诗意,所以翻译起来的难度不大。当然,从好故事的角度,这依然是一本值得好好阅读的短篇小说集,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氛围的营造,都已经有明显的斯威夫特的写作印记,是好的故事,且有回味的余地。相对长篇小说而言,这些都是“浓缩”后呈现,所以是用来接近斯威夫特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用来开启对他的阅读。 格雷厄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