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
作者: 叶北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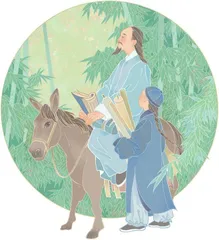
郑板桥跟于适没有见过面,算是神交。
这份交情竟是从一块墓碑开始的。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骑着一头小毛驴去潍县上任,路过城南的墓田,望着层层坟头歇脚。
书童寒茗打了个哆嗦:“老爷,太阳快下山了,要不……”
“不急。”郑板桥在坟堆里溜达,“老爷我下驴,第一件事就是体察民情。”
寒茗抽肩缩颈,捋捋胳膊上的寒毛,小声嘟囔了一句:“到坟地里体察什么……”
郑板桥笑了,拍拍身旁的青石墓碑:“看看,这石料,这款式,这雕工!再数数旁边的坟头,有多少个?”
寒茗挠挠头皮:“老爷是说,潍县的百姓,比范县的富裕?”
“孺子可教也。”郑板桥扒拉开荒草,看碑上的文字:“深恩显考宋公讳长松之墓”,字是颜楷;“故严父徐公讳祥之墓”,书仿汉隶;“故显妣慈母孟孙氏之墓”,用的馆阁体……郑板桥微微摇头。也是,能入他眼的书体,当世还有几种?
看了十几个,郑板桥终于眼前一亮,那碑上刻着一副联:“青山芝兰盛,碧海瀚泽长。”中间是“故吏部郎中于公讳远大人之墓”,背面还有一大篇碑文,仿的是《瘗鹤铭》的笔意。妙哇!用《瘗鹤铭》写碑文,不减庄肃,自得哀伤。郑板桥竟站在人家坟头前,欣赏起来。
寒茗也四下里乱瞅:“老爷快看,这是不是‘一盒茗’?”
郑板桥顺着他的手看去,周围几块墓碑碑文竟都是《瘗鹤铭》,而且墓主都姓于,当即断定:书碑之人必定来自于家。“寒茗!快!去打听一下,这城南可有个于家庄?”
“啊?”寒茗指着即将落山的红日,“您老再折腾,城门可就关了。难不成,咱们要在坟堆里露宿?”
“有何不可?”郑板桥来了兴致,“绝妙书文为伴,纵然与鬼魅为伍、尸骸同穴,也是天下第一等雅事。”
话虽如此,他到底还是赶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后来派人打听到,城南竟真有个于家庄,就在离墓田不远处;庄里于适老爷子,字肇诜,监生出身,以书法名于世,乃“北海三俊”之首;于氏碑文,都是他写的。
第二天,郑板桥熟悉政务,会见乡绅,抽不开身,便派寒茗带着礼物拜见于适。结果没见到于适,只带回一张便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郑板桥笑了,北冥者,北海也,也就是这潍县城。鱼嘛,自然是他于适老先生喽。意思是说这条鱼太大,老爷我这口锅炖不下他。好家伙,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此后,郑板桥勤政爱民,几年工夫就把潍县治理得政通人和,路不拾遗。郑板桥闲来无事,吟诗作赋,书画会友,潍县城谁不知道他兰竹石皆妙,诗书画三绝?于适虽没有亲自登门拜访,但每到年节,都会寄来一封信笺:从《逍遥游》到《人间世》,到《齐物论》,再到《养生主》。
寒茗头皮都快挠破了:“老爷,这是在夸您吗?”
郑板桥摇摇头:“总觉得这里边透着古怪。”
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修东岳庙,从二门上拆下一块匾来。寒茗飞奔来报喜:“老爷,快看,又是‘一盒茗’!”于适的信笺看多了,寒茗竟也识得字体了。
上眼一瞧,写的是“发育万物”四个字,郑板桥很不厚道地笑了:你用《瘗鹤铭》写写碑文也就算了,至少书文相称;眼下倒好,用“瘗鹤”来发育万物吗?
寒茗也笑了,原来这字不好呀。
郑板桥沉思半晌,神情凝重起来,竟然向牌匾鞠了一躬。当即召见乡绅富商,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建学舍,请名师,大兴文教。文教不兴,学风不盛,纵然是五谷满仓,又有何用?
到年关时,于适的信笺又送来了:“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大宗师》,好,得劲!
郑板桥一夜没睡,竟用他的“六分半书”把《大宗师》抄了一遍。
好景不长,郑板桥发官仓赈灾,被罢官了。临行之日,他特意去了趟于家庄,再不见于适就真没机会了。
开门作揖的是个青年,说:“先父临终前曾经嘱咐,让我代他拜见郑大人。”说着长揖及地。
先父?郑板桥愣了。
“实不相瞒,先父向来仰慕大人的书画文章,得知您来潍县任职,更是喜不自胜。奈何病体沉疴,不久于世,在您上任的第二天,就……”
“第二天?”寒茗叫了一声,“那不就是……”
“也就是说,如果那天我登门,还能见他最后一面?”郑板桥悔恨不已。
寒茗掏出那些信笺:“这又是怎么回事?”
青年道:“那是先父临终前写下的,让我每年往县衙投递一份。他说看大人的书画,大人必定是个孤傲清高的人,他愿与大人做个隔世之交。”
郑板桥怅然若失:“老先生的坟墓在哪儿?我去拜一下。”
来到坟前,却见青石碑上光溜溜的,没有刻字。青年连忙解释:“先父说了,他给人题了半辈子碑文,自己就不操心了,留待有缘人吧。”
郑板桥知道说的是自己,吩咐寒茗研墨,望着石碑沉吟片刻,挥笔写下两句:“北冥有鱼适南海,西风何意过东隅。”
(胡不归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25年第1期,曾 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