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女性的独立空间
作者:孙雅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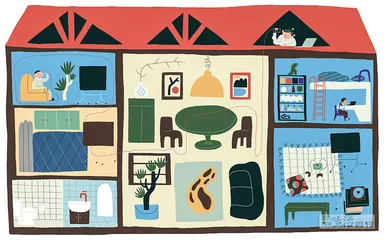 天天结婚两年多了,却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她住在福州市中心。那是一套35平方米的“老破小”二手房,没有电梯。她老公则住在城市的另一端,距离她家有十几公里。夫妻俩分别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都是婚前买的。通常情况下,两人只会在周末或节假日里见面,轮流去对方家中小住。如果去对方家里,提前打好招呼,不会突然造访。每次去谁家住,谁就负责家务,不存在谁照料谁的问题。结婚后,两人在财务上也保持独立,互不干涉对方的收入,只是平时的开销男方会主动多承担一些。两年多下来,天天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模式,这让曾经“恐婚”的她变得没那么抗拒婚姻了。
天天结婚两年多了,却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她住在福州市中心。那是一套35平方米的“老破小”二手房,没有电梯。她老公则住在城市的另一端,距离她家有十几公里。夫妻俩分别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都是婚前买的。通常情况下,两人只会在周末或节假日里见面,轮流去对方家中小住。如果去对方家里,提前打好招呼,不会突然造访。每次去谁家住,谁就负责家务,不存在谁照料谁的问题。结婚后,两人在财务上也保持独立,互不干涉对方的收入,只是平时的开销男方会主动多承担一些。两年多下来,天天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模式,这让曾经“恐婚”的她变得没那么抗拒婚姻了。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天天给自己设立的结婚门槛。如果没有这套小公寓,她觉得自己未必能有走进婚姻的勇气。面对不理解自己独立买房的亲戚朋友,她总是半开玩笑地解释道:“有了自己的房子,如果跟老公吵架了,至少不用担心没地方可去。”
2021年买房时,天天还是单身。那时她已经在福州工作了几年,一直租房住。一次换房期间,她去对面小区看房,发现有一套房正在出售,总价83万元,首付35万元,月供2100元左右。天天算了笔账,首付可以让父母支持一部分,月供跟她的房租差不多,心想买房比租房划算,也省得老是搬家。加上这一带自己住习惯了,毗邻商区,交通便利,是她心中理想的居住地。房子买完没多久,福州的整体房价就开始走低,但天天并不后悔,觉得至少提前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住进新房没多久,天天就恋爱了。男朋友比她小两岁,两人谈了一年恋爱,感情虽然稳定,但都没打算结婚。不过在双方的家人看来,女方已经30岁,男方28岁,是该结婚的年纪了。天天来自莆田,男友来自泉州,都是家庭观念很重的地方,长辈催婚的压力不小。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他们决定结婚。但两人约定,婚后依然不改变婚前的相处模式,各住各的房子,也不再买共同的婚房。结婚前,天天按自己的心意一点点布置起自己的小家,她花两万多块翻新了硬装,又购置了很多田园风的软装。她满意自己打造的空间,也享受独自在家消磨时光的感觉。这种日子刚过了一年,让她突然换一个地方,和另一个人共同生活,她不愿意。好在,她老公欣然同意了天天的提议。他也有自己独立充实的小世界,家里养了三只猫和一些鱼,喜欢打理植物。这也是天天当初喜欢上他的原因,觉得对方跟自己一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并且足够尊重她的想法。
在遇到老公之前,天天一度觉得自己不会结婚。她害怕结婚后两个家庭搅在一起的生活,光是长辈对年轻人指手画脚,以及逢年过节各种烦琐的礼节,就足以让她恐惧婚姻。并且,天天一直觉得,女性一旦结婚,就没有自己的家了,娘家会自动把女儿归入夫家,不再给她们单独留房;而夫家的房子又常常归于老公名下,很难视为已婚女性的保障。在老家莆田,天天见过婚后回娘家小住的女性被人在背后议论,“嫁出去的女儿怎么还天天回娘家?”她觉得这对女性实在不算公平。
不过,天天很小的时候,还曾听说过另一种婚姻模式,俗称“两头婚”。“两头婚”在福建和江浙一带流行已久,这是看重“传宗接代”的地区在独生子女时代兴起的新风俗——没有“男娶女嫁”的概念,也没有高昂的彩礼或嫁妆,新人不需要成立自己的小家,生下的小孩姓氏可以商量。某种程度上,这种相对自由的婚姻形式启发了天天,让她觉得夫妻俩分开住也没什么大不了。即便如此,像天天和老公这样各自买房的夫妻,也并不是“两头婚”中常见的现象,为此她不停地被家中的长辈念叨。
天天说,就像现在流行的“城市逃离计划”一样,分开住就是她的“婚姻逃离计划”,在她看来,独居可以祛除自己身上的“婚味”。她所理解的“婚味”,就是进入婚姻后逐渐失去自我,把伴侣和家庭放在第一顺位的状况。
与伴侣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为她经营婚姻的一种理性策略。结婚前,她和老公同居最长的时间只有一周,那已经是她能坚持的极限。说起来,她和老公并没有出现什么较大的矛盾,不过是两个人吃饭的口味不同,对房间整洁度的要求不太一样,作息时间也难以保持一致等等,但就是这些生活习惯的差异让天天不愿意将就,她更想回到自己的节奏里。自从约定“周末夫妻”的相处原则,独立的生活空间就成为天天保持稳定情绪的前提。每当遇到和老公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她就告诉自己,反正只共住这么几天,忍一忍就过去了,也犯不着对老公指手画脚。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婚姻中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最是徒劳,既然自己都不愿意被改变,又何必妄想去改变对方。 除了像天天这样,进入婚姻却不愿意为了婚姻而改变的,也有人是在婚后通过寻求独立空间进行自我探索。她们偶尔离开是为了让亲密关系走得更加长远。
除了像天天这样,进入婚姻却不愿意为了婚姻而改变的,也有人是在婚后通过寻求独立空间进行自我探索。她们偶尔离开是为了让亲密关系走得更加长远。
生活在绍兴的虾米已经结婚11年。她拥有独立住所已经3年。她的房子是一间套内面积43平方米的小阁楼,就在婚房的楼上,虽然是和婚房一起买的,但可以独立入户。这间小阁楼从前要么租给了别人,要么闲置,虾米和老公、两个孩子以及公婆都住在楼下,直到虾米动了打造一个独处空间的心思。
虾米做了很多年的全职妈妈。她第一次出现独立居住的想法是在怀上二胎以后,那时她的第一个孩子才8个月大,第二次怀孕并不在计划当中。二胎的到来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也让她和家人的关系突然紧张了许多。生活习惯和育儿观念的差异,让虾米和公婆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老公对她情绪的忽视也让她难以忍受,再加上产后激素分泌的失衡,众多压力让虾米患上了中度抑郁。去医院确诊病情后,她首先想到了和公婆分家,并向老公提议再买一套房子,但遭到了拒绝。老公是独生子,不愿意和父母分开住。一家人又勉强过了两年,公婆最终答应离开,住回离城区不远的乡下,每隔一个月再到城里住几天。
分家以后,虾米发现自己的状态并未明显改善。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对虾米的需求越来越多,与之相对,丈夫对家事的投入越来越少。因为,她的丈夫长期在她公婆的照护下生活,很少独立承担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这些让她感到,自己身陷在家庭琐事之中,身边围绕的朋友全是不同小孩的妈妈,大家谈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家庭。那段时间她总是想到,自己为了老公,只身一人从杭州来到绍兴,放弃了婚前收入不低的工作和熟悉的社交圈,一切都从头开始,换来的却是完全迷失自我的生活,对老公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两人的关系也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走出迷茫的状态,虾米决定先把自己从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而这首先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她想到了楼上的小阁楼。小阁楼原本简单装修过,虾米想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重新翻修,算下来需要10万元资金。这个想法很快遭到公婆和老公的反对,甚至连虾米的母亲也不赞成。为了减少计划实施的阻力,虾米主动提出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也不动用家中的存款,她要自己攒钱。为此,她专门出去工作了半年,又拿出理财所得的收益,等钱一攒够就立马动工。
因为预算有限,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找不到愿意接单的设计公司,虾米又开始自学装修。其间她改版了无数次设计,画了无数张图纸,还因为台风天家中灌水经历过紧急抢救,也被拿了定金却消失不见的装修师傅坑过,历时200多天终于完工。让虾米略感欣慰的是,小阁楼装修期间历经几次拆除返工,老公再没有表示过反对,而是任由她去折腾,偶尔也会帮着虾米处理一些状况。虾米能感觉到,老公似乎越来越能理解她的需求和坚持。 小阁楼装修一新后,虾米几乎每天都会上楼,有时候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是一整天,偶尔也会在楼上过夜。自己独处的时候,孩子就交给老公带。房子的装修设计只考虑了她一个人的需要。她在这里安装了可以生火的壁炉,可以泡澡的小浴缸,还有像洞穴一样的卧室,楼梯也不用安装防摔的扶手。待在小阁楼里的虾米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愉悦自己,泡茶、看书、冲咖啡、练书法,或者在露台种种花草。最重要的是,小阁楼的钥匙是小虾米专有,老公和孩子上楼需要提前预约,逗留期间还须遵守她制定的规则:需要的物品自己从楼下带来;临走前要带走自己的物品;要随时保持房间的整洁卫生;用房间的东西要先征得虾米同意。对虾米来说,这里是独属于她的私人空间,即使对家人也只能算是分享。保留从婚姻中出走的底气
小阁楼装修一新后,虾米几乎每天都会上楼,有时候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是一整天,偶尔也会在楼上过夜。自己独处的时候,孩子就交给老公带。房子的装修设计只考虑了她一个人的需要。她在这里安装了可以生火的壁炉,可以泡澡的小浴缸,还有像洞穴一样的卧室,楼梯也不用安装防摔的扶手。待在小阁楼里的虾米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愉悦自己,泡茶、看书、冲咖啡、练书法,或者在露台种种花草。最重要的是,小阁楼的钥匙是小虾米专有,老公和孩子上楼需要提前预约,逗留期间还须遵守她制定的规则:需要的物品自己从楼下带来;临走前要带走自己的物品;要随时保持房间的整洁卫生;用房间的东西要先征得虾米同意。对虾米来说,这里是独属于她的私人空间,即使对家人也只能算是分享。保留从婚姻中出走的底气
尽管在婚姻中极力保持独立,天天依然很看重跟老公维持必要的情感联结。不见面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保持联系,经常视频连线,跟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天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不奔现,但网恋不能断,精神陪伴始终要在。”独自居住的日子里,天天对自己的要求是,绝不搞精神内耗。如果对方一整天都没有消息,那就主动联系他,问问他在干吗,而不是暗自埋怨或语带责怪。不内耗的前提,是老公也给予了她足够的安全感,即使不常见面,也能让她感受到关心和爱意,尤其是在那些不经意间的细节里。老公会经常记得那些不太重要的小节日或纪念日,或是冷不丁地送她一些小礼物,还都能送到她的心坎上,比如一个“美丽废物”小摆件,或是她养生使用的生活用品,让她感受到他心里时刻装着自己。
随着婚后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天天越发满意老公和自己的适配程度,这尤其体现在老公对她的无条件支持上。结婚以后,天天经常面对双方父母的催生压力,母亲时不时劝她卖掉自己的公寓,跟老公一起买套大一点的房子,方便以后养孩子。但天天恐惧生育,也不想过早成为一个母亲。如果可以,她希望一辈子不生。这一点老公和她达成了一致,从不劝她卖房子,还会主动帮她挡住来自公婆的压力,有时候还会开玩笑地说,大不了以后领养一个孩子。早在结婚以前,她老公就经常在闲聊中表达对女性的共情,觉得女性很容易在婚姻中过多地妥协,不希望天天结婚后也面临这样的处境。天天没想到他真能做到言行一致,这让她越发觉得自己找对了人。
互相独立的婚姻难免显得过于风平浪静,偶尔天天还是会忍不住想,“我们之间是不是少了一些爱情?”否则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和对方黏在一起,即使分开住也怡然自得。但转念一想,充满激情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自己也从来没体会过,也就无从比较哪一种是更好的婚姻。她和老公甚至明确约定,如果谁遇到了更喜欢的人,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对方,再友好协商离婚。这在天天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她更在乎婚姻里随时可以离开的底气。她很难想象,如果夫妻俩绑定在一套房子上,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对离婚与否的判断,随之而来就是无限的妥协和忍让,而这样低质量的婚姻生活才是她最不想要的。 独立空间对女性来说,似乎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范畴,而是进一步走向自己精神世界的驿站。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创造性地提出,“女人想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要年入500英镑,房间还要能上锁”。既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女性因社会结构长期遭遇的逼仄处境,也敏锐地从物质角度分析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条件。她说:“一年500英镑的收入象征着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当中。不管我是否能将这种生活描绘出来,那都将是一种生机盎然、富有活力的生活。”英国另一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也曾在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中,描绘了一个中产家庭主妇试图通过独立居住寻找自我的故事,她拥有一个体面的丈夫、带花园的大房子以及四个孩子,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感到疲惫和空虚,于是专门去一个破旧的旅馆租下一个房间,在这里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椅子上坐着,这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谁的太太或母亲,而只是自己。
独立空间对女性来说,似乎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范畴,而是进一步走向自己精神世界的驿站。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创造性地提出,“女人想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要年入500英镑,房间还要能上锁”。既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女性因社会结构长期遭遇的逼仄处境,也敏锐地从物质角度分析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条件。她说:“一年500英镑的收入象征着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当中。不管我是否能将这种生活描绘出来,那都将是一种生机盎然、富有活力的生活。”英国另一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也曾在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中,描绘了一个中产家庭主妇试图通过独立居住寻找自我的故事,她拥有一个体面的丈夫、带花园的大房子以及四个孩子,却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感到疲惫和空虚,于是专门去一个破旧的旅馆租下一个房间,在这里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椅子上坐着,这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谁的太太或母亲,而只是自己。
自从开启偶尔独居的模式,虾米有意识地让自己从家庭中抽身,这让老公不得不更多回归家庭,不再理所当然把所有家务都留给她。如今夫妻俩在家中有了明确的分工,早上由老公送孩子上学,傍晚由虾米接孩子回家;孩子的兴趣班和作业辅导,老公也要参与进来;每周有几天由老公负责拖地,还有几天由他负责做饭;孩子的外套归虾米洗,内衣和袜子则交给老公。虾米说,老公的改变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放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说再多的话也不如行动有感染力,可能是我的改变影响到他了”。当初虾米说服公婆分家的时候,其中一个理由也是希望公婆能放手让儿子成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公婆发现儿子确实改变了不少。去年,公公还亲手封给虾米一个“本命年”大红包,以此表示对她的感谢。
独居生活也让虾米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她总觉得是孩子对她需求太高,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向她寻求帮助,后来她逐渐意识到,是自己事必躬亲的态度“喂养”出了孩子的高需求。当她试着把自己与孩子隔离开来,发现孩子找妈妈的次数明显减少,自己也不再容易感到身心疲惫,连脾气都变得温和起来,即使被孩子惹生气了,回到小阁楼待一阵就能冷静下来。面对老公,虾米也不再一味委屈和埋怨,随着独居的时间越来越长,虾米发现,自己对老公的情感依赖开始渐渐淡化,很少再因为老公对自己的忽视而感到不开心。她说:“我越来越能接受任何事情的发生,哪怕未来迫不得已要一个人生活。”
小阁楼的装修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虾米内心世界的一角。房间里除了必要的桌椅、床铺、柜子和餐具等,几乎没有太多其他的陈设,零碎的物件都被收进看不到的地方,一眼望去整个装修风格极其简洁。这种极简风格不同于虾米的婚房设计,婚房虽然有192平方米之大,但总是显得拥挤杂乱。到了装修小阁楼时,虾米开始有意去做减法,甚至每住一段时间,她还会扔掉一些东西。她把这种断舍离的心态也带入到了家庭关系中,她曾对老公说:“不要以为结了婚,我们的关系就永远是这样了,结婚才是我们关系的开始。如果你不愿意维系,这段婚姻我也可以不要。”
整理好自己的心境和生活,虾米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只围着锅碗瓢盆打转的主妇,内心的焦虑缓解了不少。前不久,她又在绍兴郊区租了一个房子,想在这里学做陶艺,偶尔和家人一起去爬爬山、亲近大自然,她觉得自己离理想中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文中天天、虾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