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冬与加速变暖的地球
作者:邢海洋 又到了《节气歌》里“三九四九冰上走”溜冰的日子。可“三九”已到,北京的那几家著名的户外冰场还没有一家开门营业的。今年暖冬无疑了。
又到了《节气歌》里“三九四九冰上走”溜冰的日子。可“三九”已到,北京的那几家著名的户外冰场还没有一家开门营业的。今年暖冬无疑了。说起冬天的冷,从圣诞到元旦,这段时间是最容易用体感判断的,每年“双旦”时节大家聚会逛街,从热气腾腾的餐厅或商场走出来,夜晚呼啸的北风总给人深刻的记忆。可今年就没有这种皮肤和骨骼感受。植物也感受到空气的薰暖,12月的北京的多所公园内,不仅腊梅悄然开花,连迎春、山桃都提前登场了。如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内上山的小径边,已有迎春等春花星星点点,在圆明园、朝阳公园、奥森公园等地,也偶有山桃花开放了,这些植物被天气“骗”开花,春花冬开昭示的暖冬比人类的体感还要来得客观。
冰场开业时间更是有着严格的寒冷“标准”。为确保安全冰场的开放对结冰状况有硬性要求,冰层的厚度得在15厘米以上。可1月4日,“二九”的第六天,据报道什刹海冰场后海最厚处仅11厘米左右,最薄处只有5厘米左右。即便厚度达了标,还需要之后一周气温持续保持在-8℃到1℃之间,以确保冰层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按照天气预报,“三九”第一天北京的平均气温才降到1℃以下,这意味着即使冰面迅速结冰到15厘米厚,“三九”天冰场也很难开放了。
通常,北京的冰场是12月底开放的,比如2023年末到2024年初的冬季就是2023年12月28日试营业开放的。此前的冬季,2022年12月29日什刹海边上的北海就可以上冰了。再向前的上冰时间,有据可查的是2022年是1月12日、2021年是1月9日。疫情三年又逢冬奥会,冰场的开放时间或增加了其他的考虑,但疫情前2020年初冰场是1月5日开的,彼时冰场的管理人员在解释晚开放的时候,很明确地告知公众是因为结冰结得晚了。从冰场的开放时间看,2024年末到2025年的冬季的“暖”是历史上罕有的。
暖冬似乎是好事,走在户外不会被寒风吹得站不住脚、冷到彻骨,户外活动频繁了;供暖节省了燃料,在没有集体供暖的南方人们也不再遭受阴冷天气的“摧残”。但从户外冰场这一项上看,溜冰的乐趣是要被大大压缩的。冬天没有冬天的样子,蛰伏在土壤和空气中的害虫冻不死,植物乃至作物接收到错误的物候信号冬日里开花发芽,却经受不住天气反复,一次寒潮就可能被团灭,一年的收成都可能因之泡汤。所以我们通常所希望的风调雨顺也包括冬天的冷,该冷不冷并非理想的气候环境。并且,这个暖冬还很少雨雪,冬天少了感觉,土壤少了滋养,病毒在干燥的空气中传播,呼吸道疾病于是高发。
当然,暖冬还可能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届时我们将遭遇真正的气象灾难。 暖冬之前,2024年11月我国平均气温5.1℃,较常年同期偏高1.9℃,创历史同期新高。2024年10月,全国平均气温为18.8℃,较常年同期偏高1.7℃,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而这一年春季,我国平均气温12.3℃,夏季平均气温22.3℃,秋季平均气温11.8℃,均为有公开的、完整的气象记录的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2024年均气温10.92℃,较常年同期偏高1.03℃,且是最暖的一年。
暖冬之前,2024年11月我国平均气温5.1℃,较常年同期偏高1.9℃,创历史同期新高。2024年10月,全国平均气温为18.8℃,较常年同期偏高1.7℃,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而这一年春季,我国平均气温12.3℃,夏季平均气温22.3℃,秋季平均气温11.8℃,均为有公开的、完整的气象记录的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2024年均气温10.92℃,较常年同期偏高1.03℃,且是最暖的一年。
2024年妥妥的炎热之年,这一年还是厄尔尼诺消退之年。通常情况下厄尔尼诺发生强盛的年份,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反而小一些。厄尔尼诺消退年,太平洋海温过了峰值,赤道附近海水在信风的吹拂下,高温传导到印度洋,那里离中国南方比太平洋暖池还近,构成中国春夏降水的主导力量。印度洋海温偏高,在季风的吹拂下印度洋水汽大量登陆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华南会形成大规模降水。我国长江流域几次大汛,如1998年、2020年乃至2024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都是在厄尔尼诺消退之时产生的,去年开春到夏天华南更是一场雨下了小半年。
可过了夏天,刚入秋降水势头戛然而止。长江下游近乎干涸,干流露出了河滩;北方自10月以后也很少降水了,更不用说下雪。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曾在夏天引导着太平洋水汽对中国中东部狂轰滥炸,可到了冬天当季风转向,副热带高压仍然强势,当冬季副热带高压偏强且位置偏北时,它就像一道屏障,阻碍冷空气大规模向南推进。2024年末到2025年的冬天,很少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北风,而是沿着纬度方向的西风,而同纬度来的风温差不大,气温是降不下来的。
全球变暖,即便西伯利亚这个传统冷源也缺乏足够的寒冷储备了。那里冬天气温大幅偏高,亚洲冷极奥伊米亚康2024年12月全月均温-34.7℃,比1991~2020年均值高出10.3℃,打破了1980年12月保持的最暖纪录。西伯利亚大冷源不给力,冷空气在生成和积累上严重不足,尽管偶尔有冷空气南下却难以形成强势的寒潮。当然,全球变暖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充满波折,圣诞过后西伯利亚冷极的温度又急转直下,给中国大地带来一次大范围寒潮,暂时扭转暖得让人不安的冬天。即便如此,按照2024年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11月全球空气表面温度月度公报,目前超高温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的前几个月。
我们刚经历了工业革命乃至第四纪冰期以来最热的一年,2024年在2023年已经接近努力控温目标的基础上又升温0.14℃。除了2024年是最暖年之外,观测史上第二暖的年份为2023年,第三暖为2021年,第四暖为2022年,排名前四暖的就是最近4年,甚至我国有完整记录的1961年以来前十暖的年份都出现在21世纪。 突然就突破了《巴黎协定》的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的目标,这真让人措手不及,要知道,这个目标是本世纪末,也就是76年后的控温目标。不过,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举办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9)上,与会国“巧妙”地回避了这一敏感话题——《公约》判断地表气温的标准不是某一特定年份的气温,而是20年的平均气温。阿塞拜疆,这个中亚腹地的国家,其石油天然气的产能正在快速释放,正致力于成为中亚能源大国。
突然就突破了《巴黎协定》的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的目标,这真让人措手不及,要知道,这个目标是本世纪末,也就是76年后的控温目标。不过,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举办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9)上,与会国“巧妙”地回避了这一敏感话题——《公约》判断地表气温的标准不是某一特定年份的气温,而是20年的平均气温。阿塞拜疆,这个中亚腹地的国家,其石油天然气的产能正在快速释放,正致力于成为中亚能源大国。
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1)上,全世界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缔约国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的统一安排。其长期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也就是1850~1900年间全球13.5℃的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如果足够努力做得更好,则可以把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内。
在《巴黎协定》签署的2015年,受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当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连续第二年打破历史纪录,较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0℃。这一年地表升温刚好达到1.0℃,使之注定成为里程碑式的年份。因为强厄尔尼诺作用,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气温登顶有着偶然性。不过,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人类又一个美好的愿望,2016年,厄尔尼诺消退之年,全球地表均温再次打破纪录,地球正式进入了超1.0℃时代。幸运的是,随后的两年全球均温有所下降。可到了2019年地表气温再次掉头向上,温度几乎与2016年的纪录持平。再后来,地球温度又进入了全新的升温周期,从升温1.0℃到1.5℃,地球只用了9年。而在20世纪的100年中,全球地面空气温度平均上升了0.4~0.8℃。
不过,2024年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9)并没有确认我们已经超过了《巴黎协定》所给定的第一个控温目标。大会的主要议题围绕着如何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展开,达成了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安排。事关地球温度变动的数据和背后的原理,则交给科学家团体。
2023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的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指出,相对于1850~1900年,2001~2020年这20年平均的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0.99℃,而2011~2020年10年平均的全球地表温度已经上升约1.09℃。
联合国气候报告对权威性科学性的追求,使得它的结论非常谨慎,这也意味着它的判断会严重滞后于当下地球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动。
其实,地表温度是否超越了《巴黎协定》努力控温目标已经不重要了,通过体感、物候以及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气温播报,我们显然正在向着《巴黎协定》所声明的,要严防死守的2.0℃迈进,正在进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气象大时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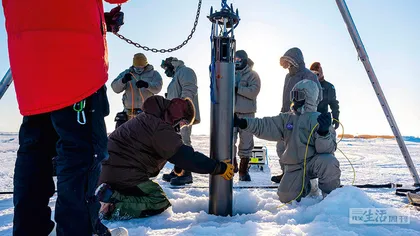 冬天暖了,我们似乎享受到了全球变暖的红利,可到了夏天,那才是真正的考验。不妙的是,按照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元旦这一天,全球平均气温又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1.71℃。
冬天暖了,我们似乎享受到了全球变暖的红利,可到了夏天,那才是真正的考验。不妙的是,按照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元旦这一天,全球平均气温又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1.71℃。
2024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创下新高,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420ppm,比1750年的278ppm高了51%。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会“困住”热量,地球越来越热。这是传统的地球变暖的科学解释,以此为基础的气候模型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全球变暖的研究已经成熟,似乎无需改进了。
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人做过实验,证明了它的升温作用。可20世纪前半期气候变化并不明显,人类还在战争的泥潭中疲于奔命,即便科学家团体也很少有对全球变暖发出警告。战后百废待兴中科学研究步入正轨,陆续有科学家提出了全球变暖的机制,如日本科学家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在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研究中,借用了刚刚开始普及的计算机来预测天气,他用一个自地面到高空的空气柱模型简化大气运动。空气柱中空气上下对流,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升,大气温度随之升高。2021年他和另外一位科学家一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奖委员会表彰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分别设计了气候模型,预言了全球变暖。
按照真锅淑郎的计算,当二氧化碳水平翻一番时,全球温度上升将超过2℃。
20世纪80年代,尽管那时候的地球平均温度只比工业革命时期的温度高了0.6℃,可感知性并不太强烈,幸运的是,人类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开始设立气象站,此后便有了连续的、科学的气象记录,0.6℃虽变化不大,但在气象记录里却呈现了连续的趋势。而从1958年起夏威夷的冒纳罗亚观测站开始记录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自此以后科学家发现浓度曲线一直在向上,与全球温度变化形成了对应关系。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的目的便是提供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评估,其发布的一系列报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依据。
IPCC最近发布的两次报告,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到第六次(AR6),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AR5报告期间,1998~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的升温速率每10年为0.05℃,小于1951年以来每10年0.12℃的升温速率。报告发布后还引发了一阵对全球变暖的质疑声浪,可很快2014年地表温度就创了纪录,AR6发布的时候,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更为清晰、确定,在加速变暖、气象灾害频发的现实面前质疑的声音基本消声灭迹了。
地球温度变化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IPCC集中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的研究团队,似乎可以从各个层面涵盖气候变化的各种成因,做出精准的分析和预测。AR5中科学家们确定1951~2010年全球升温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在AR6中,由于地表更显著变暖,科学家进一步溯源,从而确定从1850~1900年到2010~2019年,人为影响造成的全球增温幅度为0.8~1.3℃,最佳估计值为1.07℃,与观测的升温幅度1.06℃基本一致,其中温室气体的贡献为1.0~2.0℃。又由于空气中气溶胶增加反射了太阳辐射,相应抵消了部分升温效应。
但显然,这仍然是未能预测2020年后地表温度以更快的速率升温,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的确在增加,但增长曲线并未如地表温度一样陡然加速。面对着加剧变化的世界,再按照IPCC以10年乃至20年为周期的研究,似乎已难追赶上这个加速变化的世界了。 来自工业化排放的二氧化碳,一直是全球变暖研究的主要因素,这无可厚非,它是温室效应的推动性因素,也就是强迫性力量。但近年气候突变,很可能出自次生因素。
来自工业化排放的二氧化碳,一直是全球变暖研究的主要因素,这无可厚非,它是温室效应的推动性因素,也就是强迫性力量。但近年气候突变,很可能出自次生因素。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显示,在任何给定时间,大约有67%的地球表面被云覆盖。这是基于2002年7月至2015年4月期间收集的所有卫星云观测数据的平均值得出的云量状况。根据IPCC报告的评估,气温每升高1℃,大气可以多保留大约7%的水汽。水蒸气也是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3倍。但在评估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推动作用时,人们似乎更关注二氧化碳,较少提及水汽,其原因是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主要受气温控制,而不是由排放量控制。科学家认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增减是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反馈,而不是作用力。
但水汽在空气中的分布和形态,却可能是气候变化背后重要的催化剂。刊登于2025年1月3日《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地球上的云层正在缩减,加剧了全球变暖》揭示了有关大气中云量的一个事实,在过去20年里,全球反射云层面积缩小了,虽然幅度不大,每10年覆盖率下降约1.5%,但确实减少了。缩小的云让更多的光线透过大气照射到地表,加剧了全球变暖。
云层是地球的遮阳伞,当全球变暖,科学家本来预测它们会相应地变多变厚,从而抵消温室气体的作用,想不到的是云却在变少变薄,天空也会变得更加晴朗,而毫无阻隔的阳光可能会让全球升温加剧。至于云量变少的原因,科学家的解释多种多样,至今仍难达成一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大气环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云层的形成和分布;而人类活动也可能对云层产生间接影响,如航运业排放的废气中的颗粒物可能改变大气的成分和结构,进而影响云层的形成。一些新法规的实施虽然改善了空气质量,但也可能无意中改变了大气的某些特性,影响云层的分布。
其实早在NASA公开发现前,已经有气象学家用模型预测到一个地球低空云减量的临界点正在出现。科学家重新对20世纪中叶气溶胶排放量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中叶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大量气溶胶排放在数十年内为地球带来了冷却效应,掩盖了二氧化碳积累造成的变暖效应。21世纪后各国对大气污染的控制日渐严格,空气中气溶胶减少,水汽缺乏凝结核,少了聚集的条件。一旦气溶胶排放——也可视为空气污染达到了顶峰,气溶胶对地球的降温作用将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温室气体的升温作用,于是在单一的升温作用下,全球变暖将呈现出更快的速度。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气候科学家塔皮奥·施耐德(Tapio Schneider)在2016年的研究中指出,在计算中加入工业排放导致的气溶胶因素后,气候模型预测的全球变暖速度更快。美国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心的诺曼·勒布(Norman Loeb)对2013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急剧上升,同时海洋云层覆盖也在减少的解释是,云层的减少可能与中国和北美加强污染控制有关。当全球多地区,尤其北半球寒带和温带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大气治理,空气更为清洁干净,水汽却失去了附着物而无法凝聚成云。
《巴黎协定》确定在2100年前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力争在1.5℃之内。从AR5和AR6的预估结果不难看出,只有在很低排放情景和低排放情景发展路径,到21世纪末全球增温才可能不超过2℃。而场外的气候建模师们,给出的是远高于2℃的升温。根据现在大多数领先的气候模型〔包括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和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Hadley Centre)的模型〕计算,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时的气候敏感性比原先的预计高1℃或更高,最高可达5.6℃。来自卫星的数据显示,研究人员建模得出的预测可能已经成真。
当然,即便气温更高,我们也不希望生活在大气污染、不见天日的雾霾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