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刑法学研究历程
作者: 高铭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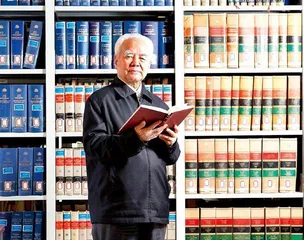
一、殷勤致力于学术探索
学术研究最直接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这是我六十多年一以贯之在努力的事。审视从1954年到1979年二十五年的岁月,虽然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刑法立法中,但还是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195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体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其中“犯罪构成”一章由我执笔。又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完成后,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认为我对刑法立法工作颇有心得,要求我写一篇关于如何学习刑法的材料,为相关专业的教职人员提供教学资料。我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近8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学习纪要》,把刑法立法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梳理了一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正式颁布实施,许多人又拿出这本小册子,发现其中不少有意义的观点,这本小册子一时风靡学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印的《检察业务学习资料》第13辑中,特别刊载了全文,推荐检察系统人员学习。同时,法律出版社的负责人通过友人联系到我,请我从一名参与立法学者的角度,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刑法诞生方面的书,这正与我的想法相契合,于是迅速进入了写作状态。当时,学校分配的教学任务很繁重,我只能将夜间的空当用来写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近20万字的书稿,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在这本书中,我发挥亲身经历立法的优势,对我国刑法条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对制定过程中的各种分歧意见,进行了客观评价。1981年7月,该书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法律出版社经过初步考察,设定印数为12000册。但是面世后,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太多人渴望读到这本书,而市场上买不到此书,有的人就动手抄写,于是就出现了“手抄本”。
这本书的再版是时隔31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因市场供不应求,法律出版社就计划再次印刷,我考虑到从1981年起,国家立法机关就不断制定单行刑法,而这本书并没有包含这些内容,表示等以后有机会修订时再印为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行,我才最终下定决心对这本书进行修订,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2015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由于刑法修正的内容较多,且2014年4月还一次性通过4个刑法立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蒋浩先生又找到我说:“本来书已售完,与其简单地不修改加印,还不如利用此机会,对书的内容充实完善后再版。”后来我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对刑法的修正内容,以及其间出台的4个立法解释增补到书中。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后,全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刑法教科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十分尴尬的事情。1982年,由司法部牵头,邀请了全国12位刑法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在北戴河召开刑法学教材统编研讨会,组成了刑法学教材编写组,大家一致推荐我担任这本教材的主编。1982年底,经过刑法教材编写组的共同努力,“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最权威的刑法教科书顺利完稿,定名《刑法学》。这本教材发行后仍然供不应求,出版社再版了8次,印数达200万册,创同类教材数量之最。1988年,该书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的双重殊荣。受益于这本教材的人,难以计数。
与此同时,我国的刑法学研究生教学正处于启动阶段,教育部又把刑法学研究生教材的主编工作交给了我。刑法学研究生的教材定名为《刑法专论》,编写者几乎都是当时国内刑法学界的资深学者。《刑法专论》交付出版后,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对此书深表肯定,推荐此书作为全国刑法学研究生的指定教学用书。这本书因此成为我国第一本刑法学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在研究生群体中掀起了一阵热潮,不少成名学者也把这本书纳入书单。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在原国家教委的组织下,我又于1987年受命主持了供高等院校文科专业使用的新教材的编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刑法学》一书终于问世。与其他刑法学教材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新,富有开拓精神,为我国刑法学教材的编写树立了一个更加成功的典范。此书后来在1992年获得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我主持出版了《刑法学原理》(三卷本)。这套书集合了我国刑法总则理论领域的重要成果,荣获国内图书出版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起初,该书以“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后来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做了调整,将其列入“中国丛书”出版。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我的刑法理论主要观点的话,那就是:坚持并倡导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刑罚人道主义等基本原则;坚持刑法的职能是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并重;坚持实质和形式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坚持主客观要件有机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坚持定罪量刑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坚持治理犯罪必须运用综合手段,刑法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的、谦抑的,刑法的干预要适度;坚持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和矫正,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逐步减少死刑,直至最后废除死刑。以上八个“坚持”,可以说代表我的主要学术观点,也是我著书立说着重阐发宣扬的。
说到犯罪构成理论,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过时了,应当采用德日的阶层化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很明确: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仅是学习借鉴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学界共同建设、发展和完善的本土性成果,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对中国刑法学术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这也是对过去四十年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基本肯定。我特别想强调,这个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事司法人员的作业指南,对于维护和推动刑事法治一直都是发挥了正面价值,学术界有的同志对于四要件体系的担忧或者指责,事实上只是理论上的自我设想,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成为现实。
中国的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事业在过去四十年里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相关性。德日的犯罪论体系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具有很多优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同时认为必须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乃至现行中国刑法学体系推倒重来的观点则是不可取的。我先后在《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发表《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在《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发表《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在《法学》(2010年第2期)发表《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等论文,将我的这个立场和观点说得很清楚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一向关注死刑问题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就一直把死刑制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始终认为,死刑制度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国死刑问题涉及多方面因素,诸如立法动向、司法实践、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政策方针、理论观念等内容,死刑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关乎全社会。中国疆域辽阔、风土人情各异,民情复杂,死刑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国,“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所以我国死刑改革的步履应当稳健一些。然而,从更长远、更广阔的角度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近代刑法学鼻祖切萨雷·贝卡里亚就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不人道以及不必要,限制以至最终废除死刑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多次参与中国刑法的制定、修订工作,有责任、有义务推动刑法的适用和研究向更科学、人道和良性的方向发展。作为学者,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尽其所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要努力把死刑改革的正确理念推向公众,引导公众的死刑观念,尽可能地为社会的法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最终确定在68个,占罪名总数的16.5%。随后,我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解读”文章,多次指出“死刑罪种过多”等问题,提出应当设法逐步削减直至最终彻底废除死刑的改革方向。我尤其不赞成对单纯经济犯罪判处死刑。从各国刑法来看,经济犯罪基本都没有设置死刑。开放的中国,必将适应更加开放的法制,我呼吁有关方面尽早对此进行改革,以树立生命的最高价值观。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种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原则上免除了已满75周岁老年人的死刑。这是我国自颁布1979年《刑法》以来首次作出大幅度减少死刑的规定。我参与了修正案的起草修订工作,在修正案通过审议时我感到很欣慰,对国家决策机关在死刑问题上的理性表示充分肯定。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削减了死刑罪名。我认为,下一阶段,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努力重点应当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并分阶段削减死刑罪名。今后,我将继续为死刑改革工作而努力。
二、全程参与刑法立法
1954年10月,那年我26岁,接到通知,要求我暂时搁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去全国人大参加刑法立法工作。刑法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法律室,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参与起草刑法的小组中,负责人是彭真,由于他另外担任重要的职务,主要承担刑法起草的把关和审核工作。具体工作是由法律室主任武新宇和副主任李琪负责,武新宇负责向大家分派任务,李琪负责向上级(主要是彭真)汇报工作。武新宇后来担任中国法学会第一任会长。刑法起草工作分三个小组,霍幼方负责第一组,刘仁轩负责第二组,张松负责第三组。刘仁轩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霍幼方和张松分别来自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东北局。其余的人员,都是像我这样从其他单位借调而来。
党中央一直强调,立法的依据必须建立在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因此,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和调查,让立法者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内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万多件刑事审判材料,分析总结形成了《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总结》,其中对所有法院适用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加以统计,总结了90多个罪名、5个主刑和3个附加刑的刑罚种类,提供给立法小组作为基础资料参考。立法小组又从天津市人民法院调取了1953年至1954年两年间全部刑事案件总结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此外,立法小组还要求每个小组成员到相关部门和工业企业,对工业企业运行中出现的责任事故进行调查。当然,除了国内的资料外,国外的刑法立法现状也在立法人员参考之列。如1926年的《苏俄刑法典》就成为我国刑法立法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刑法典,立法小组也都一一研读。像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我们本着批判吸收的原则加以借鉴。
1955年,我和参与立法的成员如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拟成任务。紧接着通过无数次的会议讨论,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每次会议都充满了思辨和诘问,会议之后都会出现新问题和新意见,修改之后又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进入修改阶段的早期,几乎每个月都会换一个近乎面目全非的稿子。细微的修改次数,已无人能记得清了。在一次次的修改后,修改幅度慢慢变小了。较大篇幅修改就有22次。1957年6月,法律室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这个稿子完成后,立即送到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据说,毛泽东同志当时也看过这一稿,表示还算满意。在相关领导层面走了一圈后,稿子又进行个别修改,最后提交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是充分肯定的,最后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回馈的意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作最后修改,然后作为刑法草案公布试行。立法小组成员听说这个消息后,都很受鼓舞。我也激动极了,一直盼着一部真正的刑法出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近三年的努力在这一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