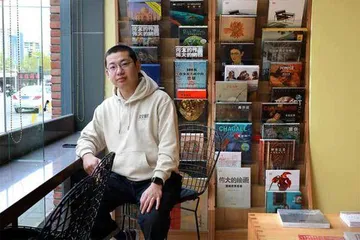播客:客厅、都市摇篮曲与声音的河流
作者: 欧阳诗蕾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十多年里,中国人的手机使用流量仅在2017到2020年就呈现出月均从1.775G到10.3G的变化。知识付费、短视频、直播……媒介风潮一波接一波,视听快感与心神涣散同时发生,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一种不需付出的即时快乐,手机一点,随时随地采撷刺激、新鲜与快乐。
声音产品的弧线也越来越私人化,以往人们收听广播,现在用智能手机和入耳式耳机。播客这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内容生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从字正腔圆、体贴温柔的广播节目变成了更日常或更有“人味”的节目。新旧创作者们共同塑造了播客的气质,学人、媒体人、脱口秀演员、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人……
相比我们熟悉的那些抚慰人心的深夜电台、字字皆“金”的知识付费音频,播客当然是新媒体,而相比国外的播客(podcast)热潮,播客已经不算新了。它恰好出现在视觉传播已无可扩张的媒介节点、出现在疫情时期人们保持物理间隔的常态中,还出现在有越来越多历史经验之外的现象的当下——这三年里,公共场域蹦出35岁焦虑、内卷、打工人、穿衣自由等等新词,近处有疫情波动,远处有俄乌冲突——无论从表达还是接收来说,人们需要一个性价比高的场域。
当流量、字节的规律被越来越熟练地运用,把人切分成点击量、停留时长、点赞数时,播客以声音这一介质提醒我们已经被忽视太久的事实——人是完整的肉身。
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调研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播客听众约有8600万人。PodFest China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播客听众中超过85%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近九成35岁以下,多数听众来自一线城市。
陪伴感,是播客创作者和听众在过去两年里常讲到的词。我们采访了播客主播、听众、研究声音文化的学者,试图理解在播客流行的这几年里,被智识、快乐与陪伴感包裹的播客的内核。
笑声太大了
在“随机波动”主播张之琪的客厅,笑声常常太大了。
北京望京,一间有整面落地窗的客厅,自从做播客随机波动以来,这里成了节目的主要录制场地。播客备受关注的这几年,随机波动这档泛文化谈话类播客始终是最有代表性的播客节目之一,也是播客平台小宇宙订阅量第一。每当嘉宾到来,客厅里的两只小猫先熟练地躲起来,三位主播和嘉宾落座,麦克风打开,录音设备的显示屏上,声音条开始跳动。
历史学家罗新几次来做客,有一次聊疫情,正值最初武汉最艰难时,几位主播情绪上涌,哭得难为情,又笑着开解,互相勉励;美食博主田螺姑娘聊做菜,妈妈计算着她回家的时间做好饭菜;媒体人、作家梁文道做客聊007邦德,从间谍聊到服饰美学,聊到小时候妈妈为了看邦德总带他去电影院……有时在两个多小时的录制中,三个主播聊着聊着突然对上眼,笑出声。
从2019年初到2022年春天,一百多期节目录制下来,窗外樱花更替了几个来回,其间播客越来越受关注,随机波动在小宇宙上的订阅量上升至28.9万,节目动辄收听量过10万,三位主播以强烈的个人风格组成了这档节目的气质。
播客是英文单词“podcast”的直译,在视觉空间过载、有声书和知识付费音频课陷入红海之际,包括随机波动在内的文化类播客为知识分享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风气。
“大家是不是还是觉得,播客是一个很正式的东西?”主播张之琪疑惑地望着我,又望向主播冷建国。这天主播傅适野因小区疫情而居家隔离。这是个安静的春天的晚上,接连两天的大雪已经化开,樱花开在落地窗外。
笑,不行;抢话,不行;有口音,不行;如果情绪到了,理解主播和嘉宾,但最好也不要哭——张之琪和我讲起这些常见的播客评论,分别在大前年、前年、去年和现在。“笑声太大了”是最常见的评论,毕竟连脱口秀演员的播客都被批评笑声太大,这类评论随着一拨一拨新听众的出场而接力棒似的出现在播客评论区。“现在这种随便说话、互相抢话、不时大笑,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大家对音频节目的记忆都是字正腔圆,剪得干净,大家一板一眼讲话,这就是‘对,标准的样子’?”
按照以往的内容产品规律,不应该照着批评来修剪节目吗?
“我们特意全保留了下来。”张之琪声音愉悦而柔和。随机波动依然是三位主播自己剪辑。和她们以往在媒体写稿一样,四五天的操作周期,不留备份,一周出一期。她们会做大量的准备功课,但在节目剪辑中不会剪去那些无伤大雅的嘴瓢、重复和语气词。
“因为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她说。
两年前,因参加《奇葩说》而大热的学者刘擎在一次采访中面对“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和媒介更新并没有带来更开放、平等、理性的言说和对话(在年轻一代身上尤其如此)”的提问时表示,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同的趋势,“我发现年轻一代的学人做的播客(比如像“随机波动”)、公众号等,水平非常高。有时候也会注意后面的评论,质量也相当高。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好好说话的人仍然很多,也存在好好说话的人。”
35岁焦虑、穿衣自由、内卷、亲密关系、学术生态、青年人的焦虑,还有最近的俄乌战争,当下人们关注的公共议题几乎被一网打尽,在这个文化访谈节目中,来做客的有梁文道、学者孙歌、艺人姜思达……主播们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和嘉宾交谈,这些交谈往往因双方的知识储备和善意而过于“丝滑”,但也有针锋相对的凌厉时刻,有听众戴耳机在路上听到也紧张得驻足,大气不出。
“我们还是不知道听众喜欢什么。”冷建国望着我想了会儿,又望向了张之琪,我毫不怀疑如果三位主播都在场,她们将击鼓传花似的望下去。
“我感觉,播客没办法像以前公众号时代。总结公众号10万加一样地总结出一个公式或算法。”张之琪补充,“声音很个人也很不常规,有些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她举的例子是,一百多期节目中收听量第二是她们三个人在聊“树”,在小宇宙有将近十四万的收听量(节目有一个半小时)。这个选题是题荒时三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最后定下的原因也十分“随机波动”——那天恰好是植树节。
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用户数超过200万,播客节目超过一万档,随机波动位列第一,29.2万订阅量。在福建厦门,医生张洋每周在小宇宙上像摘果子一样摘下新鲜播客,许多播客是周更。他从随机波动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的一期节目入门,之前他以为播客就是广播电台和有声书、音频课。现在,他每天都在听播客,有学人、媒体人录的“随机波动”、“忽左忽右”,脱口秀演员录的“无聊斋”、“谐星聊天会”、“不开玩笑”,还有声音纪录片式的“故事FM”。
张洋29岁,2021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临床工作。他每晚从小宇宙下载好播客节目,在上下班40分钟车程里听,1.5倍速播放,有时坐在单位班车里,他被耳机里主播们的笑声吓得一愣,但小宇宙四百多个小时听下来,他也接受了。“可能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
只要打开手机,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在朋友圈、微博、新闻弹窗的包围里,他原本觉得听播客只为取代听歌,但过去几年,一度是他青睐的舆论场的微博已经很难开展讨论。他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是交流,但微博上沟通的性价比太低。注册到不记得第几个微博账号时,他不再在微博发言,只转发一些社会求助信息。
累了,他说。
智能手机普及的这些年里,张洋最大的感受是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比如国内大大小小的争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比如2022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威尔·史密斯的一巴掌。遇到不太明白的事情,他会期待他信任的几个播客聊聊,要是还不够,就点开梁文道的播客“八分”,戴上耳机,“听听道长怎么说。”
都市摇篮曲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梁文道,千万别客气,”梁文道笑声洋溢,“坦白讲,我听过你们聊的很多期节目,实际上是我没法聊的。”
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调整,“随机波动”和“八分”的“串台”主题定为爆米花电影007邦德系列。“我从007系列的邦德形象演变中发现一个规律,英国越是不行的时候,邦德就越雄壮威武。到克雷格出演邦德的时候,英国已经越来越没有大国的感觉了,离帝国时期越远邦德就越强调雄性气质。”与随机波动的两位主播围坐桌边,梁文道抽着雪茄分享了他的英国观察。
录制前,主播们准备好内容提纲,但只有真正进入聊天后,她们才听到另一个人眼中全然不同的世界,对梁文道来说,邦德电影就是他成长中的消费主义天堂,邦德穿的西装、喝的酒、开的车、戴的表,这些数不清的门道和故事与消费符号是男人之间的密码——“是两只公狗互相辨认彼此的气味。”梁文道大笑。
作为播客八分的主播,梁文道常去其他播客串台,2019年创办的随机波动、2016年创办的“日谈公园”、2013年创办的“大内密谈”等。串台时,梁文道一贯谦逊:“久仰久仰”“我是来向几位学习的”“我不太了解,尝试说一说”。主播们则一致表示,道长好,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
“如果梁启超在现在,他肯定也会做播客。”2019年,作家、媒体人许知远在做客播客“忽左忽右”时说。相比传统媒体,许多人开始尝试制作内容和形式更自由的播客,门槛也更低。
尽管中国第一批播客之一“反波”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当年就拿下了国际播客大赛最佳播客奖,但直到2020年,播客在疫情中才开始流行。2018年开始,媒体人、脱口秀演员、综艺节目的大热嘉宾等纷纷入场,因为成本低到只需要一台手机,普通人也开始制作播客。接着平台涌入,垂直播客平台小宇宙拥有播客节目超过一万档,喜马拉雅、蜻蜓FM、网易云音乐等网络音频平台纷纷增加播客的入口和权重。
2018年8月开始,梁文道的八分作为单人口播的播客,开始了每周两期的更新。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八分连续一个月每天更新,那是人们居家隔离最难熬的时候。播客中,依然是人们熟悉的那个梁文道,谦逊、温和,娓娓道来,从当下事件出发,结合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去剖析和思考社会趋势、文化现象。对当时在湘西老家隔离的张洋来说,八分让他在不安里感受到被抚慰。有几位听众表示,2020年春居家隔离的那阵子,都是在梁文道声音的陪伴中度过的,他们也在那时养成了收听播客的习惯。
在八分的评论区,常有听众问,道长聊书的《一千零一夜》什么时候开呀?“但是真正聊书的时候,数据就会偏低一些。”八分的编辑、文化品牌“看理想”内容主编杨大壹说,和社会事件相关的节目收听量高很多。
“一开始,节目只想做八分钟。”在北京北三环的看理想办公室,杨大壹说,团队原本希望梁文道像以往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把这一成熟的节目模式从视频转到播客。可播客有自己的媒介逻辑。“我们在选题群里讨论热门话题,分享资料和用户留言,但道长发来节目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内容的,每次我收节目都跟开盲盒一样。”有时早上一醒来,杨大壹在群里收到梁文道凌晨四五点发来的播客音频,讲文化、聊时事,也讲漫画《进击的巨人》,这位老媒体人以三四小时的节目体量去准备内容,再录制一到一个半小时的素材,最后编辑剪辑成50-60分钟左右的节目。
从书籍、专栏到电台、电视制作、播客,梁文道在不同媒介中依然保持着恒定的表达方式。一位梁文道的多年听众表示,“我觉得长期的陪伴感和价值观的认同最重要,尤其是听时事内容有时会获得安定。虽然每当这时,道长几乎都会强调‘八分’不是时事节目,是文化节目,(笑)我们也都明白这样说的不易。”而在录制时,梁文道的对话感也很重,比如“今天是礼拜五了”,他会对听众说“你累吗?我告诉你,我可累坏了,凌晨快3点了”。也会说,“我又回到北京了,在北京的酒店里头,开始准备这期节目,明天一早又要去做节目,你说我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