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童年美术馆里的奥秘
作者: 孟依依
占地近3500平米的麓湖·A4美术馆坐落在成都天府新区,离主城区近二十公里路程,平日并不热闹,但每年8到10月,这里会像过节一样,刚放暑假的孩子与家长们来往不绝。“你会发现整座美术馆的气氛都在改变。”副馆长、首席策展人李杰说,他戴一副黑框眼镜,高瘦健谈,因为一头卷发被孩子们叫作“爆米花叔叔”。
每年8月开始,A4美术馆如期开启iSTART儿童艺术节,自2014年举办第一届,至今已进入第九年。与国内绝大部分展览不同,iSTART像一颗奇异的种子,在这里儿童与成年艺术家一样拥有思考和行动的主导权。他们说要建立“宇宙共和国”,于是建立宇宙共和国,他们拍摄13岁以下孩子接管地球的电影,在论坛上讨论运动、冷战、校园欺凌,他们观察自我,也观察世界,“为什么我谈论的一些那时认为不怎么深刻的理念和思想观众会‘哇’?关键是这一群在‘哇’的大人们为什么没有读懂《先知纪元》里面的隐含信息和思考,是认为我那时太小了不可能想到而不‘过分解读’吗?”看起来颇为早慧的14岁孩子吴联成说。《先知纪元》是孩子们的动画作品。
让儿童发声,李杰常常将之视作为儿童赋权的行动。
儿童长期以一种边缘的形式存在于成年人社会,作为附属得到了诸多关爱,同时受到许多束缚。直到学校教育逐渐取代学徒制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晚近的儿童观念及赋权行动才逐渐发展起来,至今不过一百多年。
然而,“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扭转了家庭作为仅有的儿童教育途径的情势,人类社会赋予儿童新的社会角色:学习者、投资未来的对象,并将其作为社会共同的财产……而童年则成了一份长期无薪的实习工作,用来在日渐缩小的中产阶级中谋得一席之地。”李杰在《童年美术馆》中写道。
“我们要去注入一些变量,不能让一个社会过于单一叙事和固化。”李杰想,非营利美术馆也许可以部分承担民间教育的角色。
2011年的“植物奇妙纪”,2013年的“∞”儿童艺术展,2015年的“不可思议的世界”,2017年的“没大没小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2018年的“童年疗养院”与“Little Bang”,2019年的“童年的秘密”,2020年的“do it”和“行动学校”,2021年的“1001游戏学校”……至今iSTART已展出超出3000件作品,8000名儿童和一百多位/组成年艺术家参与创作,也展开了近600场公共教育活动。
如今不少城市开始筹办儿童艺术节,比如重庆的O'Kids,深圳的Bang!儿童艺术节,厦门的TCCAKids艺术家,也有同行找到李杰,问能否带着iSTART做巡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尊重每一个孩子。”李杰说,“我们要跟每个孩子说为什么把他的作品带到那个城市去,要和每个孩子以及家庭签署协议,和成人是一个标准,不能因为这是孩子的事情就小看它,我觉得反倒因为是孩子的事情,所以应该重视它。因为他们经历的所有体验和过程都是一次启蒙,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权利的主体。”
除去日常展览的打理,李杰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策划iSTART,从5000个报名的孩子和百来个项目中选择、跟踪和讨论,最后与1500名左右的孩子共创,完成七十多个项目,日常其实不过两三名工作人员和他一同推进,琐事繁多。
“工作量是蛮吓人的。”李杰好像刚意识到这件事,又显得乐此不疲。
以下是李杰的自述:
灾难作为启蒙
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一定程度上使成都从一个小市民社会转向了一个公民社会。地震过后没几天,的士司机开始免费送物资去灾区,只要有能力的,比如学过急救的人都愿意过去,我们在对抗天灾——一个敌人或者说想象的敌人——的过程中培养了共情能力,它是一个被唤醒和启蒙的过程,并且成为了社会的毛细血管扎根在社区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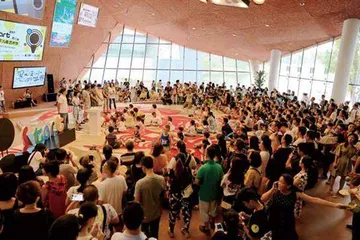
A4美术馆在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被迫闭馆。馆长孙莉带工作团队和艺术家到灾区去,看能用什么办法帮助失去亲人的儿童。在那样的现场里,艺术是很无力的。孩子们满脸都写着表达,可他们并不需要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们继续联合NGO做乡村公益活动,做艺术疗愈,馆长一度觉得我们介入得过深,我就以个人身份跟着NGO继续做了两年。慢慢我发现也许问题出在城市。在乡村的价值感分裂这件事上,城市是有“原罪”的,它像一块强势的磁铁把所有东西都吸过来,从不考虑他者。
不过后来我又修正了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在面对儿童这个群体时,城市和非城市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眼中没有多少“儿童”,简单来说就是儿童没啥权利。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确实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教育机会,但在学校里上课也不能随便说话,必须唯唯诺诺,被一种虚无的所谓成功的价值裹挟,甚至不能跟自然接触。
既然无法很好地介入和改变乡村,那就不要去消费他们。从某方面来说,城市或许可以反向提供动力。所以我们又回到城市做儿童艺术节。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实际上除了馆长和我,包括美术馆的很多同事、合作的机构、学校、政府部门、教育工作者,他们虽然觉得很好,但也都有担心,比如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持续?这些展览会不会改变当代美术馆的严肃性和学术性?艺术家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参加这种项目?谁愿意投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也时常自问这些问题,以提醒自己不能陷入狭隘的境地,其实我无法明确答出其中的“利害”与“动机”。
我们只是认为要站在儿童的视角去看儿童的问题,去了解人类后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时候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想象成外星人,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曾经都是他们,而现在我们试图把他们都变成和我们一样。实际上呢,他们还在那儿,和我们很不一样。
我常常说是要为儿童赋权,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赋权”这个词,因为它仍然是上位者给下位者。但我找不出更好的词,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结构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儿童”在哪儿。
首先,我们要先成为伙伴,大人得少说话,让孩子多说话。
告诉大人,我去嘎嘎共和国了
原先iSTART里成年艺术家和孩子的展览是分为两个平行展的,因为成年艺术家更有经验和观点,孩子的东西很有意思,可是太多太杂,放在一起会有点吃亏。但孩子们的能量在持续爆发,一直到2017年,我觉得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有三个小女孩托我太太把一本带锁的紫色小本送到我手里。听我太太说,这三个孩子从9岁开始就秘密利用课外时间传递这个小本子,用三年时间创造了一个来自外太空的虚拟“国家”——“嘎嘎国”。

我第一次拿到那个本子的时候特别震撼,没有任何人指导她们,也没有什么框架,她们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像一种文学叙事。那本“国家指南”上满满一页写着目录:居民、等级、节日、护身符传说、国歌、法律、梦想、习俗……在嘎嘎国的等级制度里,数字越大,级别越低,所以“叫花子”是地位最高的,而“总统”是最底层的人。
我几乎怀着敬佩的心情邀请这些孩子参与iSTART,并且和艺术机构一起筹备“嘎嘎宇宙共和国”项目组,有150个孩子报名参加,作为首批“国家智囊”参与到更具体的“国家建设”中,我也全程参与了他们建构想象国度的过程。
他们就是自己擅长什么做什么,有的孩子喜欢钱就创造了货币,一个设计能力不错的孩子设计了语言。他们还有一个国家宪章,开头就说嘎嘎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宇宙共和国,我说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国体吗?他们就反问我,你们大人怎么国体弄过来弄过去就那么几种,你们好笨哦,都没有想象力。我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我们每天都在用各种方法证明哪个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还有什么样的能更好。
在嘎嘎国还有一所学校叫霍噶尔学校,孩子们是通过跳进水里来毕业的——那这之前国内出现了一些学生自杀的事——孩子们跳入清澈的水里后所有的抱怨和负能量都会被吸收掉,他们的下一段人生就变得轻松快乐。其实是他们内心的一个困扰,他们听到那些消息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得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本子,很多年之后要么本子去哪里自己都不知道了,要么翻出来觉得以前好幼稚。我们就错失了很多东西。
实际上嘎嘎国到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现在这批孩子和最早那批孩子可能想象的都不是同一个东西,甚至有了迭代,像是同人漫画和二次创造。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其实是可以由其他孩子的活动衍生的,我们老想的是他们得学习成人的东西,为什么同伴的文化不能成为他们的文化呢?
我们的儿童文学真应该交给孩子。去年有个小朋友Lorrie做了一个“人抓风”的项目,它并不是一个肢体游戏那么简单,是一个小朋友和三个成年人玩,一个人扮演人,三个人扮演风,有东风、南风、北风,没有西风,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西风,每一次被抓到的风要跟人家说,我是什么风,再接一句一个什么样的风。其实这样四个人每玩一次就是一首诗。

去年还有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拒绝参加iSTART,他们说没什么想法,不知道要做什么,问能不能提一个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说可以啊。他们就提出做一个“反睡觉联盟”,因为在学校不想午睡,太讨厌了。我们就让学校老师去收集他们不想午睡的时候在想什么,最后他们做了一张3米高的床立在墙上,把那些孩子的想法做成投影投在上面,可以进行互动。你会看到一只奶牛,奶牛不断地靠近屏幕,越来越大,可以看到奶牛上的黑色斑点上有字,写的“吃冰淇淋”“去动物园”这些话,最后奶牛爆了,这些黑斑就飞走了。
这些小朋友想说的就是,大人就是吹破牛皮的奶牛。
这样的每个项目都充满了奇思妙想。
我在跟这些项目的时候经常要和儿童交流,但并不会模仿他们所谓低幼的语气,而是用跟平常人说话一样的方式。儿童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大人总觉得他们幼稚,在无理取闹,要么生气要么哄,其实可能是大人跟不上他们的思维。跟孩子说话思维得更加敏捷,因为要耐心捕捉他们的许多信息并且做出回应。
他们的很多想法往往很有穿透力。前年和去年我总是很忙,有时候回到家也必须加班。有一天我儿子睡觉前看到我还在工作打字,他说他也想试试打字什么感觉,然后他就爬上来噼里啪啦打了一会儿,说,你们大人好孤独哦。当时的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圣人一样,咚地敲了我一下。
乌鸦的勇气
孩子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发声机会的。
2020年,有一群高二高三的孩子,这些孩子因为要高考或者出国,家长很少同意他们参加项目,但他们觉得不是为了自己来参加iSTART,是在代表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