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赵冬梅
作者: 徐琳玲
江南的5月黏腻闷热,雨一阵,晴一阵。抵达金陵次日,赵冬梅蹬着一双带跟的皮鞋,就去寻访王安石的半山园故居。熙宁九年(1076年),这位一心推行变法的“拗相公”被二次罢相,自此彻底远离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六朝古都的钟山脚下筑居、读书、研习佛经,直至元祐元年四月(1086年5月21日)离世。
“王安石变法怎么就算失败了呢?神宗可是他最好的学生。”她一边强忍着脚上的疼痛,一边念叨着在故居里看到的解说词和那些名人评价,略略不满:“梁任公是个大才子,但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他们‘找到’的那个王安石,是不是真实的王安石呢?”
眼前的赵冬梅,要比电视里看上去更娇小一些。她生气勃勃,语速飞快,爱自拍也爱八卦,还有几分古灵精怪——正是花木繁盛的晚春时节,她钻进校园里的花丛中,把脸凑在两朵硕大的芍药花中间来一张合影,然后发到微信朋友圈——“好像还是我的脸更大一些。”
我们正儿八经地谈起她的《大宋之变》。说起写作后半部遭遇的困顿和之后的豁然开朗,她一口一个“guang”——足足十秒钟后,我才猛然反应过来,那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温公的“昵称”——每一位“祖国花朵”童年思品教育读物里的那个“砸缸少年”。
一提到讲述北宋仁宗朝政治的热门电视剧《清平乐》,她有几分小激动,为里头的朝堂戏连连点赞,“好的影视剧真是可以开民智的。”紧接着,又和我一道狠狠吐槽了另一部以北宋真宗朝为背景的大女主戏——“从头到尾都是错,第一句台词、打出的第一行字幕就已经是错了。”
2012年,因着央视“百家讲坛”编导一句“知识是应该分享的”,当时还是副教授的赵冬梅登台讲寇准、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小小地火了一把,成为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走上电视向公众传播历史学知识的学者。
十年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崛起,公共文化领域兴起一波接一波的“宋代文化热”,她也被推着往前走,在“出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喜马拉雅开课、和史航等文化界大V们同台直播,逐步转型为公共史学界的大V和颇为闪亮的知识界“网红”。
在诘屈聱牙的学术语言和群众的“喜闻乐见”之间,她切换自如,飒飒有风。
“八八级的赵冬梅”
在拥有六万五千多粉丝的微博上,赵冬梅的ID叫“八八级的赵冬梅”。
17岁时踩着80年代的尾巴考进北大历史系,赵冬梅一路读本硕博,然后留校任教至今,除了短期的国外访学、授课,从未离开过未名湖,是纯度百分百的老北大人。
她说自己是“迷迷糊糊做着梦上了北大”。在还没来得及“内卷”的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人是昏睡着的,中间偶尔有几个醒早了的,然后脑子还不错,略略勤奋一点,然后进了北大。”
那个年代的文艺少年们都做过五彩斑斓的文学梦。那时,赵冬梅想当作家,“写历史小说的那种”。虽然家里没人教,但她早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读中文系和当作家不是一回事。
念中学时,她无意中从集市书摊上买到了一本讲文化大革命的书。书的装订质量极糟糕,连页码都是错的。但她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干脆自己把小书拆了,重新装订了一遍。“就是很好奇,很想知道那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彼时,经济建设已成为时代的“中心”,金融、外贸、法律这些看上去最能赚钱的专业热了起来。填报高考第一批录取志愿时,赵冬梅填写了一溜的“历史专业”——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到第二批志愿,才有了中央财经学院这些看起来很有“钱途”的热门高校和专业。
“我当时第一想去搞历史,如果搞不成历史,那就去赚钱好了。完全和别人倒着来。”如今回过头看,她狠狠地夸奖自己当时真是个“很聪明的小孩”,很早就靠自己悟出一些个道理——譬如“学那些虚无缥缈的,就一定要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如果是搞实务的,专门院校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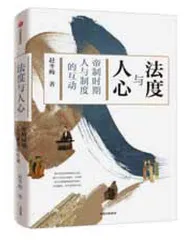
偶尔地,如今已是宋史学者的赵冬梅也会遐想一下人生的其他可能性——如果当年念了法律呢,现在大概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吧;如果去读了经济、金融呢,也许在一家大企业里当一个独当一面的女老总——“就是看上去很白骨精的那种。”
“树林里有好多条路,但你最后只能走一条路,没有尝试这回事。一条路就造就了一个人,”抑或一个王朝、一个国族长达数千年的命数。
2020年,赵冬梅出版了《大宋之变,1063-1086》。该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主线,聚焦从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司马光离世的北宋三朝政坛风云。通过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推演了皇帝、大臣、后妃在这些政治事件背后的心理、情感动因,再现了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一批北宋政治家在历史变局中的行动与博弈。
在赵冬梅看来,从1063到1086这24年间,北宋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深究其因,转折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此前,北宋历经开国三朝至仁宗朝,政治文化达到了帝制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接近于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但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大逆转,破坏了之前政治生态里的宽容共识,朝廷政策出现法家转向,并最终走向皇帝和受其信任的宰相的专制;士大夫群体内部恶性分裂,批评纠错机制失灵,宋帝国因此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
由此,她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国破家亡虽然发生在宋徽宗-“奸臣”蔡京治下,其根子却是王安石与神宗共同种下。
面市后,这本完全颠覆公众对“王安石变法”的惯常认知、有着强烈人物传记风格的著作很快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截至2021年5月31日,该书已加印5次,发行达56642册,获得第十六届文津图书推荐奖,入选2020年“搜狐文化”、《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等榜单。
“好看。”“读着都停不下来。”“完全改变了我过往的认识。”——这是赵冬梅从读者那里得到最多的反馈。在一些青年历史学人论坛上,也有人批评该书对王安石、司马光这对著名政治“冤家”的评价“有失公允”。“拉偏架的嫌疑很大。”一位近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如此点评。
虽然戏称自己是“司马温公门下走狗”,赵冬梅认为自己在《大宋之变》中对司马光、王安石两人都有诸多深刻的批评——一个是患有政治“幼稚病”,完全缺乏行政能力和政治手腕,而且有道德洁癖;一个能力极强,并有达成目标的决心,“但在方向上错了”。
“其实,我真正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惋惜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有了。北宋最好的东西就是政治生态问题,但它很脆弱。最后,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它一步一步被毁灭掉。”
尽管得到大众的“追捧”,赵冬梅仍把《大宋之变》视作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她到目前为止“唯二”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另一本则是代表她在宋史领域专业水准的纯学术著作——《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通常写人物传记的人,哪怕写的是政治人物,他一般不会太深地涉及政治史、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甚至是军事史、社会生活史。但我是希望把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作品。”
“它是好读,但它的知识浓度一定是不输于、甚至应该超过学术论文这一类论述性作品。因为论述性作品通常是单线,而叙述性作品其实可以多线,不但多线,我还希望是多义的,可以把很多东西都综合进去。”
在赵冬梅看来,“好读”应当成为叙述性历史著作的一种重要特质。“它立足于真实,立足于史料,立足于严肃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再好读,我觉得应该不是缺点。”
勾勒人心与制度
读研究生时,赵冬梅主攻宋代官制和制度。在中国史学界,制度史研究是北大历史系的“立家”根本之一,前有邓广铭、祝总斌、田余庆,现有阎步克、邓小南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
研究了近20年官制,赵冬梅打趣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从没管过人,曾经做过最大的“官”是本科生的班主任,如今“高升”了,是系里的工会主席。但她对那些古往今来心怀政治理想并实现之的人都存有最高的敬意。
看上去冰冷无趣的制度,赵冬梅在里头兴致勃勃,因为在制度里看到人心,看到人与制度的互动。等到自己当导师带研究生,她越发认同:从制度史研究入手,是进入史学领域的一条能打下基本功的好路径。
“制度怎么会是枯燥冰冷的?绝对不是。就像今天你也被制度困着,有愉快的地方,有不愉快的。在制度面前,个体的人力量很弱小,但是那些真正取得权力的人,或者说一批人形成一种力量之后,他们是有可能改变制度的。所以,你看到了人,怎么可能是枯燥的呢?”
顺带地,她也小小挤兑了一下隔壁中文系——“你去书店里翻一翻,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写的宋代文学家小传,一涉及官衔,80%以上都是出错的。”“因为这套官制很复杂,如果你没了解,那你看了老半天,也不清楚古人挂着的这些官衔到底干什么,因为里头有虚有实,然后同一个头衔有时实、有时虚,那究竟是实的还是虚的呢?你只有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你才知道这人具体是干什么的。”
早年受邀在《百家讲坛》讲宋史时,赵冬梅一度动过讲制度和社会文化史的念头——最终被节目方给否了——“相对而言,电视受众的面可能更广,以我父母辈的人居多,整体上的知识文化层次略低一些,他们认为节目得去够着那些人。”
2019年底,赵冬梅最终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过足了一把瘾,开讲“冬梅讲国史”, 从“典章经制”的视角来审视王朝的“理乱兴衰”。每周更两次,一篇接着一篇讲,最终形成了40万字讲稿。2021年,这最终整理出版为《法度与人心》一书。
在《法度与人心》中,她也尝试了一把通史的写作——里头既有她读前辈、同行史学著作的笔记与思考,也有她个人在几十年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对中国古代史的通贯性理解和把握,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存在的特殊通史”。
当初之所以到喜马开讲通史课,缘于赵冬梅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不服气”——每次出去和读者、观众交流,几乎都会有人请她推荐适合一般大众阅读的中国通史书籍,她思来想去,推荐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后来,我和系里的张帆、叶炜老师交流,结果他们自己给非专业读者推荐的,也统统是《国史大纲》。”
“我就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推荐来推荐去的都是《国史大纲》,可是《国史大纲》是钱先生1940年代写的。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推荐这个,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历史学界这么多年的工作仍然是不能够被外行看见的。”
“我就是不服气。这80年,我们史学工作者显然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可能缺一个总结,缺一个在(学术圈)里边的人愿意掰开、揉碎,按他的理解讲给大家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相比钱穆先生的时代,一是今天的我们更心平气和,此外我们已有了更深厚的学术积累,很多研究已经展开。我做这些,是希望能让大家看见这些工作。”
人:人民周刊 赵:赵冬梅
为什么今天我们爱宋朝
——对话赵冬梅
人:钱穆先生对宋的评价一直颇低——认为它“积贫”“积弱”,在政治制度上也几无建树。但在《法度与人心》中,你对宋代的赞誉极高——认为它是“帝制中国史上政治文化的顶峰”,“是接近于理想状态”。为什么你们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分歧?
赵:钱穆那个时代当然瞧不上宋代,因为宋“积贫”“积弱”,而他们所立足的是一个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自1840年以来就是时代的主题。哪怕是像钱穆这样对传统怀着温情与敬意的人,对我们的文化也主要怀着一种批评的态度,然后当他想回头从历史上找亮点时,容易找到的肯定是像汉唐这样的强盛时期。但是,即便是钱穆也同意,他和严复都承认:宋代其实是“后代中国”的开端,它以前是一个“古代中国”。是宋代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子,这就是宋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