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开放,让互联网真正互联
作者: 胡泳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的一片高歌猛进之中,我曾撰文谈及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隐忧,其中之一便是垄断造成的企业创新隐忧。
我写道:“互联网时代呼唤的是开放、包容和自由竞争,互联网也应该是协作和共享的平台。可是与其背道而驰的想要一家独大的垄断逻辑,却开始逐渐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当时,更准确地说,中国的互联网不是一家独大,而是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独大。它们彼此采取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中国互联网不能完全互联互通。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新浪微博禁止进行微信公众账号推广;微信屏蔽来往分享链接、快的红包,腾讯被指“选择性开放”;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在这个过程中,屏蔽甚至成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为其贡献流量,那一方屏蔽这一方,则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规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这些你来我往的狙击中,用户的利益何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户对这些损害自己利益的平台行为不仅完全无能为力,而且眼看着类似的屏蔽,都打着更好服务用户的旗号,并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逐渐加码升级。例如,2018年,当字节跳动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开始流行时,许多用户意识到他们无法直接点击进入在微信上分享的抖音链接。消费者也不能从微信内顺利打开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的链接,如淘宝和天猫。这一切的结果是,用户没有办法在数字海洋里恣意遨游,而只能学会在数字孤岛间跳来跃去。
虽然消费者的不满层积,而且平台之间也互相以涉嫌垄断兴讼,但无法互联互通的障碍始终横亘于前,难以移除。最终,这一影响中国互联网已久的痼疾,依靠监管方的强势出手才开始得到疗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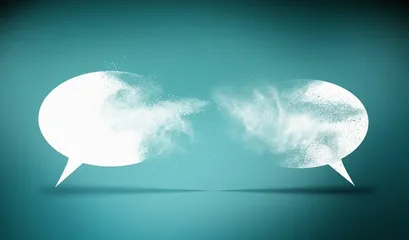
互联互通本来就是互联网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互联网的互联互通问题积重难返,既有数据安全问题,也有隐私保护问题,既有数据共享问题,也有流量竞争问题。复杂问题交织,犹如乱麻,必须先找头绪。
工信部以各大平台的外链管理为切入,抓住了中国网络用户的一大痛点。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和正常访问,弊端重重,既影响了用户的体验、损害了用户的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发展。对此进行整顿,势在必行。
然而,中国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并不是开放网址链接那么简单。
最基础的互联互通
最基础的互联互通,要看路由和互联的监管政策是什么样的,以及运营商自主权的多少,会如何影响互联网的联网方式。
在一些国家,日益出现的一种趋势是,对互联网运营商如何管理网络互联和路由进行监管。互联和路由选择是基于本地的和运营的原因而作出的关键决定,为的是确保网络的适应性和最佳流量。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在互联和路由方面的自主权不断减少,那么它将破坏互联网的两个关键属性:具有共同协议的开放和可访问的基础设施,以及分散化的管理和分布式的路由。
具体而言,第一个关键属性表明,网络或个人节点访问互联网的唯一基本条件是使用其通用协议,包括TCP/IP协议。这种“无许可”的最低技术准入门槛,构成了互联网快速增长和全球覆盖的基础。
2021年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首次提到“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等说法,指向互联网平台单一垄断行为背后的生态垄断和更深层次的平台治理难题。9月9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在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多部门对平台生态垄断的监管趋严。9月17日傍晚,腾讯发布《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调整声明,称将在“安全底线”基础上,允许用户在微信“一对一聊天场景中访问外部链接”。微信群暂不在开放范围当中,后续将开发功能提供访问选择。腾讯表示,微信还将推进“分阶段、分步骤”的互联互通方案,也会积极配合其他互联网平台,探讨跨平台顺畅使用微信服务的技术可能性,实现进一步的互联互通。
而第二个关键属性则意味着,每个网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商业模式和本地要求,独立决定如何将流量路由至他处。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没有集中的控制或协调,而是由每个运营商作出自己的决定,并与它选择的运营商自由协作。
互联网越是接近于以符合这两个关键属性的方式运行,它就越是开放和灵活,有利于未来的创新,以及协作、全球到达和经济增长等更广泛的利益。互联网离上述的联网方式越远,它就越不像全球互联网,而会走向所谓的“分裂网”(Splinternet)。
例如,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Sovereign Internet)正在进行的集中控制的趋势,大大降低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网络恰恰在需要更多弹性的时候反而弹性变差了。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在监管机构认为存在来自国外威胁的事件当中,运营商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路由。一些互联决定将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则需要依据当局作出的决定。运营商反映当地情况和自身的运营及业务需求的自主权和能力,都被大大削弱了。
而美国“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的五项新工作涉及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从物理基础设施(电缆)、网络互联(电信运营商)到云系统和应用(应用商店与应用程序),阻碍了网络之间的互联,也妨害了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和机会。
正如特德?哈迪(Ted Hardie)对拟议措施的批评所说:“不同网络的互联是互联网及其所有服务和机会赖以建立的物理基础。阻碍这种互联打击了作为企业的互联网的核心。它也使互联网处于危险之中,并将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拥有最广泛的国家基础设施。它们为中国约70%的家庭宽带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并为小型接入商提供大部分骨干网络。这三家公司还控制着国际连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经营网关,将所有互联网流量输送到中国境内和境外。
除了对国际网关的垄断外,三家公司对全国市场的支配并非中国独有。然而,这些公司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中国接入商之间的互联制度,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层级网络拓扑结构,破坏了分散化管理和分布式路由。中国网络的这种极端层次化拓扑结构以及对极少数中央控制的国际网关的严格设限,意味着中国并未体验到全球互联网,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
中国的运营商必须在集中管理和集中路由的情况下工作,这与互联网灵活、有弹性和可扩展的特性正好相反。因此,它们无法优化连接,无法选择网络伙伴进行自由合作,无法为用户提供真正的全球覆盖,似乎也无法提供最佳服务质量。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围墙花园”
在基础设施之外,互联网背弃互联的初心,还出于其他的复杂原因。
首先是数字平台的崛起,令互联网迅速变成一种平台控制物,这出乎很多互联网用户的想象,因为去中心化曾被广泛认为是互联网的标志。现实的演变是,10年前,人们还拥有一个开放的网络乌托邦,而到了今天,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若干互联网巨头联手控制的网络空间,它们拥有许多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平台”——每个其他企业甚至是竞争对手所依赖的基本构建模块。
数字平台已经成为纵向整合企业的真正可行的替代商业模式,也代表了一种与更典型的市场结构有着显著不同的经济协调活动的机制。这些平台是不可能躲开的;你可以选择退出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但它们一起形成了覆盖整个经济的镀金网。
而随着其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开始遭受质疑,随着它们凭借巨大利润成为经济主宰而引来垄断的指责,随着人们担心自身的政治见解、知识习惯和消费方式都可能经由算法而为人所操纵,这些平台现在到了被迫自我反思的时刻。
阻碍互联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苹果发明了中央应用商店,由应用商店又催生出大批新经济活动,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App(应用程序)里从事商业活动。以万维网为核心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连接的、透明的和可访问的;相比之下,移动互联网是封闭的,特别是苹果在移动领域的战略被描述为旨在创造一个“完全集成的封闭系统”,其中公司“保持对整个产品生态系统的高度控制”。
这些开放性的差异反映在移动互联网接入中“围墙花园”模式的重新出现。“围墙花园”的比喻出自早期的拨号上网,当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试图将用户限制在自己的专有内容中,而不是把业务定位为通往整个网络的门户。这种早期的“围墙花园”后来渐渐走入末路,但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围墙花园”模式卷土重来,因绕过万维网的移动应用程序的爆发而得到加强。
应用程序的设计,部分是为了弥补基于移动网络访问的各种缺陷。尽管它可以提供高效和用户友好的体验,但移动应用程序模式代表着一个比万维网更加不开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例如,主要的应用程序商店(无论是iTunes App Store还是Google Play)发挥着强大的把关作用,而万维网中的内容和应用程序却可以绕过中介机构。这是内容和应用传播上的一个根本变化。
一些批评者认为,限制可用的内容来源和应用程序的范围,可能会扼杀创新。例如,应用程序往往只能通过专有的应用商店获得,这些商店控制其平台对开发者的开放性,并限制用户在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和链接。开发者被迫为每个平台定制它们的应用程序,这导致了额外的成本。一旦应用程序被应用商店批准,就会受到排名和特色列表的影响,这使得新应用程序打响知名度和在竞争中胜出变得特别困难。赞扬App的人则以应用程序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例,指出App创新为用户提供了在家接受服务、与医生互动、进行金融交易、管理员工工作甚至确保停车许可等的新途径。无论如何,我们难以否认,尽管在向移动应用迁移的过程中,巨大的终端用户利益被生发出来,却也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利因素。
中国互联网要想互联互通,一个关键举措是打开应用程序之间的通道,因为过去十几年来,阻止应用程序用户从使用的应用程序中访问对手的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
以媒体App而言,在这种“围墙花园”里,读者无法进行互动评论。《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发行人和编辑杰森?庞廷在讲述该杂志的App实验时痛切地说:“App试图把旧式、封闭的印刷媒体气质强加于崭新、开放的数字化空间。”媒体App和用户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获取习惯冲突:读者希望应用程序拥有互联网式的链接,并且可以随意评论。如果新闻应用不能和其他数字化媒体相容,那么不管该应用多么漂亮和新奇,读者的沮丧感都无法消除。
移动互联网的终端设备本身在开放性方面也有根本的不同。移动手持设备(包括平板电脑)远不如个人电脑开放。与个人电脑迥异,移动手机主要是封闭、专有的技术,人们很难为不同的用途进行调整和编程。通过更封闭、更难编程的设备上网的用户,没有能力提升网络服务,也没有能力获得相应的好处。
“围墙花园”式平台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互联网被切分成若干个巨大的“电子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的门口都蹲守着一个巨大的怪兽,人们被关在电子集中营里,还以为那是遍地芬芳的花园。
而这些平台无不视数据为金矿,以流量为生命,通过设置技术壁垒,阻碍数据跨平台转移,造成互联网上高墙林立,更出现平台通过数据“绑架用户”的怪象。
平台大循环,胜过单一平台的小循环
由此可知,中国互联网要想互联互通,一个关键举措是打开应用程序之间的通道,因为过去十几年来,阻止应用程序用户从使用的应用程序中访问对手的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